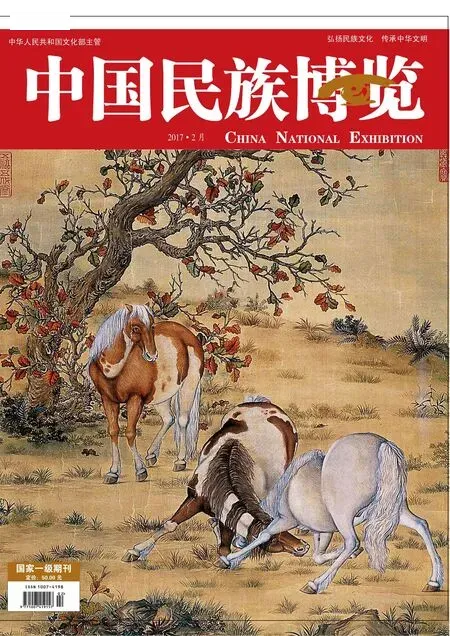Cornelius Cardew實驗音樂作品《The Great learning》中的中國儒家思想研究
黃椏婷
(四川音樂學院,四川 成都 610021)
Cornelius Cardew實驗音樂作品《The Great learning》中的中國儒家思想研究
黃椏婷
(四川音樂學院,四川 成都 610021)
《The Great Learning》是卡迪尤創作的樂隊和人聲的非標準型態的作品,分為七個段落,創作素材來源于中國古老儒家著作《大學章句·序》中的七句話。本文對實驗音樂發展的歷程進行梳理,再探究Cornelius Cardew實驗音樂作品《The Great learning》中運用的音樂素材與中國儒家思想的聯系。
實驗音樂;Cornelius Cardew;《The Great learning》;《大學章句》
一、實驗音樂
“實驗音樂”(Experimental music),是一種從20世紀中葉開始興起的音樂,主要流行于北美地區,其創作特點是創作成果的“不可預見”。約翰·凱奇①是最早使用這個詞的作曲家之一,主要創作手法是利用不確定性技術,尋求未知的結果。
實驗音樂,作為20世紀現代音樂發展歷程中出現的一個集激進的創作觀念和手法于一身的新音樂概念,具有不定、變化的特性。實驗音樂一詞在學術界認識中,尚未有明確的定義。因此,當人們談到實驗音樂時,將其作為一種音樂類別來看待,將某種或某些音樂現象歸于實驗音樂。《新格羅夫美國音樂辭典》之“實驗音樂”詞條中,約翰·洛克威爾②明確指出,實驗音樂尚無法定義,人們在描述它時,概念十分模糊。[1]
1953年,皮埃爾·謝弗③最先發展了具體音樂,作為創始人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實驗音樂樂隊GRMC。這是謝弗的一種嘗試,他反對將“具體音樂④”歸入電子音樂⑤,認為應當將具體音樂、電子音樂、磁帶音樂⑥和世界音樂⑦全都包含在“實驗音樂”范疇。約翰·凱奇早在1955年已開始使用“實驗音樂”一詞。在凱奇的定義下,實驗音樂是“一種成果不可預知的實驗創作”,且完成一部作品,會留給演奏者部分空間發揮創作。邁克爾·尼曼⑧在凱奇實驗音樂定義的基礎上,將“實驗”一詞延伸到對更多作曲家作品的描述中,如美國作曲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厄爾·布朗(Earle Brown)、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等,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作曲家,如科尼利厄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基思·羅(Keith Rowe)等。并不認為當時歐洲的前衛音樂家們,如布列茲(Boulez)、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的音樂屬于“實驗音樂”的范疇。尼曼認為“實驗”一詞形容前者的音樂是恰當的,因為“實驗”一詞不是用來描述一個完成之后用成功與否來判斷的行為,而是一個在完成前不知道成果是怎樣的行為。大衛·柯普(David Cope)也區分了“實驗”和“前衛”兩者的不同。他認為,“實驗音樂”是指一種“反抗接受現狀”的態度。籠統地說,前衛音樂游走于傳統的極限邊緣,而實驗音樂則已然佇立于傳統之外。1958年,雷賈仁·希勒(Lejaren Hiller)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建立了工作室,第一次顯著使用電腦創作音樂,成為第一名實驗音樂創作總監。他同艾薩克森(Isaacson)將“實驗音樂”與計算機控制作曲法聯系起來,從科學角度看待“實驗”一詞,即“基于既定的音樂技術上為新作品做出預測”。“實驗音樂”一詞在當時也與電子音樂同用,特別是用于法國謝弗和亨利早期的具體音樂作品中。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科學、文化、哲學等領域的復合影響下,現代音樂環境中出現的各色特立獨行的嘗試不斷擴充著實驗音樂的內涵,噪音、電子音樂、計算機音樂、偶然音樂、微分音音樂、簡約音樂等無一例外地加入此行列中。[2]
二、The Great Learning中的儒家思想
科尼利厄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1936—1981)英國實驗音樂作曲家,60年代改革最有遠見的作曲家之一,卡迪尤最重要的實驗音樂作品是《The Great Learning》(1968—1971年)和《Treatise》(1963—1967年)。1968年卡迪尤與霍華德·斯肯普頓(Howard Skempton)和邁克爾·帕森斯(Michael Parsons)一起創建實驗表演合奏的劃痕樂團(Scratch Orchestra),首演的作品就是《The Great learning》,其中的成員包括專業的音樂老師和學生、視覺藝術家、演員、舞蹈者以及一些沒有藝術實踐經歷的業余愛好者。
《The Great Learning》是卡迪尤創作的樂隊和人聲的非標準型態的作品,分為七個段落,創作素材來源于中國古老儒家著作《大學章句·序》⑨中的七句話。它由即興實驗組成,是一種企圖通過音樂實現平等、博愛的烏托邦思想的嘗試,是20世紀音樂的一個里程碑。
中國儒家思想,儒家比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倫理更政治化[3],把政治權威視為社會秩序的基本條件,儒家反對專制與殘暴,主張仁政,推己及人,儒家的中心價值是仁、誠、恕,重視忠恕之道。[4]仁是最基本的美德,靠自我修養達成。儒家有修己和治人兩方面,修身最為根本,是儒家的起點、“為己”之學。儒家要求人“反求諸己”,找出人生之道,并擇善固執,接受各種考驗。《中庸》主張為人要出之以“誠”,抱持真誠的態度。違背仁義,應感到可恥,勇于改過,所謂“知恥近乎勇”。人要成為有道德修養的君子,不要做只求利益的小人。君子能無私無我,不會自私自利,愿意顧全群體而犧牲小我,把個人利益置于群體利益之下。儒家思想贊賞勇氣,主張見義勇為,敢于據理力爭,但反對為個人榮辱而報復的匹夫之勇,主張中庸之道[5]。儒家具有強烈的入世性格,并不將理想寄托在彼世或彼岸,而要在人間實現理想,具有強烈的托付與使命感,不會拒絕人群脫離社會,亦不擺脫現實生活。要實現自我,儒者必須投入群體,不單求個人的救贖,對家庭、社會、國家甚至整個世界都負有責任。儒家思想是以道德仁義風化天下,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透過道德教化,潛移默化,使人心良善知恥。
中國儒家著作《大學》是一個初學者如何在道德中完善自我的手冊。隨著早期儒家思想關于對人的自我完善和社會轉型的無限樂觀,文本的開篇句為該轉換的標準,它設想社會個體的領導者完美的德性作為引擎可以復興人類社會,改變其他人的行為,到達一個完美無瑕的狀態。
本文將《The Great Learning》的七個樂段列出,著重闡述幾個重要樂段。
(一)第一樂段
合唱(說話聲、吹口哨和敲擊石塊)和管風琴。持續時間30分鐘左右,創作日期為1968年4月末,運用素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在《The Great leaning》中運用的中國漢字都為繁體字)作曲家在樂段開始前給出一個合唱部分的演出指示,由圖表、文字、符號組成,根據字符相對應節奏音符及拆除字符筆畫變成口哨音符。如用石塊敲擊節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分別敲擊八分音符2次、5次、4次、3次、4次、4次、4次、2次,口哨聲按照中文字符“在”“親”的筆畫順序構建音符。[6]
(二)第二樂段
擊鼓和歌唱。持續時間1小時左右,創作日期為1969年1月,運用素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樂段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鼓樂,由26個節奏模式組成,負責樂段的節奏組織。第二部分為歌唱,由25個小節的不同音高排列組成,負責樂段的旋律組織。
(三)第三樂段
大型的樂器和聲音。持續時間45分鐘左右,創作日期為1970年7月。運用素材“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四)第四樂段
合唱(大聲吶喊并且演奏有脊狀線或鋸齒狀的樂器,能發出響亮聲音的物質,搖鈴或作叮當聲)和管風琴。持續時間大約40分鐘,創作日期為1970年10月。運用素材“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五)第五樂段
大量未經訓練的音樂家做手勢,表演動作,說、誦經并且演奏各種樂器,另外,隨意地,10個歌唱家演唱“頌歌”或者分開表演,為默劇表演形式。持續時間大約2小時,創作日期為1969—1970年。運用素材“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作曲家根據原文中的素材,對中國文字的象形含義進行理解,都給出了具體的形體動作說明,每組成員進行動作模仿傳遞。如“而”字,象形含義“頰毛也”,動作說明為“梳理臉上的須發”;“知”字,象形含義“識也”,動作說明為“結合發聲法的射擊動作”等。
(六)第六樂段
任何數量的未經訓練的音樂家。持續時間大約30分鐘,創作日期為1969年10月。運用素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作曲家根據16個字符的筆畫特征分別給出了16段文字的演奏說明,作曲家將原文中所出現的不同筆畫轉換成四種類型的聲音:將“點”筆畫對應為“獨立音符”(Isolated sounds);將“折”筆畫對應為“同步音符”(Synchronized sounds),如果“折”中的第二部分朝向左邊,則表示強音或長音;將有彎曲的筆畫對應為“選擇性音符”(Optional sounds) ;將“豎”筆畫對應休止符(Pause)。[7]如“自”(FROM):發出的或聽到一個獨立音符,并且聽完后緊跟著一段休止,然后四個音符,第一個為同步音符;“天”(THE EMPEROR):一組音符,后接一組選擇性音符;“子”(SON OF HEAVEN):兩個音符,中間間隔一個長休止,第一個音符為同步音符;“以”(DOWN TO):一個同步音符,后接一個獨立音符,然后一個選擇性音符,再接一個獨立音符;“至”(DOWN TO):五個音符,第二個為同步音符,第三個為獨立音符,最后一個音符后接一個長休止。
(七)第七樂段
任何數量的未經訓練的聲音。持續時間大約90分鐘,創作日期為1969年8月。運用素材“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作曲家要求演唱者必須在一次呼吸的長度內完成所規定的重復次數,每行樂譜的重復次數正好等于對應中文字符的筆畫數,每一個演唱者的第一個音符的音高位置是自由選擇的。如“其”字八畫,對應sing8,重復8次,“本”字五畫,對應sing5,重復5次等。而字符“矣”和“也”語氣助詞,作曲家將其轉換為持續的哼鳴聲,無歌詞,無規定重復次數,只需按呼吸長度演唱即可。最后結尾處穿插一段說白段落,并由此結束全曲。
三、結語
以上筆者對實驗音樂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梳理,對作曲家科尼利厄斯·卡迪尤及其作品《The Great learning》和作品中的儒家思想等方面進行了闡述。外國音樂中的中國因素常常是外國作曲家們使用的一種工具或手段,以豐富和發展自己的音樂風格和創作理念,如約翰·凱奇,以中國古代哲學典籍《易經》為創作素材,用類似于易經中的搖簽方式來決定音樂中的每一個細節,演算八卦和拋擲硬幣來決定其音高、時值、長度和速度,創作其第一部偶然音樂作品《變化的音樂》,爾后完善了偶然音樂的創作理念;又如齊爾品的《敬獻中華》,來自于作曲家的一種“歐亞合璧”的理念,將熟悉的材料融入自己的音樂風格。還有許多西方音樂作品中蘊含著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以中國思想為創作靈感的源泉,更深層次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吸收,使得西方音樂閃耀著許多東方元素,為中國文化在世界的普及打開更廣闊的空間。
注釋:
①John Cage,1912—1992,美國作曲家,音樂理論家,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
②John Rockwell,1940— ,美國音樂評論家,編輯,藝術管理員和舞蹈評論家。
③Pierre Schaeffer,1910—1995,法國20世紀著名作曲家、音樂學家、聲學家、作家、工程師和節目主持人。
④具體音樂(Musicque concrete)指處理的聲音素材取自現實生活(因此這種聲音是真實的,或“具體的”)的那種音樂。
⑤電子音樂(Electronic Music)指以電子合成器、效果器、電腦音樂軟件等電子樂器所產生的電子音色的音樂,劃分為三種主要類別:具體音樂、合成電子音樂與電腦音樂。
⑥磁帶音樂(Tape music)指使用多種聲音材料(包括電子化及自然的聲音),通過磁帶及磁帶式錄音機進行創作的音樂作品。
⑦世界音樂(World music)大致可分為兩種:廣義的世界音樂,泛指世界各國的民族音樂;另一種是狹義的概念,即民族音樂、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相結合的混合體。
⑧Michael Nyman,1944—,英國極簡主義音樂作曲家,鋼琴家,音樂理論家。
⑨南宋時朱熹編撰《大學章句》,并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編為《四書》。按照朱熹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弟子們創作,是儒學的入門讀物。因此,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1]朱寧寧.英美實驗音樂:1950—1970年代——傳統邊界之外的探索[D].上海音樂學院,2011.
[2]朱寧寧.何為實驗音樂[J].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2012(2):23—30.
[3]杜維明,陳靜譯.儒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M].上海:中華書局,2014.
[5]黃光國.“道”與“君子”:儒家的自我修養論[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4,53(3):166-176.
[6] Virginia Anderson,Chinese Characters and Experimental Structure in Cornelius Cardew’s The Great learning[N].From JEMS on line,2005-3-17.
[7]羅薇.Cornelius Cardew《碩學》中的“中國文字”實驗音樂手法[J].西安音樂學院學報(交響),2007,26(2):34—40.
J601
A
黃椏婷(1992-),女,漢族,四川瀘州人,學生,藝術學碩士,四川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學院,研究方向:高師鋼琴。指導教師:王文,副教授。
本文系四川音樂學院2015研究生科研項目《Cornelius Cardews實驗音樂作品<The Great learning>中的中國儒家思想研究》的結題成果(項目編號:CYYJS201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