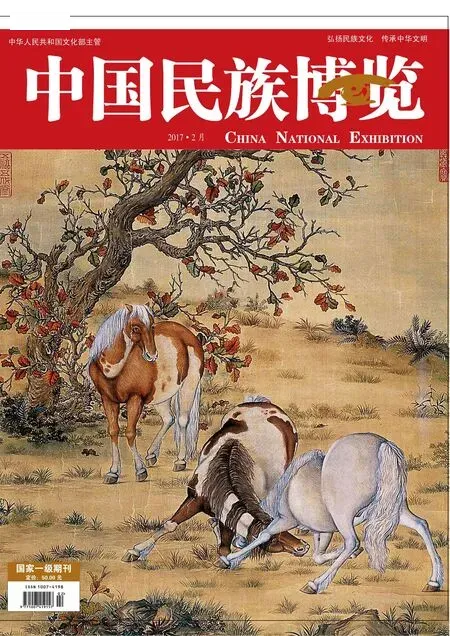淺談導演在傳統南音中的創新作用
——以作品《邂逅·絲韻》為例
王彩娥
(福建省泉州市南音傳承中心,福建 泉州 362000)
淺談導演在傳統南音中的創新作用
——以作品《邂逅·絲韻》為例
王彩娥
(福建省泉州市南音傳承中心,福建 泉州 362000)
南音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古泉州府的一種優美、典雅、古樸的優秀樂種。它歷史悠久,深受群眾喜愛。南音流傳于福建泉州、漳州、廈門、香港、澳門、臺灣及南洋諸國閩南華僑聚居地。隨著人們對南音審美需求的變化,南音不再只是一成不變的形式。如何讓舞美、燈光為其所用,讓演員輕松自如地駕馭其中,更讓觀眾視聽愉悅,這就對“導演”在傳統南音中的創新和起到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導演的職能就是挖掘即將展現之藝術的精髓,前瞻后仰,高角度、全方位地為該藝術服務。本文所要論述的便是人類音樂史活化石之稱的泉州南音與近現代才為人所知的導演者之間的關系,并以南音樂劇《邂逅·絲韻》為例,論述“戲劇”的導演對于傳統音樂如何在新時代的舞臺上創新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南音;導演;創新作用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能亙古彌留并仍在延續的,便是國之瑰寶!物質的、非物質的,在當今這個絢麗的藝術舞臺上競相綻放,泉州南音便是其中之一。泉州南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晉唐時期,其保存了中國古代音樂諸多遺響,專家認為它是“中國音樂歷史的活化石”。泉州南音有著“宮廷雅樂”和“御前清曲”的貴氣,也有著“萬灶貔貅戈甲散,千家羅綺管弦鳴”的基底。而導演和導演的藝術創造,則像一條默默流淌的暗河,涓涓細水地隱含在古老戲劇演出的大河之中,直到近現代才為人所倚重。本文所要漫談的便是兩者之間該如何相輔相成,以及導演對于傳統音樂如何在新時代的舞臺上呈現所起的作用。
泉州地處福建省東南部,北承福州,南接廈門,東望臺灣島,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泉州歷史悠久,周秦時代就已開放,唐朝時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宋元時期為“東方第一大港”,被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光明之城”。正是這么一座曾經輝煌內外,后又偏安一隅的歷史名城孕育和守護著一個古老的樂種——泉州南音。
泉州南音源于漢、唐時期,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古泉州府的一種優美、典雅、古樸的優秀樂種。它歷史悠久,群眾喜聞樂見,人們又稱其“弦管”,也叫“南管”“南曲”,東南亞華僑和港澳臺同胞因為它是故鄉的音樂而又稱其為“鄉音”。南音流傳于福建泉州、漳州、廈門、香港、澳門、臺灣及南洋諸國閩南華僑聚居地。泉州南音主要由指(指套)、譜(器樂曲)、曲(散曲)三大部分組成,它的主要樂器分別是橫抱曲項琵琶、十目九節洞簫、三弦、二弦、拍板等。這些樂器的名目及圖型,在隋唐的“九部樂”“十部樂”或敦煌壁畫及《韓熙載夜宴圖》中都有記載。南音演奏時,左側琵琶、三弦,右側洞簫、二弦,執節拍著居中而坐,古樂研究者認為它是漢相和歌“絲竹更相合,執節者歌”的寶貴遺存。
據史料記載,唐禧宗光啟元年(公元885年),王潮率軍入閩,其弟王審知后為閩王,重視宴慶、祭祀中的各種禮樂,而福建的民間音樂不能滿足其要求,便稷植唐代《大曲》中的“遍”“破”等宮廷演奏音樂入閩,這些宮廷音樂在泉州根植后逐漸形成了南音。“南音”一詞古代就有,泛指音樂或南方音樂,而它作為一個樂種的名稱,則是1952年泉州成立“泉州南音研究社”后才出現的。
1993年,筆者通過層層考核,進入福建藝術學校泉州南音班學習,開始與南音這一古老而又深沉的樂種進行了近25年的耳鬢廝磨。
早在學生時期,用不同形式演繹傳統南音中不同故事內容的想法就不斷地在撞擊著筆者的思緒。年少輕狂,懵懂無知,縱有諸多想法,也常因為知識、經驗和表達上的欠缺而一一不得實現。彈指一瞬,心中那顆一直跳動著的種子,終于2013年勃然萌發。
2013年9月,當筆者跨入上海戲劇學院大門的那一刻,心中豁然開朗。專業課程、名師講堂、作品研討、觀摩采風,時間將無數訊息轉進渴望的心田,不斷的研習與課堂實踐讓筆者的導演思維逐漸清晰。導演是什么?導演是劇作思想的揭示者和舞臺演出藝術的創造者,是舞臺藝術的靈魂人物。導演的任務是準確地揭示劇本的思想內涵,并將這種思想內涵賦予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最終在舞臺上體現出來。
前蘇聯導演尼·奧赫洛普科夫曾經說過:“導演應該積極地、富于創造性地幫助演員。歸根到底,就是應該向他提出更高限度的任務,而不是那些只要演員‘方便’就行的東西。”方便,是的!對于傳統藝術,除了亙古不變的固守和創新的紛爭外,“方便”也是舞臺演出形式單一、演員滯殆的原因之一。筆者前面說過,自己從事南音已近25個年頭,對于傳統,心存敬畏,對于創新,亦毫不猶豫!用先輩遺留下的瑰寶,展示現代南音一輩的風姿,是筆者歷來的索求。然,筆者很清楚南音演員“不動則雅,動則死”的尷尬。怎么讓演員“動”起來卻還能“活”,這是對筆者身處導演一職的最大考驗。
美國戲劇教育家貝克在他的《戲劇技巧》一書中說過“動作是激起觀眾感情最速捷的手段”。南音的表演形式要改變,“動”是必然,但是必須“動”得適然,“動”得合理,更要讓演員“動”得舒坦。
2015年7月,筆者應單位領導要求,構思并導演一臺南音專場。2003年,泉州南音樂團申報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時,由北京聘請一位知名導演,為赴聯合國匯演作專場排演。這應該是泉州南音第一次由非南音人士以導演的身份對南音進行的全面包裝和整合。那次的成功毋庸置疑,南音的申報也最終圓滿。2013年,泉州南音樂團再次由外來導演介入,完成一臺傳統與創新相結合的專場。兩臺專場相隔十年,可見一般人對南音這一傳統音樂的敬畏,也反映南音對于現下舞臺趨勢的慢熱(其實當下一些大操大辦的舞臺表現形式筆者也非全然茍同),現在,筆者身兼演員、編劇、導演,如何呈現出一臺領導滿意、自己釋然、觀眾也喜歡的南音專場,筆者誠惶誠恐。
上述兩臺專場筆者皆經歷其中,兩位導演在燈、服、道、效、化上的運籌,和對演員情緒上的引導,給予筆者諸多經驗,取其精華,在于南音的了解上,筆者優于上述兩位導演。書山曲海,筆者不想重復南音無情節、無故事形態片段式的演唱,筆者要做一臺有故事的、情節連貫的、“音”“畫”“意”相結合的南音樂劇,于是,《邂逅·絲韻》誕生了。
《邂逅·絲韻》以閩南人熟悉的《陳三五娘》為載體,對傳統的南音曲目進行篩選并對個別曲目進行章節處理,節選了《陳三五娘》故事里的“燈下邂逅”“暗惹相思”“投荔傳情”“互述衷情”“決意私奔”這五個故事場面,配以相對的曲目將男女主人公相遇、相慕、相思、相隨最后私奔的故事娓娓道來。演出在南音四大名普之一的《梅花操》中拉開帷幕。弟子焚香,先生凈手,于琴案前調弦整音,諸弟子垂首靜立,待先生彈畢,弟子上前恭恭敬敬地接過琵琶作序幕的開始,最后以先生的怡然品茗,欣然環視眾弟子為演出的結束,意在讓觀眾了解到泉州南音的世代相承和南音人的清逸淡雅。借用燈光投影的形式將每場的主題映于后區幕條之上;輔以南音人耳熟能詳的南音清唱曲《元宵十五》第一句唱詞“元宵十五,阮共君親相見”或純器樂合奏、或哼鳴、或女聲吟唱的形式作為主線貫穿全場;再以表演唱、琵琶彈唱、傳統清唱、洞簫音配畫、現代與古裝隔空對唱等表演形式演繹。簡潔雅致的舞美、富有詩意的燈光、淡雅輕柔的服裝再加上演員們濃淡適中的妝容,輕柔地把觀眾帶入了我們的南音故事之中,使其在與南音的邂逅中得到視覺上和聽覺上的享受。讓南音不再只是一成不變的形式;讓舞美、燈光為其所用;讓演員輕松自如地駕馭其中;更讓觀眾視聽愉悅,這就是“導演”在傳統南音中所起到的作用。
導演的職能就是挖掘即將展現之藝術的精髓,前瞻后仰,高角度、全方位地為該藝術服務。筆者脫離以往的演員身份,以導演的意識重讀南音。從構思到文本,從文本再到舞臺呈現,用導演的思維和視角去審視整場演出,舞臺上的一切因為有導演這么個人物而更加有條不紊。越是傳統的就越值得用心去呵護,越是在舞臺上得到認可的就越值得借鑒。當導演出現在傳統藝術中,就表明該傳統藝術正在與當下舞臺趨勢進行融合,其產生效果雖視導演者的藝術修為和文學修養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該傳統藝術仍在探索恒傳之路,仍在為服務當下觀眾而努力。
從一些客觀的反映來看,《邂逅·絲韻》還是比較成功的,不足之處定然會有,不足則修之、改之,唯有行動起來,才有前進的可能。任何藝術形態都不能固步自封,“走出去,請進來”是發展的必然路程,泉州南音在“走出去”和“請進來”這兩方面都還是局促了些,舞臺藝術是一個集體的呈現,任何一個崗位的欠缺都將影響到整體演出效果,全方位、多崗位地培養人才是當下傳統藝術最迫切的任務。但愿《邂逅·絲韻》不再像前兩臺南音專場一般“曇花一現”,而是通過對導演一職的認識與認可延伸到 其他,如演員的表現能力、舞美人員、燈光人員的專業化配置以及服裝、化妝的跟進等,如此這般,傳統的泉州南音何愁沒有煜煜衍生的前景。
J61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