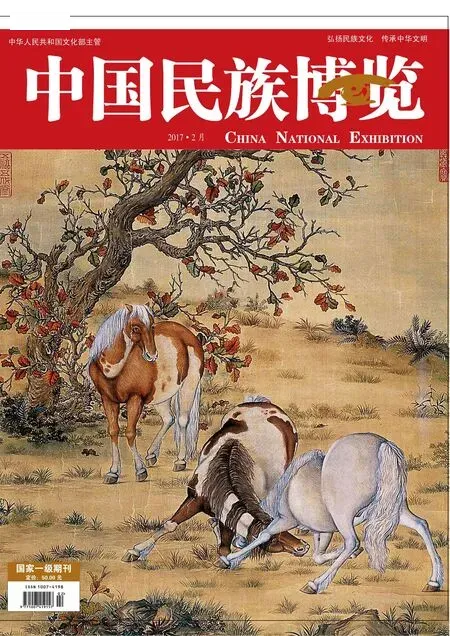從《苦瓜和尚畫語錄》看石濤
——對“一畫”論的淵源初探
潘 飏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從《苦瓜和尚畫語錄》看石濤
——對“一畫”論的淵源初探
潘 飏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00)
石濤作為一個最富個性情感和頗具傳奇色彩的角色,氣質兀傲,畫風也灑脫不俗,筆墨跌宕排奡,不落前人窠臼,他的內心充滿矛盾和隱痛,筆墨中有種淡淡的苦澀味。這是一種和苦瓜極為近似的韻致,所以又號苦瓜和尚,《石濤畫語錄》又名《苦瓜和尚畫語錄》。《畫語錄》識見之獨到、論述之全面,在古代畫壇上沒有幾人能及,論及藝術與現實的統一、內外統一、心物統一、識受同一,還有借古開今論、不似之似論、遠塵脫俗論等,今天畫界還封為圭臬。其實董其昌以“南宗”含蓄的筆墨創出“北宗”簡明的畫風,已經是開了現代繪畫的先河。而石濤睥睨陳法,法古而不泥古,向現代繪畫更進一步。他的主張和實踐使畫家重又面向生活,師法自然,開創了清代中國繪畫的新局面,是中國古典美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本文將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和特殊的身世經歷所形成的獨特的思維模式和藝術感悟的藝術淵源出發,探尋其個性特質及藝術理論客觀內涵。
石濤;一畫論;畫法
一、關于《畫語錄》形成的時代背景
在唐代,尊道教為國教,但兼容并蓄,對待其他教派一視同仁;到了宋朝儒學開始復興,新儒學以一種時代哲學的面目出現,給盛唐以來飛速發展的中國畫提供了營養和能量。程朱理學將佛、道入儒,而當時的繪畫大家基本都有著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又將儒入畫中,改變了繪畫界的思想狀況,三教并立發展到此時已經可以說三教合一,但到了元明間“三教合一”一詞才出現,這時三教間的關系已經有了本質上的演變。而在朝廷腐敗、宦官專權、奸佞當道,地方暴動頻發,沿海又時有海盜劫掠的民不聊生的明朝末年,滿清政府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與統治階層緊張的關系,康熙王朝更是使中國再一次地沐浴在繁榮之中,并且滿人對當時作為文化主流的漢民族文化有著超乎想象的崇敬,各民族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思想與藝術相互交融,儒釋道又一次開始全面勃興,石濤便是在這樣的思想精神高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開始了他的藝術之路。
二、關于《畫語錄》形成的生活來源
石濤,本名朱若極,是我國清代初期著名書畫藝術家,與八大山人、弘仁、晃殘合稱為清初“四僧”,與當時以正統地位雄踞于畫壇的仿古的以王時敏為首的包括王鑒、王翚、王原祁在內的“四王”相對。石濤雖是明太祖之裔,但明朝覆滅時他尚屬孩提,因而削發為僧后雖身處佛門卻心向紅塵,在清高自許與不甘岑寂之間矛盾地渡過了一生,是個很不“安份”的出家人。石濤詩文書畫樣樣精通,畫尤擅山水,廣師歷代大家之長,又從大自然汲取創作的靈感,筆墨酣暢淋漓、秀拙相生、布局新奇、意境高妙、氣勢勃郁,畫面充滿了動感與張力,除了石濤自身性格所致,還有人生里那數十載顛沛流離時的浪跡天涯,正所謂“搜盡奇峰打草稿”。而跌宕起伏的身世和漂泊不定的經歷不只滲入了他的筆觸與畫面,還影響著他的美學思想與藝術理念,這便是《石濤畫語錄》的生活來源,他強調畫家在繪畫中一定要表現自己對自然和人生的獨特感受,所以從他的筆墨里既可以看出他不安于現狀的外在追求,也可以帶你進入他熱切躁動的內心世界。
三、關于“一畫論”形成的思想淵源
清初畫壇以董其昌風格的四王、吳、惲的摹古為宗,而石濤卻用“我自用我法”的吶喊挑戰正統,為當時的繪畫領域帶來了一陣清新的風氣。其實石濤并不是主張不學習古人的藝術文化精華,他本身一開始也是受董其昌所倡導的“南宗”之“頓悟”影響,習畫也是以當時畫壇主流為起點,但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學習古人的正確方式,不是一味摹古,而是“借古以開今”,法古而不泥古,更主要的是要面向自然、師法造化,當然石濤并不是第一個提出以自然為師的人,像唐代畫家張璪提出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元末明初的畫家兼醫學家王履也認為“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還有北宋畫家、繪畫理論家郭熙也很早就感悟到“身即山川而取之”,但是石濤當時的呼聲的確是撼動了清初擬古之風的畫壇主流地位。著述的這本極富創造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繪畫理論,全書共十八章,在論及具體的創作技巧上頗有新見,當然,《石濤畫語錄》不只談筆墨技法和個人經驗感受,最重要的貢獻是他把美學思想和佛教傳統以及老莊哲學結合起來用于解析繪畫本身和繪畫之法。
石濤論畫的最大特點就是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來分析宇宙萬物,闡明繪畫的規律,形成完整的美學體系。其中心思想是“一畫論”這一點并沒有太大爭議,雖然也有人認為書里十八章并列都是重點,但多數人還是統一于其余十七章是對第一章《一畫章》的詳述,全書以第一章“一畫”的原理貫穿到底,但對于“一畫論”的思想來源一直眾說紛紜,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禪宗佛學思想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家思想。
楊成寅教授認為石濤的畫學主要受《周易》和《道德經》的影響,吸收了儒家對《周易》太極陰陽對立統一和后者的有無相生,講辯證哲學,與佛教唯心學說無關。雖然《一畫章》開篇便說了“一”是一切事物的原始,一切道理的根源,一切文化的開端,也是一切哲學思想的起點,老子哲學認為“道”是先于天地而存在,這樣的“道”是“大道”,是萬象根本之“大象”。“道”是“無”和“有”的統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的宇宙觀。莊子認為:“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石濤認為,從“道”至一,就是由無形到有形。一是形的始原,是形象的基礎。由此得出“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這樣一個命題。而這個思想同時也貫穿全書。如第四章《尊受章》中的“夫一畫,含萬物于中。”;第七章《絪缊章》開篇“筆與墨會,是為絪缊。絪缊不分,是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和結尾“自一以分萬;自萬以分治,化一而成,天下之能事畢矣。”等等,提出“一畫”是萬物萬象包括繪畫之形最根本的法則,創作者如果掌握了并加以運用,就可以再現天地萬象,達到藝術創造的最高境界。由此而觀之,“一畫”論與老莊哲學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為宇宙萬物之本源。“一畫之法”亦是書畫之道,是書與畫的筆法之根本,是造型與審美的基本法則,是心法。所以石濤的“一畫”論是在道家“道”生萬物的理論基礎上建立的。
但楊成寅的這種看法未免有失偏頗,“一畫”論不可能與佛教思想無關,畢竟石濤少時就入了佛門,朱良志先生就認為“一畫”淵源于佛家禪宗,并且石濤所說的“一畫”是“不二之法”對應著大乘佛學所提倡的“不二之門”。所以藝術也要超越已有的存在,書心中所思所悟,畫心中所想所感,才能寓情于景,作品才能有生命力。
石濤強調的“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就是說他待人處事不是局限于言語文字之間的外在表現,也不是用約定俗成的方法解決問題,而是用心去思考、感悟,這是佛道的“人無我有、人有我無的空無”之境。“一畫”在自然之奇與人工之精上,他不僅對禪宗的悟性極高,還能參透老、莊、易經和理學,有很強的禪宗慧根。所以應當說石濤“一畫”論受到道家老子哲學啟迪和影響,同時包含有佛教禪宗的思想成分和線索,所以“一畫”論的思想淵源應當是多元的。
一部《畫語錄》從思想和技巧兩方面為當時的繪畫創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他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論畫的創新與變革精神對“揚州八怪”的美學思想影響極大,而其中詩書畫被世人稱為“三絕”的藝術大家鄭板橋的審美思想與藝術精神更是以此為基礎的,是繼宋代郭熙《林泉高致》之后中國繪畫藝術理論發展的又一高峰,此外,石濤的美學思想也為我們當今的繪畫理論和實踐提供了更多的指導和思考,以致三百年后,石濤的美學思想及藝術學思想依然是藝術界研究的重點,其對繪畫美學的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仍然對當代的藝術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
而至于“一畫”的真意,大抵就像中國繪畫的“氣韻”一樣,需要藝術家自己去“遷想”才能“妙得”了罷。
[1][清]石濤著,周遠斌點校.苦瓜和尚畫語錄[M].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2]楊成寅.石濤畫學[J].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J2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