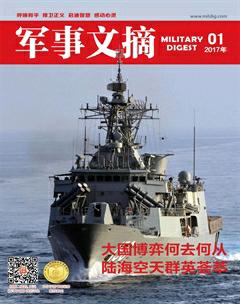透視《孫子兵法》中的戰略智慧
李鑫博
《孫子兵法》是揭示中國古代戰爭智慧的不朽之作,它提出的許多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戰略思想,不僅對當時的戰爭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而且在信息化高度發展的今天, 對國防建設、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對提高我們的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能力,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知勝”思想
“知勝”思想是未戰先勝的科學決策方法,“知勝”的智慧在于通過周密籌劃維護國家安全。孫子在《用間》篇中指出:“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 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孫子的“知勝”思想從根本上說明了信息的掌握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而信息的獲得,不是依靠占卜預測戰爭勝負,而是以科學的戰略思維方法和唯物主義戰爭觀為前提,以“五事”“七計”為主要科學依據。孫子指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即了解對手也了解自己,才能常勝不敗;不了解對手而只了解自己,就會有勝有負;既不了解對手,也不了解自己,就會每戰必敗。《孫子兵法》全篇6074字,而“知”在通篇中就有70處,這足可以說明“知”在孫子軍事思想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古往今來能征善戰者為什么能夠成就輝煌的業績,不單單是勇猛,更重要的是運用科學的戰略思維方式對戰爭的發展進行準確的判斷。
科學的戰略思維方法需要有科學的理論依據作為保證,而“道、天、地、將、法”就是“知彼知己”戰略思維方法的理論根據。在信息化戰爭中,面對的作戰對象可能是多元的。因此,要做到先知。一要知“五事之情”,即了解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和自然地理等諸方面的從戰實力,增強備戰的針對性;二要知“用兵之利害”,以維護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通過分析、籌算,權衡、判斷,得出進行戰爭的必要性,為戰爭決策提供準確可靠的依據;三是要知“得失之計”,通過科學謀劃,反復演練、評估、論證,得出指導戰爭方針或行動方案的優劣足缺,以利揚長避短,以劣勝優;四是要知“諸侯之謀”,通曉世界各主要國家與作戰對象之間的利益關系及政策、態度,以便縱橫捭聞,“親而離之”,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團結盟友。
孫子的“知勝”思想貫穿于他的整個兵法之中,也貫穿于我們現實信息化戰爭的全過程,戰爭力量準備需要先知、盡知,戰爭力量威懾和戰爭力貴使用同樣如此。只有真正做到了先謀而后動,才能使自己在戰爭力量準備上全局在胸,措置裕如,無懈可擊,才能更有力量去維護國家安全。
“全勝”思想
“全勝”是孫子戰爭體系化思想的核心內容。《謀攻》篇指出:“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的“全勝”戰略其重點就是運用非戰爭手段達到預期的效果。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做到在國家綜合實力或是整體軍事力量上占一定優勢,能起到震懾對方的效應。
今天,謀劃全勝戰略從狹義上講就是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作為國家安全發展強有力的保證;從廣義上講就是以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綜合實力為基礎,在平時就要加強國家戰略能力建設。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展雖然仍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世界呈現出多元化、多極化發展趨勢,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交織較深,但霸權主義仍然存在。在這復雜的背景下,我國面臨陸海主權被侵、發展空間受排擠等多重問題的嚴重挑戰。為了有效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和我們面臨的挑戰,確保我國安全穩定地快速發展,就必須營造“全勝”之勢,提髙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維護國家安全與穩定的戰略能力。提髙軍隊整體實力,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提高我軍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軍事實力,營造“全勝”的軍事優勢。為此,必須緊緊抓住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加快實現軍事能力的轉型。重點發展高科技武器裝備,著重發展海空軍、火箭軍以及網絡空間部隊等技術軍兵種的武器裝備建設,加快軍隊信息化的建設和集成,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軍隊信息化。此外,在硬件建設的同時,還應著力發展各軍兵種之間的聯合訓練,探索一套適應信息化條件下戰爭的新戰法,做到以理想的全勝目標為牽引,以非暴力手段為起點,根據戰爭的需要,以最小的代價,贏得戰爭的勝利。
“速勝”思想
“速勝”思想是以節約戰爭資源為目標的作戰原則,“速勝”的智慧在于保持戰略平衡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作戰優勢。孫子在《作戰》篇中提出“兵貴勝,不貴久”的“速戰”思想。他認為軍事上只聽說過雖拙也要追求速勝,而沒聽說過巧于作戰卻追求持久的。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原因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即大量的戰爭消耗帶來供給上的壓力不容許持久;二是政治原因:“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即他國會乘機獲漁翁之利,并置本國于兩面作戰的險惡境地。所以,“兵之情主速”。
加快戰爭進程,實現速戰速決,已成為當今戰爭的一個主要特征。信息時代的今天, 高技術武器裝備的投入使用,加劇了戰爭投入的資本,同時也為加快戰爭速度提供了技術保障。現代戰爭不僅僅是軍事實力上的較量,還是國與國之間經濟實力的對比。因此,“速戰”思想在當今時代體現得尤為突出。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寫到:“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與古代不同的是,迫使對方在政治上屈服已成為當代戰爭的首要目標。因此,“速戰”思想主張使用兵力要注重取得“效果”而不是“造成傷亡和破壞”,要“用摧毀敵人意志的效果補充基于消耗的硬殺傷能力”。這里的“效果”,是指軍事或非軍事行動造成的物理破壞后果和心理影響結果的總和。
近幾場局部戰爭中,空中力量都是作為主導性的力量參與,空中力量成為實現現代戰爭速勝的重要基石,其主要原因:一是現代空中力量具有精確打擊能力;二是現代空中力量具有強大的、全縱深的破壞力;三是現代空中力量的運用具有很強的靈活性。空中力量最鮮明的特征是可以超越地球表面的自然和人工障礙,對敵方核心目標進行精確打擊。因此,信息化的現代空中力量,為戰爭指導者提供了目的性更強、效率更高的戰爭手段,使戰爭不僅能夠“拙速”,而且能夠“巧速”。在利比亞戰爭中,西方國家從設置禁飛區開始,就力圖通過空中優勢遏制利比亞政府軍。卡扎菲政權的迅速倒臺,除了其政府武裝正面配合外,北約軍隊空中打擊功不可沒。因此,今天的國防建設,不僅要發揚孫子的“速勝”思想,而且要創造實現速勝的手段,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兵之情主速, 乘人之不及”,實現戰略目標。
“稱勝”思想
“稱勝”思想是以力制勝的重要原則,“稱勝”的智慧在于遵循力量循環原則的前提下實現“易勝”。戰爭是力量與力量的對抗,“稱”與“非稱”本質上是力量的均勢與失衡。孫子的“稱勝”思想有兩層含義:一是講稱如何生勝,即以經濟對戰爭的支持和制約,進而推進與經濟實力相稱的軍隊數量和戰斗力的總體水平確定勝算的大小;二是講稱如何取勝,即在力量對比上要以大稱小,以多稱少,在不對稱中求大勝。
孫子認為,全面提高軍事實力有5個要素:即度、量、數、稱、勝。就是指國土面積的度決定資源的量,資源的量決定武裝力量的規模,武裝力量的規模決定實力強弱,實力強弱決定戰爭勝負。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因素的長期作用,決定了戰爭的勝負。同時,從度到勝是一個國家在總體戰略指導下,不斷強盛的過程,但并不代表非對稱處于劣勢的就一定是“度”少的一方。當代世界戰略格局國家與國家間的非對稱比比皆是,一定量的稱要達到最大的戰爭效益,就必須做到“以鎰稱銖”。鎰和銖之間相差576倍,即使有“鎰”之能也要謀求易勝,而不能以鎰稱銖,打得不償失的消耗戰。
研究當代戰爭發展規律,要遵循“稱”與“非稱”的基本法則。我國目前處于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綜合國力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但軍事實力還明顯滯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如何確保在未來的戰爭中取得優勢,必須要辯證地看待發展。信息時代的“不對稱”是在時間上的不對稱,講求以先對后;在行動上“不對稱”,講求以快對慢;在方式上“不對稱”,講求以軟對硬。這些原則要與具體的作戰對象、作戰地點、作戰地區的民族文化聯系起來。同時還應利用綜合國力的提升來彌補我軍的弱項和短板,要把科學發展的思想運用到國防建設過程中去,以經濟發展來帶動軍事實力的發展,利用軍事實力的提髙來鞏固經濟發展的基礎,從而有效地應對復雜的國際環境給我們帶來的挑戰與威脅。
孫子的“知勝”“全勝”“速勝”“稱勝”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主要蘊含了先知后動、先謀后兵、先備后速、先稱后易等戰略智慧,為我們今天研究應對各種危機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它宏觀的指導價值已遠遠超出了軍事的范疇,在經濟等其他領域同樣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
責任編輯:張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