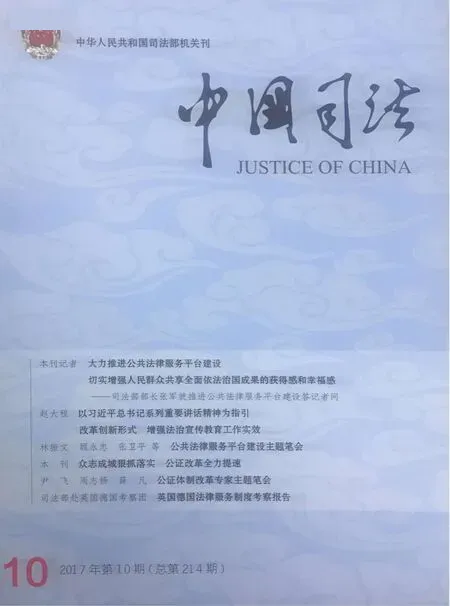法治言論
法治言論
張 晶:以案釋法是落實普法責任制的重要舉措
以案釋法制度,要求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人員、律師等主體利用辦案環節深入解讀法律,圍繞爭議焦點充分說理、解釋疑惑,讓社會公眾更好地理解法律規定,自覺執行法律裁決,并在法治實踐中感受法治精神。普法宣傳教育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項基礎性工程,需要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結合典型案例開展釋法說理,能夠充分發揮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人員等群體的職業優勢和專業特長,提高以案釋法的針對性和說服力,增強法治宣傳教育的實際效果。以案釋法是政法機關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通過開展以案釋法,有助于訴訟參與人及時、全面、準確理解司法辦案行為和所作有關決定的法律或依據,盡可能做到服判息訴、案結事了,進而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以案釋法是司法機關規范自身司法辦案行為的重要方式。該制度建立后,通過強化相關主體在司法辦案過程中的釋法說理責任,有效構建起司法機關與訴訟參與人以及社會公眾的交流溝通機制,客觀上也有利于加強對辦案活動的約束和監督,從而促進司法機關切實做到嚴格公正規范司法。
(張晶如是說,《學習時報》,2017年8月14日)
王遠山:讓法治力量深入人心
領導干部帶頭尊法、守法,本身就是最好的普法。除此之外,由國家機關肩負起全民普法的重任,是近年來全民守法的一項重要制度設計。在“誰執法誰普法”的原則之下,每一個法官、檢察官、行政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在法治實踐中,都增強了普法的意識,增加了普法的考量。他們對當事人普法,對特定人普法,對社會關注的人群普法,同時自己也深化了對執行的法律和相關政策的理解。普法正改變著每一個人的生活,并不斷推動全民守法的局面形成。當下,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越來越濃,法治的力量在一點一滴滲入日常生活。當遇到問題的時候,人們開始不是靠直覺去被動應對,而是自覺運用理性去尋求法律途徑的解決,這正是法治中國開創的新風尚。在全民守法的今天,每一個人都是奉法者。十八大以來越來越多遇事找法、辦事循法的制度安排,越來越便捷的法律服務路徑,越來越高漲的全民法治熱情,正在讓法治力量深入人心,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王遠山如是說,《光明日報》,2017年8月25日)
戴激濤: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立法協商
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做好立法協商工作的根本原則。推進立法協商也應堅持黨的領導,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等依據憲法法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立法程序成為國家意志,確保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立法機關在立法協商過程中,應始終堅持法律至上,著力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創設多元、靈活、開放的協商程序機制,廣泛聽取和充分吸納人民群眾對于立法的意見和建議。進一步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協商工作的體制機制,增強人大在立法協商中的組織協調功能,健全人大代表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工作機制。理想的合乎正義的協商程序是民主立法的規范標準,在設計立法協商規則時,應保證協商主體地位的平等性,使每位參與者能夠平等地表達意見,其意見能夠平等地受到尊重和對待,以形成更強大的論證力量。為保障協商參與者權利的落實,還應建立健全相關配套機制,如立法信息公開機制、立法協商的具體工作機制、立法協商意見的采納與反饋機制等,共同促進立法協商的功能得到最大發揮。
(戴激濤如是說,《學習時報》,2017年9月11日)
姚 莉:探索公正司法的中國經驗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啟動以來,圍繞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各級公檢法單位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進一步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有效確保了審判程序的合法化、正當化,突出了司法權威。同時,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也改變了以往一些過時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推動了司法文明穩步提高,使司法公正得到更好保障。保證公正司法,法院檢察院內部運行的“微循環”也很重要。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以來,法院以完善審判權運行體系為目標,檢察院以充分行使檢察權為目標,大力推進系統內部改革,暢通司法權力運行“微循環”。通過建立法官檢察官員額制,實現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把基層法院檢察院85%以上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院長、庭長等不再簽批案件,確保“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歷史性機遇,構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體制機制改革和科技應用雙輪驅動的司法運行新模式。如今,不論是全方位查控“老賴”、有效緩解執行難,還是視頻作證、電子閱卷、科技法庭、大數據分析等,都在司法機關得到廣泛運用。網上立案、在線調解、實時查詢、互聯網法院等各項司法便民措施,讓人民群眾深切感受科技帶來的方便快捷。司法改革融合科技進步,更加公正高效。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姚莉如是說,《人民日報》,2017年9月11日)
孟令星:探索申訴案件律師代理制度
作為專業提供法律服務的群體,律師代理申訴案件后,能夠有效地彌補當事人訴訟能力弱的缺陷。在程序的把握上,由于律師深諳訴訟程序,因此能夠及時、高效地完成申訴,避免了申訴人不了解申訴程序在期限和程序環節帶來的不便。在文書的寫作上,與申訴人的申訴書相比,律師提供的申訴書更加規范、專業也更有針對性。在證據的搜集和掌握上,很多申訴案件都是由于有了新的證據而提起的,但是鑒于我國目前對于新的證據的認識和規定上的不成熟,對于新的證據的把握,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認定上尚且很難把握,更不要說是缺乏法律素養的當事人,律師的參與能夠起到有效的甄別證據的作用。而且,律師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分子,同樣具有維護司法權威的義務。律師代理申訴案件有利于當事人息訴服判工作的開展,維護司法權威。探索申訴案件律師代理制度,必須緊緊圍繞有利于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有利于司法部門、信訪部門申訴信訪工作的開展和維護司法權威,以及有利于律師業務的拓展和調動律師的積極性這三個有利于展開,通過制度的合理設計,達到三贏的局面。
(孟令星如是說,《法制日報》,2017年9月20日)
陳邦達:高度重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從實體規則和程序規則兩方面入手,為進一步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提供了更加明確的遵循。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于何種證據需要收集、如何收集,證據應達到何種標準、如何認定疑罪等問題,辦案人員在認識方面可能會出現分歧,并由此影響案件事實的準確認定,不利于訴訟順利進行。通過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徹底否定和嚴厲制裁刑訊逼供等侵犯人權的非法取證行為,能夠使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職能行為受到有力約束。過去,我國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則較為零散、不周延,可操作性和剛性不足,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現象。例如,對于重復性自白可采性問題的態度有待進一步清晰,暴力、威脅的方法要達到何等程度,收集的口供才算非法證據等還沒有明確標準。鑒于此,《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擴大了非法證據的范圍,將威脅、引誘、欺騙及非法拘禁獲取的供述納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明確了非法證據的內涵和外延,有助于辦案人員進一步轉變執法觀念,重視對司法鑒定等客觀證據的審查判斷。
(陳邦達如是說,《學習時報》,2017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