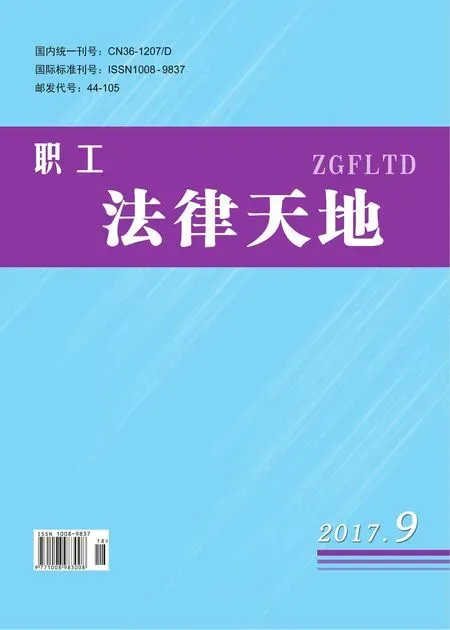淺析英國沉船吃人案
李陽陽
(100083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 北京)
淺析英國沉船吃人案
李陽陽
(100083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 北京)
英國的沉船吃人案,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法學界人世的關注,案件的殺人事實很清楚,但結合案發的情況來看,判決無罪似乎又是合情合理。本文在借鑒先賢的法學思想的基礎上,對于一些主流的無罪判決理由進行了基本簡單的匯總,進行了無罪論述。
沉船吃人;無罪;自然法;分析實證主義;功利主義
1884年,英國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海難食人案“女王訴達德利和史蒂芬斯案”,此案是標準的疑難案件,也是困擾著一代又一代法學家的難題,從不同的法學理論出發去論證,可以得出結論完全相反的有罪或者無罪判決。本文作者才疏學淺,嘗試借鑒先賢的法學思想,進行無罪的論證。
一、自然法的觀點
案發時他們不在法律管轄之下,所有實在法都不適用,只能適用自然法。法律建立在人們在社會中可以共存的可能性上,而在當時的環境下,四名船員在茫茫大海中漂泊,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求生變成了唯一的信念與正義法則,這時候再去跟他們討論遵守法律等待援救,似乎是天方夜譚,也許遵守法律會帶來4條生命的喪失。正如法律諺語“法律存在的理由停止時,法律也隨之停止”。法律的目標是改善共存狀態下人們間的相互關系,促進公平和平等。當只有剝奪別人生命才可能生存時,人可以共存這一前提并不存在,因而他們的行為是遠離我們的社會秩序的。處在自然狀態下的他們,只適用源自與當時處境相適應的那些原則的法律。所以他們根據自然法(法律制度的更高本源)做出了當時最有利的選擇。
二、分析實證主義的觀點
從法律條文著手,審判之依據不應該超脫于現行有效之法律規范。即僅以法律條文為研究參照的對象。這在刑法學中可以體現罪刑法定之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在本案中,其吃人之行是否觸犯了刑法故意殺人之規定?
故意殺人罪需要“故意”,“故意”功能在于表明“犯罪意圖”的要求,例如,缺乏必要主觀狀態的被告(如小孩鬧著玩,低能兒,精神障礙者)應當被判無罪或者減輕罪行,即被告不存在惡意,沒有犯罪意圖,就并不是故意殺人罪的故意。殺人故意意味著,存在其他一些合理的選擇,法律要求他們做出那樣的選擇,而不是殺人這個選擇。被困的船員們有預謀和有意識地采取了行動,但卻是被死亡所強迫的,因此說不是出自他們自己的意愿,因而不是故意的。如果不選擇殺人,他們只能選擇死,基于同正當防衛一樣的原因,他們沒有犯罪的故意。既然“故意”中的內涵有的滿足有的不滿足,合理懷疑得不到排除,根據疑罪從無的刑法原則,應當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決。
再者,我們也準確評估被告當時的心理狀態。在茫茫大海中漂泊數日,沒有淡水與食物,虛弱的身體和極度饑餓帶來的眩暈,加上自然的恐懼和焦慮,我想,這給被告們心理上所帶來的壓迫,很輕易就超過了我們在其他案件中要求的可免責的責任能力減弱的最低限度。
三、功利主義的觀點
功利主義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某些場合,某人不得不死,且讓他去死比讓其他人去死更合理,或者一命換多命,船員們的殺人是為了避免四個人都死亡,選擇殺人好于等待死亡。無論我們對人性懷有多高的期待,我們都必須承認,在面臨現實死亡威脅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死亡總好過四個人的死亡。這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的計算,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這種情形規定了“最大最小值規則”。“最大最小值”規則,就是指使選擇方案的最壞結果優于其他任何可選方案的最壞結果。即使對于被殺的帕克來說,這也是他除此之外最優的結果。我們可以想象,其他三個人生存下來被營救后,出于道義或者出于責任,都會給予帕克的家屬一定的補償,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的結局也比四名被困船上的人員全都餓死的結局要好的多。
四、探究立法精神
法律精神重于法律文字,正如法律諺語所說:“一個人可以違反法律的表面規定而不違反法律本身。”所以,本案應當探究立法之精神,即立法之目的為何,立法之初衷是為了懲戒何種犯罪,程度為何,對象為何?法律并非想懲治在這種不吃人就會餓死更多人的極為特殊之情形。因為這種情況下,社會危害性并不大,發生的幾率也只有偶然性,并不是刑事法律保護之范疇。而且刑法中應當為當事人所考慮,即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之問題。行為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無可奈何被迫實施了違法行為,其刑事責任如何,這就是期待可能性問題。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行為時的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其他合法行為。能夠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如果存在期待可能性,即能夠期待行為人于行為時能夠實施合法行為,行為人違反此期待實施了違法行為,即應當負刑事責任;如果沒有期待可能性,即行為人在行為時只能實施違法行為,不能期待他實施合法行為,行為人因此不負刑事責任。在當時惡劣的情況下,讓他們不選擇犧牲即將死去的帕克以挽救其他三人生命,而是選擇4個人都在小船上慢慢的等待死亡,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五、最優策略的選擇
被困的船員們必須面臨死亡:要么餓死,要么被宣判處死。但是如果這就是僅有的選擇的話,那么船員們為了避免餓死去殺掉一個人,然后碰運氣用一種新的辯解去尋求免受死刑,就是合情合理的,甚或也是必需的。
六、沒有目的的懲罰毫無意義
如果被告確實在理論上違反了故意殺人罪,那么試想一下,我們的懲罰會帶來什么呢?對于這3個沒有邪惡意圖的被告來說,剝奪他們的生命就是最好的處罰嗎?顯然不是的。社會沒有必要去防止3名被告的再次進行侵害的行為,他們的殺人意愿,也只是在被困大海上表現出來的極端處理方法,他們并沒有對真正的社會構成威脅。就算做了有罪判決,假如在下一次遇到這種極端的情況,難道就會有人因為刑罰的震懾而選擇不殺人慢慢等死嗎?顯然,法律的指引與強制作用,在此時毫無意義,殺人仍會是唯一的最優選擇。
行文至此,再回頭看前面淺顯的論述,每一點都是漏洞百出,都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抨擊與批判,當選擇進行有罪推論時,也可以列出很多觀點與理由,然而依然并不是完全的真理,這也就是法理學的魅力所在。各種觀點在交鋒中相互促進,形成整個學科的向前發展。出于現階段的自己,對于問題的探討似乎并不重要,對于這個問題所反映出來的法學思想才是自己學習的重中之重,希望以此問題的研究為契機,繼續對法學這門學科有深入的研究。
李陽陽,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法碩2016級法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