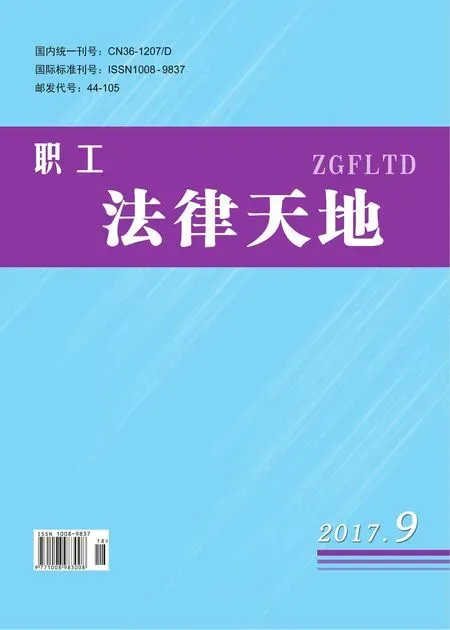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問題研究
周德軍 宮寶芝
(212013 江蘇大學法學院 江蘇 鎮江)
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問題研究
周德軍 宮寶芝
(212013 江蘇大學法學院 江蘇 鎮江)
近代商會歷經了從清末到民初的發展,既與當時政府的積極推進有關,同時也是我國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重要產物。近代蘇州商會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土壤。依賴于當時政府的支持,商會輿論的擴張,商會商事裁判權的行使促進了當時商事活動的發展,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歷史的烙印。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發展模式后,如何借鑒近代蘇州商會發展的經驗,充分發揮當代商會的積極作用,共同推動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問題研究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我國近代商會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商人,受西方商事組織管理思想的影響,開始注重自身組織發展,尋求商事組織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甚至地方自治等權利;同時,商會輿論的有利擴張加強了商會的商事裁判權,在政府管制相對寬松的背景下,商會的商事裁判權有了較大發展。此后,受到社會歷史條件制約尤其是戰亂的影響,商會發展逐步走向衰落。近代蘇州商會及商事裁判權的發展,是這一時期頗具代表的典型,其發展經驗對我國現階段商會發展服務于經濟新常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近代蘇州商會發展的歷史背景
中國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中,“息訟”思想由來已久。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普通百姓之間的糾紛往往通過宗族內部解決,商戶之間的矛盾更多是通過行會處理,很少訴諸有司。加上重農輕商的社會觀念,商事糾紛往往不受重視。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已步入初步發展時期,封建社會經濟體制下的行會管理已經很難再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清政府在1898年曾經設立商務局,兼理商務糾紛,但由于只任用候補官員,不任用商董,導致“商情不通,諸多阻滯”,嚴重制約了商事糾紛的解決。
二十世紀初,在經歷西方列強的武力打擊和經濟制度影響下,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尋求自身的發展道路,而同時期的清政府為了維持其封建統治,實行振興經濟實業的經濟政策,開始推行重商措施[1]。這一時期,各種形式的商會組織紛紛成立,尤其是經濟發展較為發達的蘇中地區。這既源于當地經濟發展本身的物質基礎,商人群體逐步發展壯大;同時,他們的政治民主思想開始進步,階級意識開始萌芽,渴望通過自身的自治進行商事管理。而近代中國國內政局不安,政府對地方性組織的約束力大為削弱,也使得這一時期商會組織的發展得以有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歷經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直至新中國建立之前,各地商會組織基本都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內部組織結構和組織外延系統。
二、近代商會商事裁判權的產生、發展及運行
在我國的傳統商事交易過程中,商事糾紛的審理主要是由地方官府衙門進行,不可避免的帶有封建專職司法制度的弊端。為了滿足商事糾紛解決的需要和商事活動發展需求,清政府在頒行的《商會簡明章程》中,明確規定了商會的商事仲裁權。商會調處商事糾紛的職權明載條文,得到清政府正式承認,為地方商會合法行使商事仲裁權提供了官方法律依據。這一時期產生和發展起來地方商會在制定章程過程中,對于商會的權利均予以明確規定,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商事裁判權[2]。
根據史料記載,近代蘇州商會商事仲裁的范圍內容非常龐雜,既有債務糾紛、違約糾紛,也有票據糾紛、勞資糾紛等,且涉及地域范圍廣。蘇州商務總會將立會宗旨規定為“保護商業、啟發智識、維持公益、調息紛爭”,并且注重“理案”,具體規定了商事糾紛的內容、調處辦法等相關內容。從商事仲裁的人員保障上,蘇州商務總會設有專職的理事員、談判員等職,專門從事商事糾紛仲裁活動,保證了商會商事仲裁活動的有效開展。蘇州總商會為便于理案,更好地進行商事裁判,成立了專門的商事裁判機構——理案處。商會理案繼承了中國民間“調處息訟”的傳統,但是實際上已具有某種民間法庭的性質,在組織形式和程序上開始接近現代社會中的商事仲裁制度。在早期的“理案”方式上,晚清蘇州商會并沒有設立評議處、公斷處、商事裁判所之類的機構,而是遴選若干名正直、公正的理案議董,在商會召開常會期間負責處理各類商事糾紛[3]。1913年,蘇州商會正式設立專門處理商事糾紛的商事公斷處,提高了調處糾紛的效率。
三、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的政府管制與協作
近代蘇州商會是在清政府矛盾焦慮的心理作用下產生和發展的,必然決定了官方既想發展商會、賦予其更多權利,更有利于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又擔心其發展失控,嚴加管制。商會雖然屬于民間社會組織,其權力尤其是商事裁判權都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于商會具有扎實的社會土壤,以商人階層為基礎,服務于民間的商事活動,通過商事交易規則與商事裁判確立了社會威信,成為社會組織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一方面,清政府當初鼓勵商界創設商會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商會的力量溝通官商聯系以促進經濟發展,所以必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鼓勵商會的成立和發展。清政府受西方影響,為了發展經濟,鼓勵商人成立商會以及其他各種民間團體,并予以一定的保護,希望借助民間的商會等社會組織的力量促進經濟發展。所以,對于商會的設立及其仲裁權的行使,官方給予了充分的支持,具體到商事公斷處處理商事糾紛的過程,官方司法組織與商事公斷處是互相合作與依賴的關系。
另一方面,清政府害怕商會等社會團體發展壯大,成為獨立的社會控制力量,對政府管理產生干擾和威脅,對商會權限始終心存戒備,制定了《商會簡明章程》等法律規范,建立了相對較為嚴格的商會管制體系,對商會活動、商會內部組織治理、商會職能及商事仲裁范圍等進行嚴密規制。清政府之所以設置這樣一套相當繁瑣的多重審核程序,是為了防止商會的商事自治活動和管理活動侵犯地方官府的行政權力,歸根到底是害怕商會的發展壯大對其統治產生威脅。盡管這一時期清政府一直對商會調處商事糾紛表示出強烈的戒心,這段時期恰好是商會商事仲裁功能發揮最為充分的時期。
四、商事裁判權的行使促進當時商事活動的發展
處理商人之間的各種糾紛是蘇州商會的主要活動之一。近代蘇州商會自其產生之日,便著力于有效解決各類商事糾紛,并且頗有成效。據檔案記載,蘇州商務總會自光緒31年(1905年)1月成立至次年2月,共受理各種商事糾紛約達70余起,順利結案的占70%以上,遷延未結而糾訟于官府的不到30%;從成立到宣統三年(1911年)8月受理的訟案多達380余起。商會商事仲裁活動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地方官府衙門審理商事糾紛;同時,商會所具有的“理案”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完全等同于傳統的民間調處息訟,由商會受理的案件均與商務有關,最多的是錢債糾紛案,即欠債、卷逃等,約占其中的70%。蘇州商會專門制定理案章程,配備專門人員,公布仲裁程序,大大提高了商事糾紛的解決效率[4]。
蘇州商會商事仲裁功能的有效發揮,促進了當地商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政府法律不完善、社會動蕩紛爭的特定歷史時期,商會商事仲裁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商事慣例,在商人群體中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一方面,促進了地方商會的發展,結構日益完善,增強了商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加強了商會自身的組織建設;另一方面,商事糾紛的解決,維護了商戶權益,維持了交易秩序,且較之官方途徑解決糾紛方便快捷,維持了正常的商事交易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五、商會輿論的有利擴張加強了商會的商事裁判權
作為一種社會團體,商會最主要的功能即在于規范會員的經營行為以維護正常的商業秩序,而商事裁判權的行使正是這一功能的集中體現。商事糾紛發生后,官方組織允許雙方當事人到商會的商事公斷處請求解決。如果商事糾紛的當事人直接謀求官方司法組織解決,往往也會首先將案件移送到商會的公斷處。特別是在官方的案件審理過程中,非常尊重和信賴商會公斷處的案件處理結果。官方組織對蘇州商會理案的認可有利于商會輿論的不斷擴張。商會輿論的擴張,不僅加強了商會自身的建設,章程內容的完善,組織機構的構建,同時在商事活動領域的有效裁判,樹立了商事裁判的威信,進一步加強了商會的商事裁判權的行使[5]。
清末的商會組織一般被認為是商辦民間社團組織,具有“官督商辦”的性質特點,主要是商會的自身運作,而官方則是間接的監督。晚清政府對于商會的最大支持當屬對商會自治權能的肯定和維護。這一時期的商會組織通過其有效、專業的商事仲裁活動,逐步確立了其民間組織的社會地位,受到社會的認可。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王朝,1912年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的成立及聯合會報的刊行為商會加強商事裁判權的輿論表達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近代蘇州商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擴張其權限職能,除了商事活動本身,還涉及到政治、地方自治以及社會公益等諸多方面,大大提高了商人在當地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
六、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的歷史反思
商事仲裁的產生源于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經濟土壤。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動蕩不安的社會狀態中,這一時期的蘇州商會及其商事裁判權的行使不可避免的被打上時代的烙印。近代中國商會商事仲裁機構的演進同商會自身的發展密不可分,仲裁機構的發展也是商會自身組織建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近代蘇州商會商事仲裁機構發展的歷史,一方面,商會商事仲裁權的行使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產物,推動了當時社會商事交易和商事活動的發展。根據蘇州商事公斷處的理案概況可知,在商事調處中商事公斷處非常有效,專業的商事仲裁人員運用商事慣例、規則解決糾紛,容易形成雙方都較為滿意的裁判結果。另一方面,盡管歷經政權更迭,商會商事仲裁權的行使始終受制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府管制。盡管商事公斷處社會評價很高,但是終究不是正式的商事裁判。作為區域性行業組織,帶有明顯的地區色彩,主要也是解決本地商戶之間的沖突,且與當地的地方政府管制寬松程度密切相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大背景下,商會自身發展和運行都處于風雨飄搖中,商事交易也經常受到戰亂等影響。不同時期的政府對商會管制政策也存在較多差異,影響了商事裁判權的行使。只有進入穩定的社會發展時期,商事活動才能正常、有序、順利的開展,商事裁判制度才能不斷完善和進步。
七、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對我國新常態經濟運行的啟示
近代蘇州商會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留下了很多值得當代商會發展學習和借鑒的經驗。
1.必須重視商會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現代商會的功能和作用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商事糾紛也主要由專業的仲裁機構進行或者法院審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現代商會在地方經濟發展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聯系政府、企業、市場之間的橋梁紐帶,商會和政府部門仍需要緊密合作。
2.必須構建經濟新常態商會新型管理體制
商會的實質是一種組織化的“私序”,隨著商會與行政機構脫鉤,商會的管理體制面臨再造,但是其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功能并未改變,政府主管部門應積極引導商會重新構建新型管理體制,加強商會的工作透明度和社會公信力,更好的服務社會經濟發展。
3.必須重視“互聯網+”時代商會輿論引導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給我國商會的發展帶來了機遇,通過互連網絡平臺實現商會的品牌傳播和影響力提升,是商會經濟價值的重要體現。然而,信息網絡亦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對商會的網絡活動不加規制,任由發展,則可能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后果不堪設想。信息經濟時代,網路輿論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高地。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加強對商會的網絡輿情監控。
4.必須重視商會機構運行機制的構建與完善
經濟新常態下,要保證商會的良好運行,必須配備專業化的人員隊伍,開發提供品牌性服務項目,實行市場化的運營管理模式。商會機構必須加強自身管理、機構建設,實行轉型發展,提升服務能力、行業凝聚力和社會公信力[6],引領區域經濟和行業產業發展思路,為國家的經濟新常態作出貢獻。
[1]朱英.清末民初國家對社會的扶植、限制及其影響——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新型互動關系系列研究之一[J].天津社會科學,1998(06):59-67.
[2]宮寶芝.扶持與管制并行:晚清中國商會發展策略[J].貴州社會科學,2014(09):126-130.
[3]任云蘭.論近代中國商會的商事仲裁功能[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04):117-124.
[4]付海晏.民初商事公斷處:商事裁判與調處——以蘇州商事公斷處為個案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1:11-17.
[5]付海晏.民初商會輿論的表達與實踐——立足于商事裁判權的歷史研究[J].開放時代,2002(05):106-114.
[6]高成運.商事裁判與商會—論晚清蘇州商事糾紛的調處[J].社會治理,2016(01):106-110.
周德軍(1978~),男,江蘇阜寧人,江蘇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法學、社會組織。
宮寶芝(1972~),女,天津人,江蘇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學、商會法律制度。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近代蘇州商會商事裁判權探析”(12YJC82002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