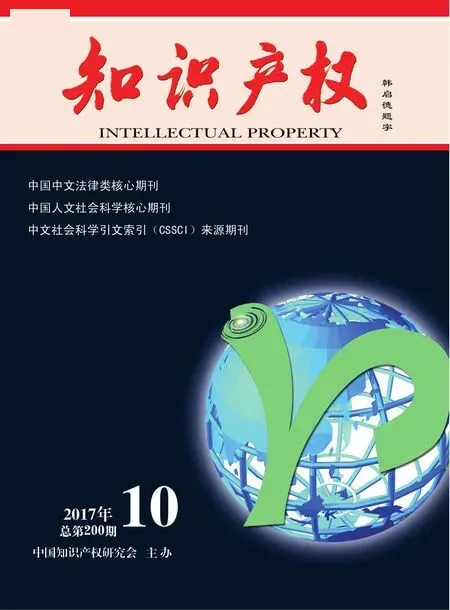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存問題分析與完善
曾粵興 魏思婧
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存問題分析與完善
曾粵興 魏思婧
知識產權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法律針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定罪標準也呈現出逐漸降低的趨勢。在此過程中,我國刑罰制度的嚴厲度卻在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產生的概率依然較高,知識產權刑法犯罪的嚴重性不斷加重。這一變化現象表明,隨著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日漸多樣化,僅僅依靠刑罰手段難以對其進行嚴厲打擊和規制;相反,要想進一步完善現階段我國知識產權刑罰保護法律制度、體系,應逐步協調和統一當前我國民法與刑法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認定結果,從而優化知識產權犯罪刑法結構,確保刑法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法律打擊的“高壓化”和“常態化”。在此基礎上,完善現階段我國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銜接機制。
知識產權 刑法保護 知識產權侵權
前 言
知識經濟時代,保護知識產權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盡管各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等各不相同,知識產權立法與規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方式存在很大差異,但采用刑罰手段對知識產權行為進行打擊與懲處已成為普遍趨勢。中國是文化大國,隨著法治化時代來臨,我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將結合實際,通過對目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存問題進行深入剖析,據此提出針對性的完善與改進建議,以期推動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工作進一步步入規范化、法治化和常態化階段。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存問題分析
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工作已運行三十多年,這一過程既是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不斷借鑒、比較、完善和修訂的過程,更是全面總結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司法經驗,并與國際公約接軌,推動國內知識產權刑法逐步國際化的過程。“互聯網+”知識經濟時代的繁榮,使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工作面臨巨大挑戰。與傳統時代知識產權相比,互聯網時代下的知識產權不再單純依賴物質載體。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我國公民更容易獲悉知識產權。在此過程中,網絡技術不斷發展,導致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形式和手段更加復雜化與多樣化,且損害難以控制,成本更為低廉。面對近年來不斷出現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我國刑法對此類刑事犯罪事件的規制顯得捉襟見肘。故適時審視現階段我國刑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缺陷已成為當務之急。總體來看,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存問題的產生,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刑法》本身的條文設置存在缺陷;二是互聯網環境的變遷和網絡技術的發達對刑法嚴肅性與完善性造成了強烈沖擊。
(一)保護范圍過窄
目前,在國際上影響最大的知識產權分類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1967年7月14日由斯德哥爾摩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中提出的分類法①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爾摩《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第2條第9項規定, 知識產權主要包括以下權利:1)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有關的權利;2)表演藝術家、錄音和廣播節目有關的權利;3)在人類一切活動領域中的發明有關的權利;4)科學發現有關的權利;5)工業品外觀設計有關的權利;6)商標、服務標記及商號名稱和標志有關的權利;7)反不正當競爭;8)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于智力活動而產生的一切其他權利。這里的定義就比較寬泛, 特別是最后第(8)項具有“兜底條款”的特點, 幾乎將一切智慧財產包括在其中。;另外一種是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中提出的分類方法。我國則通過《民法總則》設立專節對知識產權進行列舉并頒布單行法;與此同時,對主要類型的知識產權進行規定,其主要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包括計算機軟件)、商標權與廠商名稱權、產品標記或原產地名稱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發現權、發明權、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法益(包括商業秘密)還有其它科技成果權②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即《TRIPS協議》)中,知識產權主要包括以下權利:1)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即鄰接權);2)商標權;3)地理標記權;4)工業品外觀設計權;5)專利權;6)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7)未公開的信息(商業秘密);8)對許可合同中限制競爭行為的控制。這種列舉,較為明確,主要是側重與貿易相關的部分。。但《刑法》第三章第七節內容分別將“侵犯商業秘密罪”“假冒注冊商標罪”“假冒專利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非法制造商標標識罪”“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七個罪名納入其中,主要用來保護相關主體的商業秘密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商標權。因此,從部門法與刑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立法實踐的差異中可以看出,為了構建完整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法律體系,對不同法律之間的規定進行統一,促進刑法與具有刑法保護規定條款的相關法律法規之間實現良好銜接,已成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③我國也出現了一些新型知識產權權利類型。新型權利形態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對智力成果認同的不斷深化而層出不窮,例如:商品化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基因與轉基因專利權、傳統知識保護權、創意權等。。
(二)罪狀單一
現存《刑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罪狀單一。以我國《刑法》第217條為例,該法條針對著作復制權、美術作品署名權和著作發行權等內容的保護作了明確規定。但在《著作權法》第10條中法律明文規定,著作權人依法享有復制權、發行權等17項權利。由此不難看出,《著作權法》中提出的17項權利只有3項權利在現存《刑法》中受到合理保護。另外,刑法在描述著作權侵權罪狀的犯罪構成要件時并不合理。刑法指出,著作權侵權犯罪性質屬于“目的犯”,因此構成著作權侵權犯罪的要件之一是行為人必須以營利為犯罪目的。
與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于1998年頒布實施)及《反電子盜竊法》(于1997年頒布并實施)兩部法律對著作權侵權刑法規制法律依據相比,中、美兩國顯然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大差異。上述兩部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定犯罪主體構成著作權侵權的主觀要件不以“牟利”為目的。由此可見,《美國刑法》對著作權保護范圍更大。
此外,通過《TRIPS協議》與我國《著作權法》的比較可以看出,在認定侵犯著作權行為立法上,我國《著作權法》已同《TRIPS協議》保持一致。但《刑法》與《著作權法》之間卻明顯不協調,罪狀單一,難以對著作權起到應有保護作用,由此折射出我國現行《刑法》的不完整性與滯后性,而加強刑事打擊力度并非意味著要制定“嚴刑峻法”,更應該著眼于知識產權保護法是否能夠得到有效執行,打擊是否有力,若法條嚴苛則實際執行不力,既起不到法律震懾作用,同時也會對法律尊嚴產生影響。在此背景下,就會相繼出現一系列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如為了非法牟利而產生的盜播電視、電影節目或體育賽事及開設網絡零售店傳播他人作品以及非法復制、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行為等,使網絡知識產權侵權犯罪形態更加多樣。
(三)刑罰配置不合理
我國《刑法》表明,“單處罰金刑”和“自由刑并處”是打擊和懲處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主要刑罰手段之一。但事實上,該法律在刑罰具體配置方面卻尚未充分體現刑罰手段對知識產權侵權的預防作用。縱觀歐美發達國家,其在打擊或懲處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時,主要采用的刑罰手段是資格刑輔以罰金刑。通過剝奪或限制行為人的相關侵權行為,禁止其繼續在市場中對相關知識產權產品進行銷售或生產。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對于國內知識產權刑罰保護工作而言,要想充分發揮刑罰的預防作用,必須借鑒歐美國家實施的“適用資格刑”。盡管在現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九)》中法律為了起到刑罰預防作用,將“從業禁止”應用到知識產權犯罪預防中,但由于我國《刑法》對知識產權侵權犯罪的刑罰配置欠合理,所采用的附加刑依然為罰金刑。而僅僅通過罰金刑難以達到預防知識產權侵權的目的。
(四)“互聯網+”使刑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真空化”
除了傳統知識產權領域中的《刑法》存在立法和司法缺陷外,在互聯網技術環境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更加多樣。因此,為立法規制工作帶來了巨大挑戰。“互聯網+”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侵權犯罪隱蔽性強、犯罪數額難以認定、犯罪形式日漸多樣,導致現行刑法對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的懲治顯得捉襟見肘。另外,在復雜的互聯網環境下,網絡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認定和處置等立法與司法實踐情形有時異常混亂。以全國著名的著作權侵權案——“網絡鏈接型刑事”④參見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2013)普刑(知)初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書。案件為例,透過該案例司法實踐過程,可全面看到現階段我國針對網絡知識產權司法認定的混亂局面。在本案中,案件分歧之一在于“加框鏈接他人影視作品”能否被納入《著作權》法中的“復制發行”罪名中,而該侵權行為能否被《刑法》所規制,這一問題備受學界人士質疑。
二、互聯網背景下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建議
從上述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及知識經濟時代,僅僅采用傳統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難以對網絡生態時代下的復雜互聯網知識產權侵權刑事案件進行科學處理。要想使知識產權得到全面、應有的刑法保護,必須正視我國現行刑法條文本身存在的法律缺陷,正確協調與處理互聯網時代下刑法與各部門法之間關于知識侵權行為所呈現出的新特征。
(一)擴大刑法保護范圍,協調刑法與部門法關系
一方面,針對我國《刑法》與部門法之間的關系不協調、《刑法》保護范圍過窄問題,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應適當循序漸進對我國當前《刑法》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進行擴充,正確協調《刑法》與部門法關系,以《刑法》為主體,構建一套完整、系統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體系。建立執法資源的共享機制,形成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等法律為統率的打擊知識產權犯罪的合力,以防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進一步惡化為知識產權犯罪,維持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的常態化與高壓態勢。
另一方面,構建起完善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體系后,還要客觀看待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的合理保護問題。本文認為,加大刑法保護力度并不意味著所有知識產權失去了應有的傳播與合理利用空間。因“互聯網+”時代下的知識產權具有合理性與創新性。所以,不能將所有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都認定為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在此視角下,必須客觀看待知識產權的保護“度”,一旦《刑法》對知識產權保護過“度”,則會影響我國知識產權創新及阻礙市場競爭、擾亂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運作秩序。所以,構建統一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體系后,還要有效確定知識產權《刑法》保護與約束邊界,既要有效規制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又要充分促進知識產權創新。
(二)進一步完善刑法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
在傳統知識產權刑法保護視角下,罪狀過于單一,司法機關并不能有效運用刑法妥善解決知識產權侵權問題,且在描述知識產權侵權具體罪狀時,劃定“罪”與“非罪”的標準為“行為人是否以營利為目的”;而在互聯網環境下所發生的部分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并非帶有營利性目的,但這一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卻明顯與“以營利為目的”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帶來的社會危害性相當。因我國刑法尚未對該行為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從而導致網絡知識產權保護出現“真空”現象。
對此,要對我國《刑法》知識產權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進行重新審視;同時,在罪狀描述過程中,需合理取舍“以營利為目的”這一知識產權侵權犯罪主觀構成要件。為了使互聯網背景下的網絡知識產權得到合理保護,要適當舍去知識產權犯罪目的。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提升我國刑法對互聯網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效率,要合理對當前《刑法》立法、司法解釋和實踐作相應的調整與補充。比如,在完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法》罪狀時,不能罔顧“刑法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線”的法律底線,而要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打擊與懲治限度進行合理把控。互聯網時代盡管有諸多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且其具有“以營利為目的”的特征。但是,在對其量刑時,因犯罪數額標準無法確定,因此難以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人進行合理量刑。在對互聯網時代“以非營利為目的”的知識產權侵權性質進行判定時,在《刑法》定性標準中可適當加入“網頁瀏覽量”“下載次數”“點擊鏈接次數”等,以此為合理保護網絡知識產權設定具體量化標準,以防知識產權被“過度”保護。
(三)優化與調整刑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刑罰”結構
馬克昌教授曾在其《刑法》理論體系中指出,“現有立法未能及時跟進和刑事司法同行政執法、民事司法銜接不暢,都會導致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出現。⑤馬克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演進》,載《法學家》2008年第5期,第67-70頁。從中反映了當前互聯網背景下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頻發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罰配置結構不合理,而非刑罰配置力度不夠,由此導致刑罰未能及時、充分發揮刑罰對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的懲罰與預防作用。
盡管我國《刑法》一再降低著作權侵權犯罪入罪門檻,但近年來我國著作權被侵權的刑事糾紛案件數量依然在不斷上升。這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刑法》對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的打擊與懲治不在于刑罰有多重,而是在于刑罰結構配置是否合理,及能否有效對犯罪行為人起到明顯的法律震懾作用。基于此視角考量,本文認為要從三個方面對我國現行《刑法》的“刑罰”結構進行合理優化、調整。
首先,要對不同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罪名之間的法定刑刑期作適當平衡。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法律體系主要以專利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著作權法以及系列司法解釋中的刑法保護規定為補充,以刑法為主體,但在這一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法律體系中,不同法律對同一侵權行為在規定上都會存在不一致情形,不僅難以體現知識產權立法的嚴肅性,也容易給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帶來困擾。如《刑法》第216條關于“假冒偽劣”行為的規定與《專利法》第63條所述刑民糾結問題,還有相關司法解釋及《著作權》法中關于侵犯著作權行為之“發行”的規定均存在不明晰、不一致情況。因此,在知識產權領域,要平等對待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等法定權利。但透過我國現有《刑法》的法定刑期來看,著作權侵權、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的法定刑期均為7年,而假冒專利罪卻只有3年,由此可以看出現存《刑法》在不同知識產權罪名之間的法定刑刑期規定方面并不平衡,據此要科學設置不同侵犯知識產權罪名的法定刑刑期。
其次,要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司法實踐過程中合理引入“從業禁止”司法條文,或設置相應的資格刑。由于當前《刑法》中設置的資格刑并不適用于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侵權犯罪的刑罰要求。因此,為了進一步減少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數量,在刑罰設置中可參照國外刑法加入資格刑,以此全面限制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人在入罪后從事相關知識產權領域的工作;同時,可適當參考我國現行《刑法修正案(九)》中所提出的“從業禁止”條款,妥善處理互聯網時代出現的知識產權侵權刑事案件。
此外,還要對我國《刑法》中罰金刑的懲罰力度加以適當調節。通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現階段我國《刑法》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罰金刑懲罰力度明顯不足,從而易導致犯罪行為人在被執行罰金刑后,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其依然會繼續實施相應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按張明楷教授提出的觀點,“對于重復性知識產權刑事犯罪行為,可大量采用罰金刑,并引入懲罰性罰金制,使犯罪行為人從根本上失去再犯能力,同時感受到巨大的物質壓力,自覺或自發抑制其知識產權再犯行為發生”⑥張明楷:《刑事司法改革的斷片思考》,載《現代法學》2014年第2期,第3-19頁。。實踐表明,《刑法》在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進行罰金刑懲處時,適當加大罰金懲處力度能夠起到良好的預防效果,但需要注意罰金刑懲罰力度要在“法所容許”范圍內。
(四)遵從“罪刑法定”原則,適應“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犯罪形勢
互聯網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與傳統法律環境下的侵權行為存在本質差異。在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侵權犯罪行為具有虛擬性特征。因此,需針對“復制發行”這一侵權行為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同時,在刑法規制中,應科學認定侵權犯罪行為是屬于幫助犯還是正犯。基于我國現行《刑法》的“謙抑性”實踐原則,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人實施的新型犯罪行為進行入罪解釋時,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正如高銘暄教授所言,“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全新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正在發生,當無法通過司法解釋解決知識產權領域的侵權問題時,相關立法機關應積極介入法律制度創新實踐中,通過知識產權侵權新罪名的增設,推動入罪化,以防刑事立法滯后”⑦高銘暄、陳冉:《論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刑事法治問題》,載《中國法學》2012年第2期,第54–66頁。。聯系葉曉明等訴訟索佳公司技術成果權侵害案⑧一審判決,參見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1〕武知初字第37號;二審判決,參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2〕鄂民三終字第6號。不難發現,法官判決在保護葉曉明等人基本權利基礎上,不失社會公正,以侵權責任為落腳點,首先對葉曉明等人的發現是否屬于商業秘密進行了認定,第二種裁判思路是以合同契約義務為基礎,進一步確定了法律關系當事人之間具有保密關系,并賦予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對商業秘密、保密信息以默示合同義務,以合同視角來看,梳理整個案情,從事件發生之初,由葉曉明等發出邀請,索佳公司應邀前來洽談,雙方磋商、談判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與接受技術咨詢服務,在磋商中,雙方并雖并未簽訂技術咨詢合同,但葉曉明等通過檢測方法進行演示,告知了索佳公司SOKKIA100系列全站儀具有設計錯誤,并提出了問題解決方案。其實這一過程已經向索佳公司提供了技術咨詢,只是對方尚未支付咨詢報酬,因此按照《合同法》第357條和第358條規定,索佳公司屬于不當得利。
從這一技術成果侵害案判決思路中可以發現,在葉曉明等訴訟索佳公司技術成果侵害案件中,二審法院承認了上訴人葉曉明等的科技成果權利,并確定為“技術秘密”,二審法院考慮到財產權設計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公平價值目標及上訴人葉曉明等與被上訴人索佳公司進行談判本身就是為了提供一種技術咨詢服務,其適用《民法》及我國《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其由此表明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初衷本身就是為了找到一種恰當的智慧勞動成果保護路徑。換言之,即使在知識產權權利類型中無法找到一種恰當的保護路徑,也可在知識產權法之外尋求一種法律保護方式,以實現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要旨。事實上,知識產權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財產權觀念,其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人格意義。更進一步言之,知識產權具有私權根本屬性,其本身就是一項民事權利,也是我國民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應地,在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方面,要試圖尋求一種知識產權法之外的法律保護方式,遵從“罪刑法定”原則,適應“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犯罪形勢,以實現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為宗旨,突出知識產權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財產權觀念及人格意義。
結 語
綜上所述,互聯網背景下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多樣化特征,由此導致刑法對互聯網知識產權侵權犯罪行為的刑罰規制具有法律局限性與滯后性。本文通過對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實踐中存在的保護范圍過窄、罪狀單一、刑罰配置不合理,及“互聯網+”使我國《刑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真空化”幾大主要問題進行剖析后,發現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司法實踐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均存在較大差距,不僅各部門法與刑法之間不協調,且網絡知識產權侵犯犯罪罪狀、刑罰結構配置、司法解釋和實踐等均無法應對互聯網時代相關知識產權侵權難題。對此,通過分析認為,要從四個方面進一步完善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規制體系,一是擴大刑法保護范圍,協調刑法與部門法之間的關系;二是要進一步完善刑法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三是要優化與調整刑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刑罰”結構;四是要遵從“罪刑法定”原則,適應“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犯罪形勢,以此推動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工作步入“常態化”和“高壓化”狀態。
IP la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legal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standard for incriminating IP criminal behavior is lessening. Meanwhile, the severity of the penalty system has increased.The ratio for IP infringement is still high, yet the severity for IP criminal behavior has been increasing. This phenomenon indicates that Criminal Law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to regulate and crack down the diversified IP infringement behaviors. To improve China’s IP protection by Criminal Law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IP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results by both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whereby to optimize the IP criminal law structure and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IP by the Criminal Law in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 efforts, the paper suggests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of Criminal Law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in current sta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IP infringement
曾粵興,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魏思婧,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