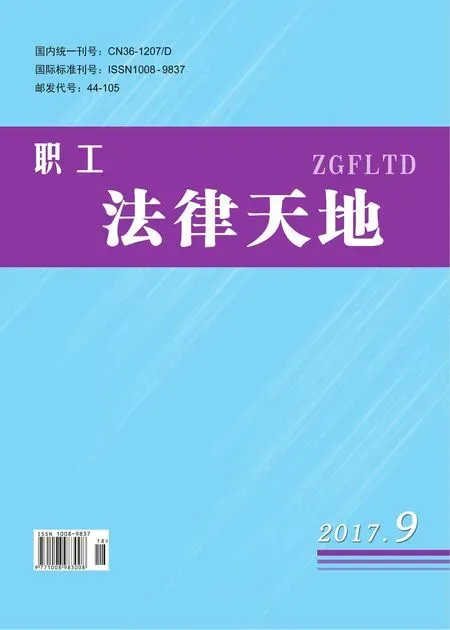詐騙犯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認定
許 奕
(362000 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 福建 泉州)
詐騙犯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認定
許 奕
(362000 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 福建 泉州)
長期以來,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對詐騙犯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未做明確的規定和解釋,而“非法占有”的形式多種多樣,在不同罪名中的表現形態也不盡相同。種種原因,使得司法實踐中對詐騙犯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認定一直困擾著司法人員。本文就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詐騙犯罪中的存在
刑法中共有十種詐騙犯罪,明確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罪名僅有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也僅在惡意透支的情形下規定了持卡人要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許多國家,這也是刑事立法的通例。如德國的刑法典規定,詐騙罪需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當得利之意圖”,英國1968年頒布的《盜竊罪法》第15條也規定,構成詐騙罪,必須具有“永遠剝奪他人對財產的所有權的意圖”。在法理上,詐騙犯罪屬于刑法理論中的目的犯。目的犯是指以特定目的作為主觀構成要件的犯罪。[1]
由此可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詐騙犯罪不成文的主觀要件。
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詐騙犯罪中的內涵
“非法”二字,從字面的解釋來看,就是不合法,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或者處于法律沒有規定的范疇。從保護法益的角度理解,侵害財產罪所保護的法益的行為即為“非法”。一般說來,行為人沒有占有他人財產的合法根據,或者說沒有使他人轉移財產給行為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根據,卻具有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就屬于非法占有目的。[2]“非法占有”在民法上有善意占有和惡意占有之分。[3]法律保護善意第三人,也保護善意占有。而在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就有所不同,其排除了善意占有,是特指惡意占有。
有的觀點認為,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是排除權利人對財物所有權的行為,表現為排除權利人對財產的合力控制,并以此為前提排除權利人對財產進行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從而實際剝奪權利人對財產的所有權。[4]還有的觀點認為,刑法上的“占有”包括了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能。因為詐騙行為人不僅僅是謀求“占有”公私財物,更主要的是使用、處分或利用該財物收益。僅是“占有”而不去使用、收益、處分,這種詐騙對行為人毫無意義,行為人絕不會甘冒觸犯刑律、遭受刑罰處罰的危險區實施僅以“占有”為目的的詐騙。
筆者認為,詐騙犯罪中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就是指行為人意圖排除財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與人),將他人財物作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實上的支配權的意思。
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詐騙犯罪中的認定
如果說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內涵的理解尚無統一定論,那么,在實踐中對它的認定就更為困難。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雖然是內心活動,但是人的內心活動難免會外化于行,認真分析是可以被感知的。因此,我們可以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精神及行為人的客觀表現,通過刑事推定的方法回溯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根據客觀事實判斷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存在。
首先,對全案證據進行仔細梳理。一是梳理行為人的口供,判斷其合理性。二是梳理除行為人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張明楷教授曾說:“我國的司法機關一直過分強調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困難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司法機關長期以來過于相信和依賴被告人口供,不善于根據客觀事實判斷被告人的主觀內容。當根據客觀事實得出的結論與被告人的供述不一致時,司法工作人員便陷入苦惱之中。”
其次,結合生活常識、經驗法則、邏輯以及《紀要》列舉的七種情形,從以下幾方面綜合考慮:
(1)行為人在實施詐騙行為前中后的經濟狀況和履約能力。如果行為人在詐騙前經濟窘迫,又以隱瞞真相或虛構事實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應當認定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其在實施詐騙時及詐騙后,經濟狀況有了無緣由的明顯改善,且與詐騙數額相符,又或詐騙后經濟狀況良好卻拒不返還,這些情況都與認定是否非法占有的目的密切相關,應當查清。
(2)行為人獲取財物后的去向。一般認為,行為人若攜財物潛逃,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也存在例外。如被害人行為過激,行為人為自保暫時離開,致被害人無法聯系,同時積極籌集款項賠償被害人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不宜輕易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又如,行為人雖未逃匿,但開始轉移資金、隱匿財產、或者搞假倒閉、假破產,以逃避返還財物,這樣的行為就應當認定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不能僅憑行為人逃匿就當然視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能因行為人沒有逃匿就當然否定其非法占有的故意,應慎重考量,不枉不縱。
(3)行為人對財物的處分。如果行為人獲取財物后肆意揮霍,可以結合其他證據予以認定。但這方面情況的取證存在一定的困難,若行為人不予配合,偵查機關難以找到明確方向收集有效證據。
(4)行為人事發后的表現。行為人有無還款的意愿和行動,意愿和行動需結合在一起考量。在司法實踐中,曾出現行為人在無還款能力的前提下,口頭或者書面達成還款意愿,或者先暫時償還一小部分款項,實為達到穩住被害人,阻止其報案,逃避刑事制裁的目的。要加以區分主動履行和被動退贓的差別。在司法實踐中,曾出現這樣的案例,行為人迫于被害人的壓力,償還了一部分錢款后,隨后又逃匿,其律師以行為人有償還部分款項主張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這顯然不是主動履行償還義務,而是為之后的逃匿打掩護,因此,最終判決認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再次,充分聽取行為人的辯解和反駁。如果行為人提供的證據和反駁更有合理性,可以推翻推定的事實,甚至僅僅是行為人提供的證據證明其反駁存在的可能性超過了推定事實存在的可能性,案件事實存疑的狀態下,也可以認定推定的事實不成立。
最后,縱觀全案,得出推定的結論。如果刑事推定的結論沒有充足的證據可以證明,存在不成立的可能,則應當認定行為人無罪。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作為一種主觀要素,其自身具有難以把握性,再加上紛繁復雜的案件事實,不夠完善的認定標準,給審判造成了一定的困惑。面對這樣的難題,法官應當立足于法律與事實,準確把握“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內涵,運用善良的感知和一般的社會經驗法則,作出正確的判斷。
[1]張明楷.《論詐騙罪的欺騙行為》,《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第13頁.
[2]陳興良.《論財產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第69頁.
[3]曾憲義.《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招生考試教程(下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頁.
[4]儲槐植,梁根林.《貪污罪論要》,《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