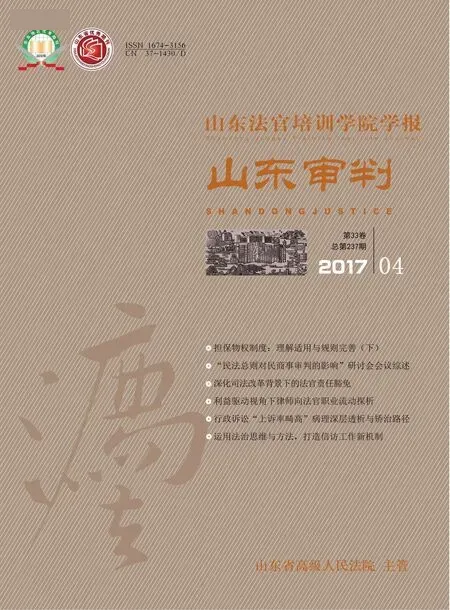擔保物權制度:理解適用與規則完善(下)
●劉保玉
擔保物權制度:理解適用與規則完善(下)
●劉保玉*
六、關于質權、留置權的行使有無訴訟時效適用的問題
這個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表述為關于權利質權的行使期間及動產出質人、留置物所有人請求返還財產的訴訟時效問題。
《擔保法》中對抵押權和其他擔保物權行使的期間問題沒有規定。《擔保法解釋》12條第2款借鑒其他國家、地區的做法,側重于擔保物權的獨立性,規定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訴訟時效結束后,擔保權人在訴訟時效結束后2年內行使擔保物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物權法》則側重于抵押權對其擔保的債權的從屬性,并且考慮到促使抵押權人積極行使權利和便利物上保證人清償債務后行使追償權的需要,于第202條規定,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抵押權,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該條規定在表述上所使用的“……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接近司法解釋規定,而不太符合法律條文的表述方式。在理解、適用上存在的問題是:抵押權人未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內行使抵押權,抵押權是否消滅?出現超過時效這樣的問題后,抵押人向抵押權人提出主張,要求抵押權人配合自己辦理抵押權注銷登記,則抵押權人通常不會配合辦理,那么,抵押人能否自己去辦理注銷登記?作為登記機構的人員,往往不會協助辦理,因為這樣做沒有法律上的依據,風險也會很大。如果抵押人訴諸法院要求判決抵押權消滅,抵押人可以申請注銷登記,法院會支持嗎?不無疑問。但我查到的判例,有法院判決支持抵押人的主張。個人認為,依據現有的規定,不能理解為抵押權存在訴訟時效期間,即抵押權沒有訴訟時效問題,它只是一個行使權利的期間,或稱作失權期間,作用類似于除斥期間,只是該期間附隨于主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而已,該期間經過的法律后果就是抵押權消滅。
上面是對抵押權行使期間規定的理解問題,接下來的問題是,質權、留置權有無訴訟時效或行使的期間問題,以及《擔保法解釋》12條第2款的規定是否在質權、留置權問題上能夠繼續適用?立法本意應該是廢止了《擔保法解釋》12條第2款的規定。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債務到期未能清償的,出質人可以催告質權人及時行使質權。質權人未及時行使質權,導致質物價值貶損造成損失的,質權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留置權同樣如此,債務到期未能清償的,留置物的所有權人可以催告債權人及時行使留置權。留置權人未及時行使留置權,導致留置物價值貶損造成損失的,留置權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問題是,這樣的規定就能徹底解決問題了嗎?比如存在這樣的情況:債務人借50萬,以古玩花瓶作為質押。債務到期后未能清償,債權人要求直接以花瓶抵債。出質人也認可這樣的做法。三年后,花瓶的價值發生了重大變化,價值100萬。出質人現在要求將多出的價額退還。這樣的情況下有無訴訟時效的問題?這些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我的認識是:以占有標的物或其權利憑證為要件的動產質權、權利質權及留置權,對權利人而言則不應存在行使期間或訴訟時效問題(這也是國外立法例上通常采用的規則),質權人和留置權人在主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屆滿而未實行其權利也不放棄對擔保財產的占有的,應推定其意思為以擔保財產歸自己所有的方式抵償債務(擔保財產的價值如果低于債權額,因主債權已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其未受償部分的債權將不再受保護);擔保財產的所有人如果認為這種依單方意思所做的處理損害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擔保財產的價值超過債權數額),則其應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主張自己的權利,否則人民法院不予保護。依據《民法總則》第188條關于訴訟時效起算規定的精神,該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應自債務到期而債權人繼續占有擔保財產開始計算;擔保物權人通知擔保人以擔保財產抵償債務的,自通知之日起計算;擔保財產的所有人催告債權人及時行使權利的,可以發生時效期間中斷的效果,時效期間重新起算。我的這一認識并非虛妄,而是具有實用性且與《物權法》《民法總則》的相關規定具有契合性。根據《物權法》第220條和237條的規定,出質人可以請求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及時行使質權;質權人不行使的,出質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拍賣、變賣質押財產。出質人請求質權人及時行使質權,因質權人怠于行使權利造成損害的,由質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債務人可以請求留置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行使留置權;留置權人不行使的,債務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拍賣、變賣留置財產。那么,如果質權人、留置權人拒絕出質人、債務人的請求,則后者自然有權也有必要尋求司法救濟,而如果此后其未再主張權利或尋求司法救濟,則當然應有權利行使的訴訟時效問題。另根據《民法總則》第196條的規定,下列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一)請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二)不動產物權和登記的動產物權的權利人請求返還財產……從該條規定可以反推,未經登記的動產物權的權利人請求返還財產的,要適用訴訟時效。也就是說,出質人、留置物所有權人的物被債權人占有,不變賣也不退還,出質人、留置物所有權人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要求返還財產或者折價的,應當計算訴訟時效。所以,我的這一認識與《民法總則》的規定精神是一致的。另應注意的是,登記的特殊動產(車輛、船舶、航空器等)作為質物、留置物的,所有權人請求返還財產,不適用訴訟時效。
此外,還存在以登記設立的權利質權行使的期間問題。登記設立的權利質權是什么性質?屬于質權還是抵押權?是稱作知識產權出質還是知識產權抵押?很多學者認為,稱作什么不重要,最終的法律效果是一樣的。個人也認為,以登記方式設立的權利質權,應準用抵押權行使期間的規定。原因在于其設立方式相同,權利的性質也無實質差異,自應適用同樣的規則。
七、附物權擔保的債權人對債務人非擔保財產的執行選擇權問題
先舉一個事例。債務人名下有A和B兩塊土地使用權,其以A塊土地使用權向債權人設定了抵押擔保。債務到期時,債務人不能償還債務,債權人主張權利,申請執行B塊土地的使用權。債務人提出異議,要求債權人執行A塊土地使用權。這種情況,形象地說,債權人的這一做法像是“占著碗里的,先吃鍋里的”。那么,從法律上和法理上看,債務人的此一異議能否成立呢?從我搜集到的諸多案例看,法院的認識并不一致。而在學理和立法例上,也有“先行主義”和“選擇主義”兩種認識和立法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的某個案件的裁定書中認為,債權人有權選擇債務人的非抵押財產申請執行。在這個問題上,個人建議,采取限制型選擇主義的態度,原則上承認其有選擇權,但不是沒有限制。在債務人的資產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債權人可以自由行使選擇權,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應當遵從約定。在實現擔保物權的特別程序中,以及單純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時,應僅限于就擔保財產主張權利。在債務人資不抵債的情況下,應適用破產清算或者參與分配的程序,原則上不存在選擇權的適用問題。擔保人為債務人之外的第三人時,債權人無權選擇執行第三人的非擔保財產。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債權人申請執行債務人的抵押財產其是以抵押權人的身份,依據其享有抵押權,他可以就抵押財產的變價價值優先受償;而債權人申請執行的債務人的非抵押財產,就變賣的財產是不可以享受優先受償權的,因為此時債權人僅是以普通債權人的身份主張權利的。同時,享有抵押權的債權人實現債權后,抵押權就消滅了,抵押財產回歸債務人的一般責任財產之中。也就是說,附物權擔保債權人如果選擇“先吃鍋里的”,那么他吃飽了之后,“碗里的”飯食還是要倒回“鍋里的”。
還有一個可能有爭議的問題,就是如果債權人選擇執行未供作擔保的財產,而該財產對債務人有特殊的意義,比如債務人在某公司的股權,而該公司股權對債務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重大,如果執行、變賣了該股權,會直接涉及公司的控股地位的問題。在類似于這種情況下,債務人可能會提出強烈的抗議,要求其執行供作擔保的財產。這種情況下,債務人的異議或抗辯能否成立?個人認為,其抗辯依然不能成立,因為在訴訟前、訴訟中以及執行過程中,債務人有很多機會可以還債,而如果其還債了,就不會這么被動了。關于這個論題,大家有興趣的話回頭可以看我在《法學家》雜志今年第4期登出的專題文章,里面有很多細節問題的論證。
八、關于動產質押中質物的移轉占有問題
動產質押中的交付問題,初看似乎并無什么爭議。但是,實踐問題是紛繁復雜的,例如在下列一些情況下,仍可能發生認識的分歧。
第一,質權人將質物存放于出質人出租的房屋,被出質人擅自取走,能否導致質權消滅的問題。這個情況下,質權人、債權人同時是房屋的承租人,他租了債務人的房屋。但是,出質人還有房屋的鑰匙,其趁質權人不在,打開房門將質押物取走。在這個情況下,法律后果如何?個人認為,這里要區分出租房屋的性質。如果租的是住宅,承租人對租住房屋享有受法律保護的住宅權益。未經承租人許可,出租人擅自進入他人租住房屋中并將質物取走,這種行為在法律上可以定性為盜竊。這種情況不會導致質權消滅,質權人有權要求出質人將質物返還。而如果租的是債務人的倉庫,則要看債權人是否真正取得了對質物的控制,比如對倉庫的某間庫房或者某個區域有實際的控制力。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出質人仍可以自由出入庫房,甚至質物與債務人的其他財產混放在同一倉庫,則很難稱得上是移轉了占有,進而導致質權不成立。
第二,經銷汽車的4S店車輛質押的問題。經銷車輛的4S店將準備出售的車輛向銀行質押,根據實際需要,質押的車輛通常還是存放在4S店的倉庫內,目的是方便客戶選購。債權銀行會委派第三方公司監管質押的車輛,同時控制車輛的合格證。4S店賣出一輛車,應把錢款匯入銀行指定的賬戶,之后銀行會通知監管人放行該車并退還該車的合格證。這是4S店辦理車輛質押的實際需要和常見情況。問題是,這種情況下能否成立質權?這種情況相當于是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設立質權。嚴格來講,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設立質權的,質權不成立,這是立法例上的通行做法。我國《物權法》盡管對此無明確規定,但學理解釋和司法實踐也都是這樣認識的。但是,如果不承認4S店的上述做法能夠為銀行設立質權,將導致4S店無法向銀行融資或者無法經營。另外,銀行也派人進行了監管,可以認為對質物有實際控制。所以,個人認為,法律上應當限制的是單純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設立質權的情形,但質權人以適當方式控制質押財產的,無礙質權的成立。我提的具體立法建議是:“債權人許可債務人代其占有質押財產的,質權不成立,但質權人以適當方式控制質押財產、表彰質權的除外。”
第三,單純將車輛的合格證交給債權人保管或者質押,能否成立質權的問題。車輛的合格證是車輛辦理所有合法手續的必備文件,無論是進口車還是國產車,一輛車的合格證都是唯一的。那么,如果當事人約定銀行不控制車輛本身,而是以控制車輛合格證的方式設定質押擔保,質權能否成立呢。個人認為,如果僅控制車輛的合格證,而沒有控制車輛本身,則不成立車輛的質權。從法律定性上而言,債權銀行控制了合格證,只是對債權的實現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擔保。
第四,動態質押或者流動質押的問題。實踐中,在很多地域和許多行業,動態質押已經成為了一種“模式”,動態質押又稱流動質押、滾動質押等,也有人稱之為“浮動質押”,不過,浮動質押的稱謂不準確。這種做法與浮動抵押是不同的模式,不宜使用容易混淆的稱謂。動態質押的基本操作模式是將油料、煤炭、木材、鋼材等種類物質押給債權人作為擔保,通常不移轉實際占有,也是由銀行委托第三方監管。上述質押的財產如果存放時間過長,會貶值、變質,進而導致損失,對債權人、債務人都不利。這種情況下,雙方商量動態質押,比如以500噸油料作為質押擔保,存放在債務人的倉庫里,債權人派人監管,保證油庫里的油不少于500噸。油料是有保質期的,因此允許一定時間后將原來的油抽出,重新注入一批新的油替代原來的油,以保證作為質物的油料不貶值。這種情況下,質物的變化對質權有無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會存在不同的認識。一旦遇到出質人有多個債權人,當其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時候,其他債權人會說,這種行為是在規避法律,現在的質物不是原來的質物,原來的質權因質物的返還已經消滅了。通過對實踐情況的調研,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是經營實踐中的一種需要,如果在法律上不允許,將會給類似的企業融資帶來極大的不方便。這種情況,應認為無礙質權成立和存續,而且是以原質權成立的時間為準。未來,建議把動態質押寫進立法,以此更好地規范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這種融資行為和經營模式。實踐中,還有超越此類做法的情況。比如,原來質押的是一批木材,后來又以一批鋼材替代了原來的木材。這種情況下,質權是否受到影響?個人認為,這種情況可以認定為質物替代,即不斷地以新質權替代原質權。為了保證質權的有效成立,應當更換質押合同,成立新的質權。綜上,在法律上考慮這樣的問題時,要照顧到交易實踐中的實際需要,對正常的交易活動可以有所放寬。但是,對于某些近似于規避法律的做法,也不能無條件放寬。
在我參加的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物權編編纂小組擬定并提交給法工委的立法修改建議中,我對上述動產質押問題作了重點設計和說明,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一個與法國學者一起進行討論的會議上,法國學者在對我介紹中國當下存在的動態質押情況作出回應時,提到法國也有類似情況且為學界和實務界所肯定,尤其是以諸如庫存葡萄酒、香檳酒等作質押財產的情況下,需要特定的存儲條件,而唯有作為出質人的酒廠具備存儲條件。此種情況下,質押財產仍存儲于出質人的庫窖但債權人派人加以監管的,無礙質權的成立;而且,出質人也可以同類、同價值的葡萄酒、香檳酒替代原來的酒,以便在不影響質權存續的前提下保持質物的價值。
九、質物被質權人丟失,質物的價值如何推定的問題
舉一案例。出質人將一塊玉石質押給債權人,借款30萬。后來,質權人不慎將玉石丟失。設定質押時雙方都未對質物的價值進行評估,現在,客觀上無法再對質物的價值進行判定。雙方關于質物的價值發生爭議。出質人主張,玉石價值50萬。質權人主張,玉石的價值僅為1萬。這個案子里的債權額度是30萬加利息。對此,法律上如何認定玉石的價值?有學者認為,玉石的價值應當推定為1萬,主要根據是訴訟法上的證據規則。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出質人主張價值50萬,應當提出證據。沒有證據證明的,應當依據質權人自認的1萬元加以認定。反過來,質權人主張值1萬,也沒有證據證明,但起碼他沒有主張更低的數額。現在雙方都沒有證據證明到底值多少錢,有人認可了值1萬,那就按照1萬計算。依據這樣的邏輯,誰當原告誰的舉證義務較大,誰也就處于較為不利的境地。個人認為,運用推定規則時,應遵循交易的慣例和法律人在同等情況下的基本認知。在這個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強者和弱者的區別。雙方在設立質權時,都有義務對質物的價值做出一個共同認可的結論。結果,雙方都有所疏忽,沒有對質物的價值進行鑒定。依據常理來推定,作為債權人,為了保障其債權安全,都想到了要求對方提供質押擔保,自然應當能夠考慮到對質物的價值進行評估的問題,即要求對方提供價值相當的質物。這樣,推定質物的價值與債務額相當是符合常理的。另外,作為質權人,質物由其控制保管,質物丟失了責任在質權人。如果此時要求出質人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顯然也是說不通的。因此,推定質物的價值與債權額相當,還是比較公允的。
這個案例好像挺特別,但由此我們可以想到,肯定還有其他類似情況,故此,有必要將當事人未對質物的價值事先評估而事后又喪失評估條件的情況下如何推定或認定質物的價值作為一類問題來提出并加以討論。我曾把這個關于“獅子、螞蟻和石頭”案例放到民商法學者的微信群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詳情大家可以查閱《人民司法·應用》2016年第34期。大致說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同志贊同我的觀點,但也仍有不同意見。
十、預告登記抵押權的效力問題
過去的《房屋登記辦法》以及2016年國土部出臺的《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中都肯定了抵押權的預告登記。但是,實踐中也發生了很多的爭議。比如這樣一個案件:房屋的預購人將預購的商品房向銀行做了抵押權的預告登記。后來,房屋的預購人負債累累,債權人都向其主張債權。但作為債務人的預購人主要資產就只有這套房子。銀行主張,其有預購房屋的抵押權,所以就其變價價值有優先受償權。其他債權人則主張,預告登記的抵押權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即使登記了,其也不同于正式登記的抵押權,不具有優先受償的效力。這個案子實際上涉及的是房屋“按揭”買賣的效力如何認識的問題。
我們知道,我國《物權法》第20條對預告登記制度作了原則規定,主要適用于當事人簽訂買賣房屋或者其他不動產物權的協議等,但具體適用范圍并未明確。建設部2008年發布的《房屋登記辦法》第67條中規定:以預購商品房設定抵押的,當事人可以申請預告登記。這實際上是對所謂的樓宇“按揭”(mortgage)購房關系的認可。由于“按揭”并非我國法律上的術語和用語,所以在我國的法律文件及登記規則中未使用該詞語,而是以近似的“預告登記抵押權”替代。但這一替代用語,也導致了其與按揭關系的差異:在樓宇或樓花按揭中,按揭權人是有優先受償權的,而預告登記的抵押權是否含有優先受償權,則值得推敲。還應提及的是,以預購商品房等設立預告登記抵押權,在抵押人和權利性質、內容等方面均不同于在建工程抵押權,不能將其混同或相互替代,表現在:第一,在建工程抵押權的設立人(抵押人)是在建工程的所有權人(房地產開發商或建設單位),而預告登記中的抵押人則是購房人;第二,在建工程抵押權是正式登記的抵押權,而在房屋預購關系中,由于預購的房屋尚未竣工,預購人尚未取得所有權,故其欲以期權設定擔保,只能設立預告登記的抵押權;第三,在建工程抵押權具有優先受償效力,而預告登記抵押權在完成正式登記之前,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效力,尚值討論。在國土資源部2016年發布的《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85條中規定,以預購商品房設定抵押權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按照約定申請不動產預告登記。實踐中,也已大量出現這樣的案例,購房人以預購的商品房(尤其是期房)預告登記抵押權向銀行貸款,此后,由于購房人的其他債權人主張以該房屋償債,而貸款銀行主張享有抵押權和優先受償權,從而引發爭議。對此項預告登記的抵押權的性質、效力及作用如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認識均有分歧。筆者認為,《物權法》第20關于預告登記的一般規定,僅系針對“買賣房屋或者其他不動產物權”的情形而規定的,而未涉及預告登記抵押權等情形;預告登記的抵押權在可以進行正式登記時,權利人可以要求辦理正式登記且當然可享有優先受償權。但現在大量遇到的問題是,房屋建成交付時發生了爭議,甚至其他債權人申請對房屋進行了查封,此時預告登記的抵押權還能否推進到正式登記上?而如果不能推進到正式登記,預告登記的抵押權人也就是債權銀行還享有優先受償權嗎?個人認為,要考慮這個預購的房屋的價值是如何產生的?可以說,通常60%以上是借助銀行貸款產生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銀行的貸款注資,購房人即債務人根本就沒有該項財產,更何談普通債權人要求債務人以此房屋的價值清償債務。如果銀行沒有優先受償權,就意味著銀行為債務人(預購人)投資購買了房屋,但是其價值卻由預購人的所有債權人平均受償。這對銀行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法律上這樣設立規則的話,我想這樣的業務以后銀行也不會再做了,而如果銀行取締該項業務,則多少人將沒有能力買房?這就不是幾個人的問題了。但換位思考一下,銀行預告登記的抵押權畢竟不是正式登記的抵押權。正式登記的抵押權當然有優先受償效力,但銀行僅僅是一個預告登記。如果承認銀行享有優先受償權,就意味著預告登記與正式登記是一樣的,這與法律規定的精神是相違背的。這樣的案例處理起來確實很棘手,難以給出一個非常滿意的答案。從已有的判例來看,似乎多數判例對預告登記的抵押權是不承認其具有優先受償權的,但也有肯定的案例。從交易的安全、房地產市場發展的需要,還有利益衡量方面的考慮,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還是要傾向于保護銀行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在非因債權人的原因導致預告登記的抵押權不能推進到正式登記的,或者在債務人破產、資不抵債等情形下,可以作出例外規定,把預告登記的抵押權視為正式登記的抵押權。這個問題,亟待立法、司法解釋或登記規則加以規范,否則還會后患頻發。
十一、擔保物權附隨債權轉讓的問題
《擔保法》《物權法》中都規定了抵押權不得與債權相分離而單獨轉讓。債權轉讓的,抵押權附隨轉讓,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其實,質權、留置權也適用這一附隨性規則。實踐中發生了很多因債權轉讓導致抵押權附隨轉讓的情況。但是,通常沒有辦理移轉登記。在這種情形下,受讓債權的人主張對抵押財產進行優先受償,但是抵押人往往會提出抗辯,主張其并非為現在的債權人提供擔保,而是為原債權擔保,原來的那個抵押權不存在了。這種抗辯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現在,受讓債權人可以要求抵押人辦理移轉登記,這種要求是有法律依據的。抵押人不協助的,可以通過判決來確定并憑判決單方申請辦理登記。這樣做,只不過繞了個圈子而已。實踐中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是資產包、債權包的轉讓,這種情況下,一個資產包及包含于其中的債權、抵押權等往往會轉讓多次。最后一個受讓的債權人主張實現債權和抵押權,而原來的抵押人提出抗辯,怎么辦?此時,抵押權附隨債權轉讓了多次,現在要求補登記,如何補?是一筆一筆地補,還是中間環節都省略,直接補到最終的債權人名下?如果必須一筆一筆地補,前手中如果有一個債權人破產了、解散了,又怎么辦?對這種連續轉讓的債權如何辦理抵押權附隨登記,登記規則里沒有明文規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對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明確,但里面有一條規定,即登記應當貫徹連續性的原則。這是否意味著要求一筆一筆地登記,不無疑問。尚未見到權威的解讀。但如果是這樣,那會給當事人帶來重大的不便。最高法院曾經出臺過一個關于國有資產移轉中抵押登記問題的指導意見。里面講到,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接受債權轉讓,可以直接申請實現抵押權。這就意味著中間不需要一筆一筆登記。這樣的規定比較合理,可以解決實踐問題。但是,這個指導意見是針對特定的情形,沒有規定所有的債權轉讓都適用這個意見。個人認為,對于其他的債權轉讓,也不必一筆一筆登記。對于不動產的所有權的轉讓,是需要一筆一筆登記的,因為涉及到契稅的問題。而抵押權本身不涉及契稅的問題,不一筆一筆地登記,不會導致國家契稅方面的損失,也沒有增加抵押人的任何負擔。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的債權人,是否可以依據《物權法》第195條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不經訴訟直接申請實現抵押權?目前司法實踐中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比較謹慎,一般認為是不可以直接執行的。
十二、擔保物權的善意取得問題
《物權法》106條規定了物權的善意取得制度。該條第1款規定了善意取得及其條件,第2款規定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前款規定。這就意味著,除了所有權之外,用益物權、擔保物權也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實踐中有這樣的案例:夫妻共有房屋登記在一人名下,登記的權利人將該房屋抵押給第三人。登記權利人的配偶主張抵押無效,第三人則主張有效。如何處理?個人傾向于認為,應當堅持登記的公示作用和公信力,承認登記的權利人有權設定抵押權,當然,第三人須為善意方可取得抵押權。質押也是同樣,無處分權人將所占有的財產質押給債權人,債權人為善意時質權同樣有效設立。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留置權能否善意取得?根據最高法院《擔保法解釋》108條規定,債權人合法占有債務人交付的動產時,不知債務人無處分該動產的權利,債權人可以按照《擔保法》第82條的規定行使留置權。這個規定被人們通常稱為是關于“留置權善意取得”的規定。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閉門造車的錯誤規定,留置權的善意取得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以身邊例子分析。甲借乙的車外出辦事,發生刮擦事故,甲將車送到汽車修理廠修理。修理完畢后,甲未支付修理費用,此時汽車修理廠能否留置該車輛?顯然是可以留置的,即使甲事先說明是借的車并出示行駛證,也無妨修理廠行使留置權。這樣的情形下,根本無需考慮甲是否是車輛的所有權人,只要是甲送來修理的,就可以要求甲承擔相應的修理費用,因此也就無所謂善意取得問題。回到《擔保法》《物權法》里面的規定,債權人有權留置債務人的動產。這里的“債務人的動產”是什么意思?必須是債務人享有所有權的動產嗎?不一定。個人認為,對該條應當從寬解釋,“債務人的動產”應當包括債務人有所有權、有處分權以及因債務人的原因而移交占有的動產等情況。綜上,留置權沒有所謂的善意取得問題,只要符合留置權的產生要件,留置權就當然產生。
說到善意取得問題,順便再說一個發生在山東某地的關于知識產權善意取得的案例。某項專利實際發明人為甲,但是甲沒有以自己的名義登記為專利權人,而是讓他的朋友乙登記為專利權人。乙把該專利的使用權許可給第三方公司,約定許可使用十年,三年內把十年的使用費付清。現在已經過去了兩年多,受讓人幾乎把十年的使用費都付清了。乙將使用費據為己有,為此甲要求撤銷乙的專利權,申請將該項專利權重新授予自己。通過法定程序,甲重新成為專利權人后,要求第三方公司停止使用該專利。第三方公司認為,根據當時專利權證書記載,乙就是專利權人,乙許可我使用,我也交納了使用費,沒有任何過錯,所以拒絕停止使用。為此,甲起訴第三方公司侵權。個人認為,在這個案件中,應當優先保護善意第三方的利益,但是裁判依據不能援引《物權法》第106條物權善意取得的規定,可以考慮在說理部分解析清楚。實際上,知識產權的善意取得與物權的善意取得原理是一樣的,只需要在說理部分論證清楚即可。但我們的《專利法》《商標法》以及《著作權法》等法律中目前并無相關規定。而在剛頒布的《民法總則》中也未設立關于善意第三人信賴利益保護的一般條款。這點是令人遺憾的。
十三、所有權人的抵押權問題
提到所有權人的抵押權問題,很多人會有疑惑。抵押權是用來擔保債務的,是向債權人提供的,所有權人在自己的財產上存在自己的抵押權,怎么理解?《擔保法》77條規定,同一財產向兩個以上債權人抵押的,順序在先的抵押權與該財產的所有權歸屬一人時,該財產的所有權人可以以其所有的抵押權對抗順序在后的抵押權。該條針對的情形是,債務人的同一個財產向兩個以上的債權人做了抵押,現在,第一順序的抵押權人與債務人發生了企業兼并。在這樣的情況下,抵押權問題怎么對待。同一財產向兩個以上債權人設定抵押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余額再抵,另一種是重復抵押。在重復抵押的情形下,第一順序的抵押權消滅了,后一順序的抵押權人就會升進位次。而如果將債務人的財產進行清算,第一順序的債權人優先受償,第二順序的債權人只能部分受償甚至不能就該抵押財產受償。現在,因為第一順序的抵押權人與債務人合并,抵押權不存在了,后一順序的抵押權升級位次,就能全部優先受償。這對于原來第一順序的抵押權人是很不公平的。在學理和多數立法例上,都是在承認后順位的抵押權在前順位的抵押權消滅時的位次升進規則的同時,設置一些例外規定。《擔保法解釋》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才作出了上述規定,這是符合法理的。
除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外,所有權人抵押權在當前情況下還有其他一些適用的空間。這里舉兩個例子來說。一是保留所有權買賣,二是融資租賃。某個債權企業將一臺挖掘機以保留所有權買賣的方式賣給某個體經營者。挖掘機價值30萬。買受人先付5萬,取得了挖掘機的占有、使用權。合同約定,出賣人保留所有權,待付清全部價款,所有權才移轉。結果,買受人嚴重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付5萬元取得挖掘機的占有、使用權后,不再支付后面的余款了,并且還把挖掘機賣給了第三人,賣的錢也自己消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債權人的利益如何保護?保留的所有權對自己的債權利益實現基本沒有作用,風險非常大。保留的所有權只有在標的物還在債務人手中的時候,才有意義,比如債務人破產了,在清算、清償時有意義。2004年最高法院發布的《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專門規定了保留所有權買賣,對此法律問題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是,該司法解釋沒有涉及到一旦所有權保留買賣中的買受人背信棄義,把標的物轉讓給善意第三人而不能追回的情況。另一個例子是融資租賃。融資租賃中的出租人出資把標的物買來,出租給承租人,承租人分期付款,到與標的物價款持平,連同利息償還完畢之后,再以一個象征性的買價支付給出租人,然后取得租賃物的所有權。在融資租賃期間,標的物的占有使用歸承租人,如果承租人與剛才講的那個保留所有權買賣中的買受人一樣,把承租的標的物轉賣了他人,賣的錢也沒有還債,出租人的利益怎么保護?這種情況下,融資租賃中的出租人也是所有權人,與保留所有權買賣的性質一樣,他的權益沒有保障。為了保障出租人的利益,多數人主張設立融資租賃的登記,使登記的出租人的權益可以對抗其他人。最高法院后來出臺了《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根據該解釋第9條的規定,出租人可以在將標的物交付給承租人之后,要求承租人就該標的物為自己辦理抵押登記,設定一個抵押權。有了抵押登記,融資租賃中的出租人以抵押權來對抗其他普通債權人和買受人,人民法院應當支持。在這個制度設計里面,融資租賃中的出租人一身三任,即所有權人、出租人、抵押權人。這就是在自己有所有權的財產上為自己設定了抵押權。我認為這是一項很好的制度設計,能夠有效地保護融資租賃中出租人的利益。實際上,在保留所有權買賣中,也完全可以運用同樣的規則。保留所有權買賣中的出賣人一方面把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保留所有權,同時要求在這個標的物上設定抵押權,這樣所有權人就可以對抗其他人。不過,在《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制定時,還沒有想到這點。在保留所有權買賣中,還有一個方案,就是出賣人不保留所有權,直接把標的物賣給買受人,同時要求買受人為自己辦理動產抵押,抵押權完全可以保證標的物價款的受償。前一種方案,也是所有權人抵押權問題,后一個方案,則是普通抵押權問題。這兩種制度設計都是可以的。
在國外立法,特別是德國法上,所有權人抵押權還有所謂的原始所有權人抵押權類型。剛才提到的幾個例子都是后來發生的所有權人抵押權。原始所有權人抵押權的作用是什么呢?比如我有一套不動產價值5個億,現在想向銀行融資,銀行能夠給我的貸款額度有限。為了最大限度發揮不動產的融資功能,德國發明了一項制度,即可以先給自己登記一項抵押權,而且登記為第一順位。將來誰愿意貸給我更多的錢,我就把自己的抵押權轉讓給誰,以此打消放貸一方的顧慮,盡可能地實現多融資的目的。我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制度設計,未來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再做考慮。
十四、抵押權登記的順位和善意取得的關系問題
《物權法》極大地拓寬了登記對抗主義的適用范圍。現在,動產抵押適用的規則是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包括特殊動產抵押權、普通動產抵押權以及浮動抵押都是這樣規定的。根據這樣的法律規定,未登記也成立抵押權。那么,就會出現如下的情況:某項動產之上設定了第一個未登記抵押權之后,抵押人又為第二個債權人設定了另一個抵押權,而該抵押權完成了登記。按照《物權法》關于抵押權順位的排序規則,登記的抵押權優先于未登記的。一方面,按照登記的順位規則,登記的要優先于未登記的。另一方面,按照登記對抗主義的規則,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這就意味著可以對抗惡意第三人。假如登記的設立在后的抵押權人知道該標的物上存在一個在先的未登記的抵押權了,還去登記,這種情況下未經登記的抵押權人是否可以對抗后來登記的惡意的抵押權人?這對順位有無影響?實踐中已經發生了類似的事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基本都認可這樣的規則,即順位的規則中無需考慮是善意還是惡意。得出該結論有兩大理由,一是考慮善意還是惡意會導致無法解決的問題,比如第一個抵押權未經登記,第二個抵押權登記了但抵押權人是惡意的,第三個抵押權也登記了且抵押權人為善意。對于這樣的情況是無法排序的。二是抵押人在同一抵押物上設定兩個以上抵押權,是否是正當行為?一般認為,在一房兩賣等情況下,出賣人的行為至少是不誠信的、應受譴責的,而一物二抵則沒有道德上的可譴責性,即抵押人有權設定兩個以上抵押權。因此,這里無需考慮抵押權人是善意還是惡意,只要看登記就可以了。
這里還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不動產上的租賃權與抵押權發生沖突,如何處理的問題。原來《擔保法》有規定,《物權法》又進一步明確,區分先出租后抵押和先抵押后出租兩種情況,分別處理。如果一個房屋先出租了,后來抵押給了債權人并辦理了抵押登記。抵押權實現的時候能否破除在先的租賃?按照法律規定,是不能破除租賃的。但是,如果房屋的租賃沒有到房管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手續,導致抵押權人不知曉已經存在在先的租賃關系。這種情況下,抵押權的行使能否破除在先的未經登記備案的租賃?解決這個問題,要分析租賃登記備案的作用是什么。根據對法律的理解,租賃登記備案的作用主要是方便管理,與物權登記的作用不完全一樣。但是,租賃登記備案只有管理的作用嗎?有無公示的作用在里面?個人認為,還是有公示作用的。如果這個推論成立的話,在先的房屋租賃關系沒有登記備案,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依現行法的規定,一些用益物權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未登記的,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而租賃關系本身還屬于債權,未經登記卻有資格對抗善意第三人,這在法律的邏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接下來又涉及到,如何認定第三人是否為善意?如果房屋是抵押給銀行,銀行審查時要不要進行實地查看?按照通常的交易規則,銀行沒有這個義務。只要房地產證書是真實的,銀行到登記機構查閱登記簿沒有問題就可以了。而如果是自然人之間的抵押,按照通常的交易習慣,就有義務去實地查看。關鍵的問題就是看第三人是否有過錯,是否構成善意。判定的基本標準就是同等條件下同類人有沒有盡到基本的注意義務。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是否盡到了基本的注意義務。多年前,有法官問過我一個案子:房屋的出賣人將房屋出售給第一個買受人。當時,房屋沒有登記,因此無法辦理移轉登記。但該房屋已經歸第一個買受人居住使用五六年之久。后來,房屋可以登記了,房屋所有權人又把房屋賣給了第二個買受人,并且登記在第二個買受人名下。現在,第二個買受人是登記的所有權人,對實際占有房屋的第一個買受人主張房屋歸自己所有,要求其騰房。第一個買受人堅決不同意。登記的買受人起訴了實際占有房屋的買受人。訴訟中,第二買受人堅持說自己沒有去看過房子,不知道第一買受人已經實際居住該房屋,而第一買受人也無法證明其知情。當時情況下,我們認為,依據通常的交易習慣,房屋是普通民眾的家庭重大財產,所以,買賣房屋時查看房屋的實際狀況是一般買受人應盡到的基本注意義務。也就是說登記的那個第二買受人應當有實地查看的注意義務,沒有盡到這個義務,存在重大疏忽,就不能構成善意,也就不能對抗在先的實際占有人。現在,司法解釋已經明確,登記的房屋所有權人不能對抗在先的房屋實際使用人。
(文章系根據作者在山東法院2017年度民事審判培訓班上的授課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定)
責任編校:陳希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