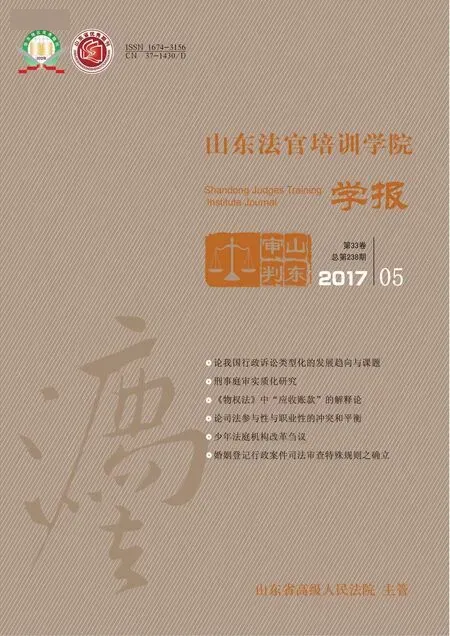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標準的思考
●耿露
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標準的思考
●耿露*
【要點】
在認定夫妻債務時,應當合理分配債權人和舉債人配偶一方的舉證責任,根據實際情況,舉債人配偶一方完成“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責任后,超出日常需要舉債的舉證責任轉移到債權人一方。
【案情】
田某訴稱,2014年7月底,劉某向其借款5萬元,口頭約定借款期限為2個月,借款利息每月2000元。該筆借款用于夫妻雙方共同經營的茶葉店生意。田某于2014年8月3日通過銀行匯款將該筆借款匯給劉某。借款到期后,田某多次向劉某主張要求歸還本金及利息,但是劉某一直拖延未予歸還,已經嚴重損害田某合法權益。劉某慧與劉某系夫妻,應共同償還債務。請求依法判令:1.兩被告共同償還借款本金5萬元;2.兩被告共同償還借款利息(以所欠本金5萬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24%計算,自2014年8月3日起計算至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暫計算至2015年8月31日,共計12000元)。
劉某辯稱,5萬元已收到,沒有償還。關于利息、期限均未約定。借款的實際用途為和別人合伙做生意用,還別人的錢,和劉某慧沒有關系,也不是用在茶葉店上。
劉某慧辯稱,劉某慧對于該債務從來不知情,田某也從來沒有提及,田某與劉某慧是多年的朋友,假如說該借款真實存在的話,田某從來不提的這種做法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兩被告已經于2015年4月13日辦理了離婚手續,在雙方的離婚協議中明確約定,男方名下的債務由其自己全部承擔,所以該債務與劉某慧沒有關系。茶葉店是兩被告共同經營的,劉某慧只負責看店,進貨很少參與。即使該債務存在,其借款也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劉某中國建設銀行62228023********493交易明細可以證明在田某轉給劉某5萬元后,當天劉某分三次轉款給孟某和高某,本案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通過2015年4月14日田某和劉某慧的對話錄音能夠證明田某說借款是劉某和別人合伙弄工程,田某關于該借款一直沒有向劉某慧提過,劉某慧對于本案借款確實不知情,田某也知道案涉款項未用于茶葉店的經營。綜上,劉某慧不應該承擔償還責任。請求法院駁回田某的訴訟請求。
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田某持有借條一份,載明:今借田某現金人民幣5萬元,借款人劉某。2014年8月3日,田某向劉某借款5萬元,同日,劉某向案外人高某、孟某共計轉賬51500元。自2014年7月至2014年9月,劉某與田某有多筆轉賬來往。被告劉某、劉某慧原系夫妻,二人于1995年10月結婚,2015年4月離婚。根據劉某慧提供的錄音,田某曾對劉某慧說:“他(劉某)借時不愿讓和你說”、“他那次說和人家合伙招標,弄工程”。
【審理】
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認為,劉某逾期未償還借款,應承擔還本付息的義務。關于案涉借款是否屬夫妻共同債務,借款雖發生在兩被告婚姻存續期間,但由于:第一,劉某與田某在借款前后因生意存在多筆金錢往來;第二,劉某慧舉證證明借款轉賬當日,劉某即向兩案外人轉賬51500元,能夠高度蓋然證明借款去向未用于家庭生活;第三,根據錄音,借款時劉某慧對該筆借款并不知情且劉某借款時聲稱借款用于合伙工程。綜上,劉某慧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案涉借款非用于兩被告共同生活,田某未繼續舉證證明借款為兩被告的夫妻共同債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4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4條,原告田某要求劉某慧共同償還借款本息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評析】
一、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律適用與沖突
《婚姻法》第41條(以下簡稱“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該法第19條第3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4條(以下簡稱“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情形的除外。”
從立法本意上,對于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夫妻共同舉債的合意以及是否為共同生活或者以共同生產經營為目的。而“41條”的規定過于寬泛,“24條”的推定原則從表面上看又僅以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為判斷依據,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就是如果沒有直接適用“24條”的推定原則,而是直接適用“41條”的規定,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例如本文中的案例,如果直接適用“24條”的推定原則,將案涉借款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則會出現截然相反的判決結果。
二、對“24條”的補正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如何認定的答復((2014)民一他字第10號)中明確:“在債權人以夫妻一方為被告起訴的債務糾紛中,對于案涉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4條規定認定。如果舉債人的配偶舉證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
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對該“24條”增加規定了第2款和第3款,即夫妻一方與第三人串通,虛構債務,第三人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從事賭博、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中所負債務,第三人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從上述《補充規定》和最高院相關答復中可以看出:一是要根據“24條”的規定來認定,但是例外情形不僅限于“24條”規定的兩種情形,還包括虛假債務、非法債務和“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述補充旨在達成“41條”與“24條”的內在統一,使推定的法律事實更加接近于客觀現實。
三、靈活運用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尋求保護“債權”和避免“被負債”之間的平衡
對于以夫妻一方名義負債的案件中,不應生硬適用“24條”或過分加重配偶一方的舉證責任,對配偶一方完成舉證責任的標準應慎重掌握。根據“41條”“24條”及《補充規定》,結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如何認定的答復((2014)民一他字第10號),舉債人配偶一方承擔的舉證責任相對應的待證事實應當包括:(5)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第(5)種情形有現實普遍性且筆者認為靈活準確運用這一舉證標準,有利于在現行法律框架之下發揮“24條”推定原則的積極作用,使推定的法律事實更加接近客觀事實,最大程度實現保護“債權”和避免“被負債”之間的利益平衡。
確定“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標準的積極意義在于:其一,適當降低舉證難度。將足以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視為完成舉證責任,相較必須證明所借債務為虛構債務或賭博、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具體行為而言,舉證負擔減輕。其二,舉證客觀現實可行。所借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搜證范圍限于舉債人夫妻雙方日常生活和消費支出,客觀上容易實現,而要舉債人配偶一方證實“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第三人知道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約定”,甚至“夫妻一方與第三人串通虛構債務”,舉證較為困難且不符合日常習慣,很多情況下配偶一方與債權人并不相識,另有情況下舉債人與配偶關系緊張,并不配合配偶一方完成舉證,更有夫妻雙方因雙方離婚糾紛及作為共同被告的民間借貸糾紛同時涉訴亦不鮮見……實踐中的種種情形無疑給舉債人配偶一方設置的一道道無形又強大的障礙,使舉證責任完成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三,自由心證有落腳之處。實踐中,法官通過庭審調查、問詢往往對事實認定有所判斷,但運用法條和分配舉證責任時,如生硬套用“24條”可能因過分加重了舉債人配偶一方的舉證責任而得出與運用自由心證認定的與客觀事實高度蓋然接近的事實截然相反的結論,因此靈活運用“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標準,有利于彌合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之間的隔閡,據個案實際綜合運用證據認定和自由心證得出最接近客觀事實的認定結果。其四,預留舉證責任轉移的空間。前已述及,根據現有法律規定,證明債務非夫妻共同債務的舉證責任在舉債人配偶一方,在舉證責任既定的前提下,法官依據“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標準,結合配偶一方提供的證據,綜合判斷是否使債權人所舉證證明的所訴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事實發生動搖,而適用舉證責任轉移,由債權人繼續舉證證明所訴債務性質系夫妻共同債務。其五,給經驗法則以適用余地。“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落腳點是生活所需,對日常生活支出,通過對夫妻雙方工資收入和借貸發生前后一段時間的消費支出情況的調查不難得出結果意義上的認定,通過運用該日常經驗法則,可以大致判斷所借債務是否明顯超過日常生活所需,從借貸金額上初步判斷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能為區分待證事實、合理的舉證責任分配提供參考。
具體到本文的案例,劉某與田某在借款前后因生意存在多筆金錢往來、借款轉賬當日,劉某即向兩案外人轉賬與借款金額相當的數額、田某承認劉某慧并不知情、田某亦稱劉某曾說借款用于與他人合伙做工程。即使是按照高度蓋然性的標準,也已經完成了舉證責任。本院在審理過程中認為,因舉債配偶一方已經完成了“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責任,才把超出日常需要舉債的舉證責任轉移到債權人身上。
責任編校:王文斌
*耿露,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