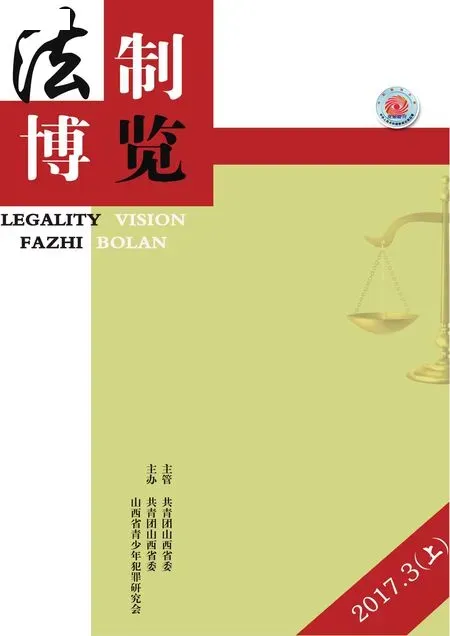法不責眾的概念及其影響分析
王中杰
西藏民族大學,陜西 咸陽 712082
?
法不責眾的概念及其影響分析
王中杰
西藏民族大學,陜西 咸陽 712082
法不責眾的概念目前在我國十分流行,并對社會造成了諸多負面的影響,對立法司法以及執法帶來了很多的困難。本文就是從法不責眾的概念進行分析,從法制建設以及傳統文化等方面探究其出現的原因以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后對此提出一定的解決辦法。
法不責眾;聚眾犯罪;法制建設
何為法不責眾,法不責眾就是指當某項行為具有一定的群體性或普遍性時,即使該行為含有某種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對其也難予懲戒。這種理論,并不是一個受到法理學所認可的理論,但是卻長久的存在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目中,并對其造成了極為巨大與惡劣的影響。
而這一觀念主要則是在法治發展不健全,民眾整體素質較低的國家較為流行,因為這種理念實質上是對法律的威嚴的一種踐踏,是一種人治的觀念,而非法治的觀念,在“法不責眾”里邊的法不是法律,而是一種社會規則。尤其在我國,法不責眾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對人民群眾的日常行為有著巨大的影響,也由此對我國當代的立法執法以及司法工作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這種現象,在小的方面的體現,如集體闖紅燈,聚眾賭博之類的情況,在日常生活中是屢禁不止,往大的方面來說,某些個人或者利益集團以集體的利益為理由來損害其他人乃至整個社會,國家的利益的現象,又或者,以法不責眾為借口來煽動群體性事件等等,這都是法不責眾這一落后的觀點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而法不責眾這一觀點之所以能夠成立,在有著現實的社會需求的同時也有著傳統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中國。
一、法不責眾的原因分析
法律本身的不足與缺陷:雖然說當前我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了,但是我國的法律在許多方面依舊存在這不足,尤其是在對群體性犯罪這方面的規定,難以盡如人意。在我國,目前所謂的聚眾犯罪就是我國刑法所明確規定的11個條文下的14個聚眾型犯罪。不是只要多數人聚集在一起實施某種犯罪活動就是聚眾型犯罪。只有刑法進行明確規定的才能算是犯罪,不然就沒有討論的意義了。
而之所以說法律本身有不足與缺陷,一方面是對于其處罰方面的問題,在這個方面,法不責眾,也可以理解為罰不責眾,固然,從寬嚴相濟的政策以及刑罰的預防性目的來說,應當要求只對其中的一部分主觀惡性較為嚴重的人進行處罰,但是我們并不能保證刑罰的公平性,而保障法律的公平性這是從執法與司法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有的法律規定,對于公民的私生活的干預也是值得考慮的方面。例如聚眾淫亂罪,是指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聚集男女多人集體進行淫亂的行為。按照犯罪構成的理論,本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公共秩序,但是,究竟這個方面的事情是不是公共秩序所應當涉及的,或者這只是一種道德層面的問題,而不應當上升到法律層面來進行考慮。畢竟這是公民的私生活的情況,是在一種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其是否對公眾的善良情感產生了影響呢?這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所謂的聚眾性犯罪,其一般都對于公共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多人參與也帶有了一定的公共性,而在法律意義上的公眾,應當是指除了自己以及與自身有著相當關系或是一定交往的人以外的人群。所以說,聚眾淫亂罪這個罪本身就存在這很大的爭議。而淫亂二字,本身就帶有一定的主觀臆斷。法律應當是客觀的,所以說,這在某些方面可以稱之為惡法,是道德綁架了法律。
民眾法律意識的淺薄:一個發達的社會,應當讓每一個公民都具有較高的道德素養與法律素養。而在我國,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過于高速的發展以及文革時期對于傳統文化的過度破壞導致了現今的人缺少了道德的約束,缺少了對于法律的敬畏。每一個公民都應當認識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犯罪的主體有多少,其在社會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都應當承擔其所違法而帶來的后果,也就是說,不論是個人的違法行為還是眾多主體共同的違法行為,其所受到的懲罰都應當是按照其所照成的后果來承擔的,不能進行差別對待。當然,這只是法理上的要求,而在現實生活中,要求法不責眾這樣的思想完全消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極低的違法成本與極高的懲罰成本:在我國,法不責眾是被大眾所認可的概念,即大多數人知道法不責眾,而這正是因為找出并懲罰違法者所要付出的代價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超出了社會所能支付的代價的,也就是對這類違法行為的執法所能得到的利益要遠遠不足其所付出的。更何況,這樣做是與當前公民的一致性的法不責眾的認識是相違背得,也就無法得到人們的支持與認同。也因此面對這類違法行為的懲處才會那么的困難。
我們要明白法律是擁有壓倒性力量的一方制定的,這時候群眾是一盤散沙,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所以無法抗衡只能遵守。因為不遵守得到的懲罰是得不償失的。
一旦法律違反一部分人(但不一定是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時候,只要這部分的人聚集起來足以和法律制定的一方的力量相抗衡,那么法就不會“責眾”。而且因為人足夠多,不遵守法律所獲得的利益遠高于可能受到的懲罰,總之不是得不償失的。
傳統文化的影響:在中國,有這么兩個成語很有意思,一個是法不責眾,一個叫眾怒難犯。這兩者都代表了一種群體性的意志與想法,都可以往好的方面來說,這才是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有這樣的訴求,要以一種群體性的力量來解決問題,也就是所謂的人多力量大。但是,人多了之后也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不同的利益訴求,也經常有人借助著這樣的力量來進行一些個人本身所不敢進行的活動,在煽動起了集體的行為之后,既得到了自己的利益訴求,又逃避了責任。而這就是群體性行為的魅力之所在。在人治的情況下,人民對法律沒有信仰,對法律的遵守不是出于對于法律的敬畏與認同,而是為了逃避法律的追責。那么,當其能夠借助群體性的力量之后,也就必然帶來各種不遵守法律的行為。這種思想,自古以來在中國就很有市場,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人治的社會,而人治的社會的統治基礎就是人心,那么,當面對多數人的違法問題時,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對這些多數人進行處理,從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來獲取所謂的民心。但是,這樣的思想在當代應當是行不通的,因為當今社會需要的不再是人治,而是法治!
二、法不責眾的利與弊
不能說法不責眾就完全是一件壞事。它在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的渠道不暢通的時候,是最后的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一些問題,但是,這也必然是發生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中的事情。這符合我國當前的具體國情,所以法不責眾這一觀點也必將長期的在我國存在下去,直到法治社會的完全建成。
但是法不責眾所存在的弊端依舊很大,下邊我們就從2014年發生在青海的一個案例來進行分析,法不責眾在很多具體情況下是否應當適用。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格爾木的野生的黑枸杞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也為此吸引了眾多人的采摘。這本身并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是,在這些場所被當地政府承包給了當地的牧民之后,在承包者利用護欄保護的情況下,依舊有大批的采摘者涌入,不顧阻攔的強行盜采,甚至于用刀子捅傷了保衛人員,對承包商的房屋進行損毀等等。這本身就是一起十分嚴重的刑事案件,但是,由于其案件所存在的群體性這一性質,明明行為當中包含了搶劫,放火以及故意傷人的行為,但是卻依舊只是進行了一些行政拘留甚至于不處理來解決問題。那么,這樣的情況是否符合常理呢?按照法不責眾的概念,這種處理方法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因為這樣的一個概念,我們是否就能無視這起事件中所存在的諸多犯罪行為呢?這明顯是十分不合理的,是不符合法治的理念的,人們對于自己的行為完全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由于處理的成本過高,以及出于盡快解決問題的考量,最終我們只是對這些人進行了最低限度的處罰。如此荒唐的事情,就因為法不責眾而發生在了我國這樣一個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國家里。
三、法若責眾是否即為惡法
有這樣的一種說法:法律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絕大數人的利益,如果某項法律對普遍的“眾”進行懲罰,那么這個法就是惡法,這個就不是一個健全的法制國家可能產生的結果。這樣的說法顯然有其道理所在,確實,一部讓許多人都會觸犯的法律,其本身的存在就有一定的問題,一部對眾進行處罰的法律,本身就很奇怪不是嗎。但是,法律所應當保護的眾,絕不僅僅是針對每一起案件當中所謂的眾,而應當是一個總體意義上的眾,不是說在具體案件當中人多的一方就是眾,而是整個法律所保護的眾的利益的眾,不然的話,我們也就沒必要制定具體的法律了,在每一件事情當中,只要看哪方人多就判定其勝訴就可以了。
既然制定了法律,我們就應當按照其所制定的內容進行執法與司法工作,可為什么能夠出現法不責眾的現象呢?
法不責眾作為一種立法上的原則,是不能成為司法與執法上的原則。這一點應當是我們所要注意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前邊所提到的青海的案件,是針對于犯罪者而言的法不責眾,但是,法不責眾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分析:“眾”可以是參與違法犯罪者以外的社會公眾,而他們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壓力,是會影響法官的自由裁量的。比如無論多少人犯罪,按法律規定都是要處罰的,但是有可能社會公眾輿論會形成壓力,迫使法院做出不同判決。比如許某案在法定刑以下處罰,我認為這是另一種意義的法不責眾。
總之,法不責眾法理不容,從本質上而言,終究還是一種人治的觀念,與當前我國所倡導的法治社會是背道而行的,在當前隨著社會發展的各類問題的不斷突出,社會矛盾愈發激烈的情況下,法不責眾無疑是在鼓勵種種暴亂行為的發生,鼓勵人們采取群體性犯罪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但是這明顯只能激化社會矛盾。
[1]郝鐵川.“法不責眾”的正解和誤解[N].東方早報,2014-6-24.
[2]陳菲.從法理學角度探究“法不責眾”的存在原因[J].今日中國論壇,2013:191-192.
[3]周瑋.法不責眾的批判與思考[J].法制與社會,2015.
[4]馮天舒.從“中國式過馬路”看中國“法不責眾”思想[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1):50-52.
[5]吳勝男.論“法不責眾”背后的法理精神[J].金田,2015.
D
A
2095-4379-(2017)07-0145-02
王中杰(1993-),男,漢族,江蘇盱眙人,西藏民族大學,法律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