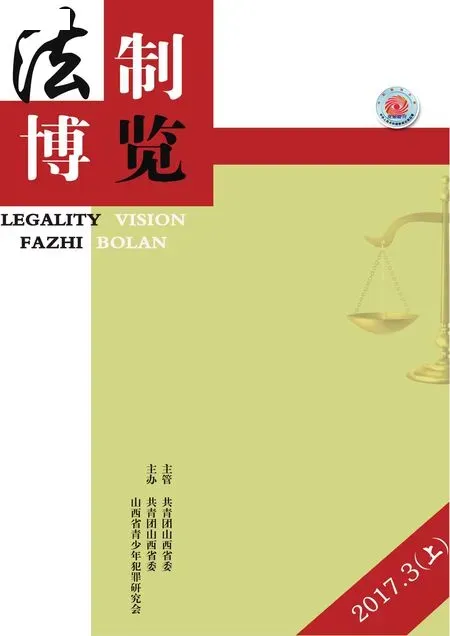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視角的反思
黃益輝
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
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視角的反思
黃益輝
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企業是市場經濟中的最重要成員,企業的基本目標是營利,但是除此以外企業還應當承擔社會責任,本文從法學視角入手,通過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發展和主要內容的介紹,對該觀點提出批判,明確企業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就不應該被強迫承擔不應該屬于它的責任,更不應該讓這種責任影響到企業的經營行為。
社會責任;企業;經營行為
一、由“某貼吧事件”所想到的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以及大眾傳媒的發展,在以前可能一直浮在書面下的企業的商業行為侵犯公共利益并遭受詬病的情況開始逐漸多了起來,關于我國企業的經營行為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發生沖突的新聞也一直不斷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履行開始逐漸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2016年初的某著名網絡平臺發生的“血友病吧”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事件以百度貼吧“血友病吧”吧主被該網絡平臺公司用商業合作公司替換而引起,以該網絡平臺公司終止商業合作并被國家網信辦約談而告終。
當一家公司的經營行為雖然沒有觸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但是卻和社會的道德準則發生沖突時,是否該企業就應該承擔原本并不屬于企業應該承擔的義務?社會責任是否應該強加在企業身上而不是由企業自主決定?如何判定企業沒有承擔自身的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的定義應該交由模糊的社會道德判斷,還是用清晰的法律予以明確?
二、我國法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
我國《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這一條是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宣示性規定,明確的提出了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關于此條文,我們可以解讀出的信息是:1.該條沒有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予以明確的規定,而是指導、號召性的條文,更多的是原則性的規范,與《公司法》中其他明確規定了企業違反法律規定的硬性條文不同,它是一條“軟法”,根據姜明安教授對于“軟法”的定義:“軟法不具有國家強制力,不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而是由人們的承諾、誠信、輿論或紀律保障實施。軟法之所以稱‘軟法',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不具有國家強制力,不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①;2.該條文明確提出了企業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法律中的地位。《公司法》第5條于05年修訂,給予企業社會責任以成文法的明確規定,對于促進我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以及在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訴訟的司法裁判有著依然有著積極的意義。雖然是軟法,但是該條文也具有著硬法所不具備的優勢,“軟法可以通過規定積極后果的方式實現企業社會責任,這種利益激勵方式同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是一致的,也正因如此,企業更樂意、更主動去實施立法者所提倡的行為。”②3.該條款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仍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雖然明確提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是缺少更進一步地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
我國《公司法》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除了第五條以外,還有其他的硬性規定,如第十七條規定:“公司必須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加強勞動保護,實現安全生產。公司應當采用多種形式,加強公司職工的職業教育和崗位培訓,提高職工素質。”第十八條規定:“公司應當為本公司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公司工會代表職工就職工的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福利、保險和勞動安全衛生等事項依法與公司簽訂集體合同。”這兩條對于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系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加強了法律對于員工利益的保護。除了《公司法》,我國《勞動法》也對于員工利益的保護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恪守社會公德,誠信經營,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得設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條件,不得強制交易。”這一條主要是對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由于企業或者經營者在交易中都處于強勢地位,所以該法規定了經營者在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時應該恪守的準則,保護了消費者的權益,也屬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
此外,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對于企業在環境方面的責任也做出了規定。《環境保護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防止、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所造成的損害依法承擔責任。”此條明確的規定了我國企業需要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屬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明確規定。
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擴大化的反思
誠然,在今天這個經濟全球化的年代,企業的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消費者權益、勞工權益等問題越來越多,這些社會責任是企業必須要承擔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不僅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也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塑造企業良好的形象。
但是,企業社會責任是否就應該成為企業的首要目標甚至比股東的利益更加重要呢?筆者認為那種將企業社會責任擴大化并且將其置于公司營利目標之上的觀點并不可取,這種觀點對于企業的苛責將會影響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最主要成員的根本職能,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類的天性,更是企業的天性,企業就是為了賺錢而生,而逐利的本性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試圖改變資本的逐利本性,企業運營的一條最基本的底線是營利。如果企業不能成為逐利的實體,那么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將成為空談。畢竟,只有在能夠給股東帶來資本回報率的前提下,企業才有能力去奉獻社會。否則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有所依賴的利益相關者也不能得到可靠的、有保證的、能持久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即使是這樣,企業仍有權利選擇是否承擔和會責任,而不是被迫去承擔。
企業應該承擔符合道德要求的社會責任,但是不能用道德將企業的經營行為完全束縛住。對企業社會責任來說,能法律責任化的同樣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線的要求實際上,只要考察一下當前已經法律責任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如有關保護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勞工等強行性法律規范,就可以發現其都是對企業道德底線的要求。③同時,道德化的企業社會責任也必須要依靠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只靠社會輿論很難讓企業主動承擔。所以,對于企業我們應該賦予它們最大化的經營自主權,而不是束縛住它們的手腳,以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理由任意干預企業的經營行為。只要企業的經營行為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就不應該任意的加以禁止。
[ 注 釋 ]
①姜明安.軟法的興起與軟法之治[J].中國法學,2006(2).
②蔣建湘.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化[J].中國法學,2010(5).
③蔣建湘.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化[J].中國法學,2010(5).
[1]姜明安.軟法的興起與軟法之治[J].中國法學,2006(2).
[2]蔣建湘.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化[J].中國法學,2010(5).
D920.4;F270;F
A
2095-4379-(2017)07-0215-02
黃益輝(1991-),男,漢族,安徽巢湖人,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法律碩士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