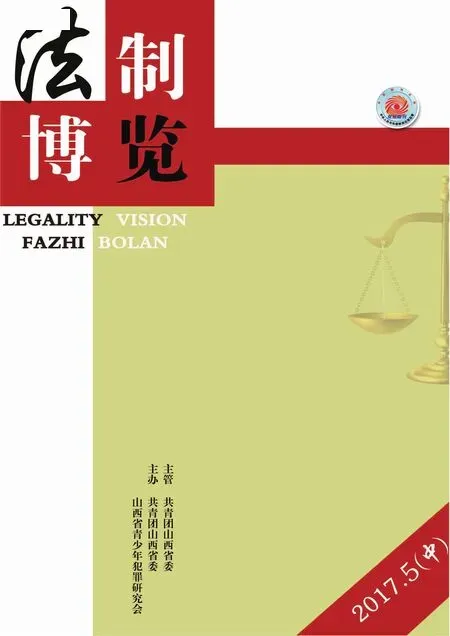涉商標犯罪案件商標侵權民事責任的認定
——評施某德公司訴高某良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李廣鶴
華南理工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6
?
涉商標犯罪案件商標侵權民事責任的認定
——評施某德公司訴高某良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李廣鶴
華南理工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6
對于損害商標權人利益的行為,我國法律設立了多重責任體系。依照商標法的規定,對于商標侵權行為,權利人可以要求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如果侵權行為損害了公共利益,侵權者應當承擔行政責任,嚴重的還要按照刑法規定承擔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是侵權者實施商標侵權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形式,論嚴厲程度,刑事責任最嚴重,行政責任次之,民事責任最輕。侵權者承擔了刑事責任,是否必然承擔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本文結合有關案件,就侵犯商標權的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為司法實踐處理類似案件提供參考。
一、據以分析的案例
原告施某德公司訴稱:原告是“Schneider”及“Telemecanique”注冊商標的普通被許可使用權人。被告高某良將假冒涉案注冊商標的電氣產品裝入印有“Schneider”商標的包裝盒中,存放在被告高某余經營商行的倉庫內。2015年6月,公安機關將高某良抓獲,現場查獲假冒涉案商標的注冊商標電氣產品42種19288個,印有“Schneider”商標的包裝盒230個。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對高某良作出(2015)穗越法刑初字第168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高某良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原告認為高某良銷售侵犯涉案商標權的商品,高某余為被告高某良銷售侵權商品提供便利條件,兩人均應承擔商標侵權民事責任,故起訴請求法院判令:高某良、高某余立即停止侵犯施某德公司商標權的行為;高某良、高永共同賠償施某德公司經濟損失40萬元。
法院經審理查明:第G715396號“Schneider”商標的注冊人是施某德電氣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為第9類,包括電子或電氣元器件、電感器等;第267665號“Telemecanique”商標的注冊人是施某德電氣工業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為第9類,包括電力配給系統中的各種操作、日用開關等。兩商標均在注冊有效期限內。施某德電氣公司、施某德電氣工業公司許可施某德公司使用兩注冊商標,自2013年1月1日起有權以自己名義對侵害兩商標權的行為進行維權。
2016年1月27日,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刑初字第1684號刑事判決書,其中查明:自2000年,高某良成立浙江某電器公司廣州市銷售公司,在廣州市越秀區從事電氣產品的經營銷售。期間,高某良在未經商標權利人的許可或者授權下,將一批假冒“Schneider”“Telemecanique”注冊商標的電氣產品裝入印有“Schneider”商標的包裝盒中,存放在廣州市越秀區惠福西路XX號某機電設備商行倉庫內,準備進行銷售。2015年6月,公安人員在上述倉庫將高某良抓獲,現場查獲假冒“Schneider”“Telemecanique”注冊商標的電氣產品42種共計19288個(經鑒定,其中36種5318個共價值407030元),以及印有“Schneider”商標的包裝盒230個、手機1臺、手提電腦3臺、銷售單據1批。據此,法院認定高某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鑒于高某良系犯罪未遂,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3萬元,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冊商標的電氣產品、包裝盒等物予以沒收、銷毀。該刑事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另查明,廣州市越秀區某機電設備商行為個體經營,經營地址位于廣州市越秀區惠福西路XX號首層,經營者為被告高某余。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30日作出(2016)粵0104民初4596號民事判決,駁回施某德電氣公司的訴訟請求。宣判后,施某德公司提起上訴,廣州知產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高某良將一批假冒“Schneider”“Telemecanique”注冊商標的注冊商標的電氣產品裝入印有“Schneider”商標的包裝盒中,存放在廣州市越秀區惠福西路39號昌得機電設備商行倉庫內,準備進行銷售,后被公安機關查獲。高某良對被訴侵權產品重新包裝的行為,屬于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的“使用”,構成商標侵權;高某余提供倉庫存放涉案侵權產品,其行為構成幫助侵權。但是,高某良重新包裝的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實際銷售,即全被公安機關查獲,其行為不符合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所規定的“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商品”之情形,施某德公司主張高某良銷售侵犯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沒有法律依據,法院不予采納。高某良重新包裝后的侵權產品尚未實際進入市場銷售,該侵權產品后被法院判決沒收、銷毀,高某良的侵權行為沒有給施某德公司造成實際損失。因此,施某德公司要求高某良與高某余賠償其經濟損失,依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高某良與高某余的侵權行為早在涉案刑事案件發生后即停止,且侵權行為尚未造成施某德公司實際損失,因此,施某德公司本無繼續提起本案民事訴訟的必要,其主張的律師費、調查費、差旅費等費用不應由高某良與高某余負擔。
二、商標犯罪及其形態
商標犯罪是指我國刑法所規定的,違反商標法規,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破壞商標管理制度,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我國刑法第213條、第214條和第215條規定了三種商標犯罪行為,即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的標識罪。相關司法解釋對三個罪名的構罪要件進行了細分。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要求行為人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且具有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等嚴重情節;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且銷售金額在5萬元以上;構成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的標識罪,要求行為人有非法制造、銷售注冊商標標識達兩萬件以上等犯罪情節。
值得注意的是,與刑法中的其他罪名一樣,侵犯商標權罪也存在犯罪未遂形態。如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達到15萬元以上的,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未遂)定罪處罰;尚未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在6萬件以上的,以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未遂)定罪處罰。據此,行為人的主觀上有侵犯他人商標權的犯罪意圖,客觀行為達到了法定情節或數額標準,則構成侵犯商標權罪,即使行為人的行為沒有實施完畢,亦可能成立犯罪未遂。
三、商標侵權以“混淆”為構成要件
我國商標法第5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仿冒注冊商標、銷售侵犯商標權商品、非法制造或銷售非法制造商標標識、反向假冒、幫助他人實施侵犯商標權等6種類型的商標侵權行為。其中,假冒注冊商標、仿冒注冊商標、銷售侵犯商標權商品、反向假冒屬于直接侵犯注冊商標人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以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發生混淆為構成要件。非法制造或銷售非法制造商標標識、幫助他人實施侵犯商標權屬于間接侵權行為,以行為人認識到直接侵權行為的存在為前提。商標的功能在于區分商品或服務的來源,權利人使用商標的目的在于使消費者能夠通過商標將商品或服務與提供者正確地聯系在一起,確保商品商譽排他性地凝結在商標中,從而提升商品或服務的市場競爭力。因而,無論是直接侵權,還是間接侵權,只有存在可能導致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的行為,才能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
根據混淆的對象不同,可以將混淆分為直接混淆和間接混淆。所謂直接混淆,是指消費者對商品的來源發生混淆,如使用某商標的商品實際上來源甲公司,消費者誤認為來源于乙公司。大多數商標侵權行為都會導致直接混淆的可能,侵權人擅自使用他人商標,往往也是為了“搭便車”,產生直接混淆的效果,使消費者誤認為其商標是商標權人的商品而購買。間接混淆是指消費者對商品的來源不一定發生混淆,但會認為侵權人的商品或服務與商標權人存在贊助、許可、控制等關聯關系。如侵權人在店鋪招牌上使用“寶X特許維修店”字樣,消費者不會相信該店服務由寶X公司提供,卻可能以為是寶X公司授權經營的維修服務,基于對寶X公司服務質量的認可而到該店接受維修服務。間接混淆實際上是侵權人利用商標權人的商譽為自己牟利,經商標權人的許可的經營者因此可能失去一部分客源,間接損害商標權人的利益,如果侵權者提供的服務或銷售的商標質量低劣,還可能損害商標權人的商譽。
關于混淆的判斷,商標法及司法解釋以侵權人使用的商標與商標權人的商標構成相同還是近似,規定了兩個標準:其一,如果行為人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近似,或者在類似上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則需以相關公眾一般公眾注意力為標準,在隔離狀態下對商標整體與顯著部分進行比對,同時結合商標知名度、顯著性等因素進行判斷。一般來說,兩個商標越近似,且商標權人的商標有較高知名度,消費者越容易混淆商品的來源。其二,如果行為人在同一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則直接推定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來源會產生混淆。既然是推定,就存在例外的可能性。雖然在同一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但使用該商標并非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而是為了描述商品的質量、產地等特征或為了說明的用途,此種使用不是商標法意義上的使用,不會導致消費者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商標侵權行為。例如,行為人在商品包裝袋上使用“紅河”二字,并非用于區分商品提供者,而是用于說明商品產地,該使用行為不屬于商標性使用,“紅河”商標的權利人不能據此向行為人主張商標侵權。
由此可見,可能導致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是構成商標侵權的必要條件,也是商標法所規制的行為。不可能導致混淆的行為對于商標權人不會造成商標法意義上的損害,也就不構成商標侵權。
四、構成商標犯罪并不必然成立商標侵權
侵犯商標權罪與商標侵權有著不同構成要件,行為人實施了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即使沒有出現犯罪結果或實現行為人的犯罪目的,其行為也有可能構成侵犯商標權罪;商標侵權以出現損害結果為構成要件,沒有損害結果,行為人雖然實施了一定非法行為,也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侵權。侵犯商標權罪有既遂與未遂形態,未遂狀態下,行為人主觀上有侵犯商標權的惡意,行為具有違法性,但未出現違法行為可能導致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來源產生混淆的損害結果,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侵犯商標權罪,但不成立商標侵權。
前述案例中,高某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而準備銷售,法院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對其定罪,并認定高某良有犯罪未遂情節,對其從輕處罰。該犯罪行為是否構成商標侵權呢?法院依照商標法規定將高某良的行為細分為兩項:一是對涉案電氣產品進行新的包裝;二是準備銷售涉案電氣產品。就第一項行為而言,高某良不是涉案電氣產品的制造和生產者,沒有將“Schneider”“Telemecanique”商標使用在電氣產品上,但其從他人處購買印有“Telemecanique”商標的包裝盒,按每十個電氣產品一盒分裝入包裝盒內,使得涉案電氣產品與包裝盒作為商品整體進入市場,可能導致消費者混淆或誤認涉案產品來源于原告,該重新包裝行為,應當認定為《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中的“使用”,構成商標侵權。就第二項行為來說,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的銷售侵犯商標權商品的商標侵權行為,以導致相關公眾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為構成要件,不會導致混淆,就不構成侵權。涉案產品存放在倉庫中準備銷售,但至被查扣前產品未上架供消費者選購,也沒有證據表明高某良與客戶簽訂了銷售合同,不具有導致相關公眾對涉案產品來源產生混淆的可能性,該行為不構成商標侵權。
盡管對涉案電氣產品進行新的包裝構成商標侵權,但是刑事判決書已判決沒收、銷毀涉案電氣商品和包裝盒,法院不再判令高某良停止侵權。另外,關于商標侵權民事賠償責任,我國商標法確定了“損失填平”及“非法獲利返還”的賠償原則,即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以權利人遭受損失或侵權人獲得利益為前提,如果權利人既沒有遭受實際損失,侵權人也沒有因侵權行為獲得利益,則侵權人無需承擔賠償責任。涉案電氣商品未實際銷售,沒有造成商標權人的實際損失,高某良也沒有因侵權行為獲得利益,故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2095-4379-(2017)14-0020-03
李廣鶴(1987-),女,黑龍江人,華南理工大學,民商法專業知識產權法方向,法學碩士研究生,曾任職于廣州越秀法院,研究方向:民商法。
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