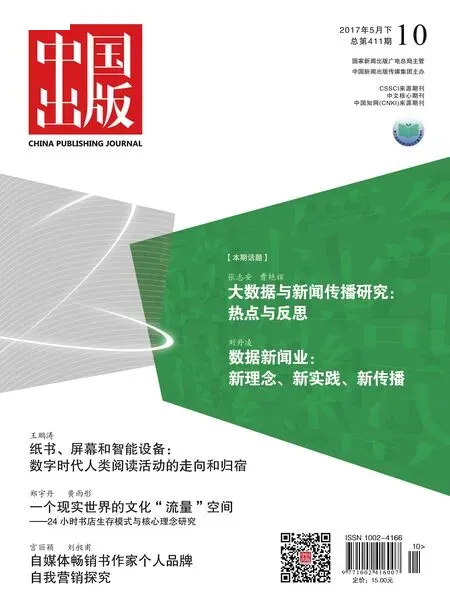數據新聞業:新理念、新實踐、新傳播*
□文│劉丹凌
數據新聞(Data Journalism)實踐的推廣和深入,昭示著整個新聞業態的數據化轉向,這是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新傳播革命之又一成果。2007年,美國《紐約時報》設立兼有記者和程序設計員的新部門,即現在的“互動新聞技術部”(Interactive News Technologies Department),探索包括數據新聞在內的多媒體新聞報道。2009年,英國《衛報》網站開辦“數據商店”,下設“大數據”“數據博客”“數據新聞”等頻道,正式以“數據新聞”命名的新聞實踐拉開帷幕。短短幾年間,數據新聞實踐遍地開花,不僅全球知名媒體紛紛試水,眾多數據新聞網站、數據新聞博客等獨立新聞機構也嶄露頭角。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數據新聞圓桌會議討論了數據新聞發展的可能性、所需工具、工作流程以及發布方式等;2012年谷歌與全球編輯網共同設立首個國際數據新聞獎,鼓勵數據新聞領域的探索和實踐。2012年,騰訊、網易、新浪、搜狐分別開設《新聞百科》《數字之道》《圖解新聞》《數讀》等欄目,開啟中國數據新聞實踐的先河,如果說這些數據新聞嘗試僅限于呈現方式的更新,那么財新數據新聞與可視化實驗室生產的“三公消費龍虎榜”及中央電視臺2014年1月29日引入百度地圖LBS定位大數據推出的“據說春運”等報道則真正拉動了中國數據新聞實踐的馬達。我們認為,數據新聞不是一種單純的新聞類型或報道方式,而是指征著新聞行業的一種發展方向,它正在變更新聞業態、重構新聞生產方式、再造新聞傳播渠道、改寫記者角色定位。
盡管部分學者已經注意到,作為一種全新的新聞實踐,數據新聞指征了一種新型的新聞業態,但是目前學界對它的實質仍缺乏深入分析。文本試圖通過相關文獻的梳理和闡釋,結合當下數據新聞實踐的經驗,分析數據新聞所代表的整個新聞業態的數據化轉向,從新理念、新實踐、新傳播三個維度厘清數據新聞的基本內涵和特征。
一、新理念:數據作為新聞業的結構性力量
什么是數據新聞?學界并無定論,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認識:一是“等同論”,認為數據新聞與精確新聞、計算機輔助報道并無實質性差別,“數據新聞繼承并發展了以精確新聞為代表的計算機發展報道”;[1]二是“發展論”,認為數據新聞演化于“精確新聞”,是“計算機輔助報道”在全球在線背景下發展的結果,三者存在內在的關聯,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明顯區別;[2]三是“差異論”,把數據新聞視為完全不同于精確新聞、計算機輔助報道的新型報道形式,[3]甚至認為數據新聞的概念代表著一種新聞發展的形態,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比計算機輔助新聞報道更加廣闊。[4]本文認為,不同于精確新聞、計算機輔助報道,數據新聞代表著新聞業態的一種數據化轉向,這不僅體現在海量的開放數據和先進的數據分析工具拓展了新聞資源,豐富了新聞呈現形式,變更了傳播交往關系,還意味著傳統新聞理念、生產方式及傳播影響力的整體變遷。在新傳播革命語境下,數據正在逐漸成為新聞生產和傳播的結構性力量,正如《數據新聞手冊》所揭示的——數據新聞是基于數據的新聞生產和傳播業態,它促使新聞生產從專業化的行業生產轉向技術化的社會生產,新聞傳播從面向“大眾”的泛化傳播轉向基于用戶需求的精準傳播。
1.數據新聞:基于公眾訴求的新聞生產
傳統的新聞生產是一種科層制的生產體系,新聞生產方式和傳播渠道為專業傳媒組織所宰制,受眾處于被動接受地位;而新媒體技術賦予受眾參與新聞生產和傳播的權力和能力,不斷消解專業傳媒組織的權威,促使新聞脫離媒介機構和記者的控制,從新聞機構的壟斷性產品逐漸轉變為社會化的公共產品。過去是新聞機構、新聞記者、編輯部在決定新聞的價值、生產、傳播,現在是公眾的認知和需求取代了他們的威權判斷。新聞業與大眾結合得越緊密,大眾發揮決定新聞的作用越強,這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新聞理念、新聞生產流程以及新聞工作者角色。數據新聞正是這種價值變遷的集中體現:一方面,基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資源開掘是公眾新聞訴求的基本保障,將更多真正的公眾議題納入新聞視框;另一方面,基于數據采集、分析和呈現的新型新聞敘事方式和交互傳播模式,拓寬了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提升了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和能力。因此,數據新聞不僅是一種新型的新聞實踐,也是一種新型的社會實踐。
2.數據新聞:數據認識論與結構化信息
在精確新聞那里,數據是增加新聞客觀性和準確性的手段;在計算機輔助報道那里,數據分析的目的是揭示掩藏在數據中的新聞;而數據新聞是回歸數據本身,將數據作為新聞的來源,新聞的內容,新聞的價值所在和新聞意義的指向。作為“計算機可處理的數據”,數據新聞的目標是讓某些新聞(尤其是與受眾密切相關的新聞)凸顯出來,它是一種“被結構化的信息”,而結構化的目的在于讓數據呈現出相關性,呈現出意義,呈現出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數據新聞確立了一種新的數據認識論——在新媒體條件下,數據(大數據)能夠展現更真實、更豐富、更客觀、更準確的信息,甚至揭示某些未來的發展趨勢和意義(比如預測性報道)。
因此,開放數據資源和先進的數據分析工具是數據新聞生產的基本條件。進入21世紀,“開源運動”消除了信息的壁壘,持續增強了人們關于信息自由的信仰。美國大企業家、社會活動家、計算機愛好者和新聞記者也紛紛要求政府開放數據以便市民的政治參與。自2004年起,美國各級政府開始大規模的數據開放,這為數據新聞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6年拉開的“維基解密”,同樣激發了傳統媒體把新聞、數據與計算機技術相結合以創造數據產品的激情。此外,收集數據,建立數據庫,打造數據庫鏈接也是數據新聞的基礎性工作。特別是開發新型工具和軟件挖掘采集、分析處理復雜、龐大的數據(包括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無人機搜集到的傳感器數據),以及不斷開發新的敘事科技。
二、新實踐:從專業化生產到社會化生產
2012年,奧萊利(O’Reilly)公司出版了全球第一本專門探討數據新聞的著作《數據新聞手冊》,呈現了國際多個主流媒體數據新聞實踐的案例,探討了數據新聞的操作原則。2013年,約翰·梅爾(John Mair)、理查德·蘭斯·基伯爾(Richard Lance Keeble)編輯出版的《數據新聞:圖繪未來》呈現了最新的數據新聞技術,并結合最新的新聞事件(包括斯諾登泄密)闡釋數據新聞的意義。與此同時,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數據新聞實踐,部分學者對國外數據新聞實踐的概貌進行了引介,[5]尤其對《衛報》、美國《紐約時報》等先驅進行了個案分析和經驗概述;[6]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比較的視野中探討數據新聞實踐的得失。[7]那么,數據新聞實踐與傳統新聞實踐究竟有什么實質性區別?它在什么意義上標化一種新的行業發展趨向呢?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數據新聞實踐展現了一種從專業化生產到社會化生產的轉向,這尤其體現于新聞生產主體、新聞生產流程及新聞生產價值的變化等相面。
1.新聞生產主體——多元聚合
傳統新聞的生產主體是作為職業工作者的記者、編輯,而數據新聞的生產主體是多元主體的聚合:一方面,數據新聞生產不是簡單的新聞采集、寫作和編輯過程,而是復雜的數據抓取、挖掘、統計、分析、可視化呈現及傳播互動過程,這需要計算機程序開發設計人員、社會學家、統計學家以及其他專門性人才的參與,同時也需要用戶的信息反饋和互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數據新聞生產是一個擴大化的社會化生產過程,其主體是多元聚合體。另一方面,在數據新聞的生產過程中,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和工具是完成繁復的數據采集、分析工作,并以可視化方式予以呈現的前提,換言之,數據新聞生產是一種依賴于“機器”的新聞實踐活動,其生產主體也是人與“信息機器”的聚合體。
2.新聞生產流程——數據處理與甄別
數據新聞作為一種跨學科、跨領域的新聞生產,改變了傳統新聞生產方式和流程。在計算機輔助報道那里,采集、分析數據只是提升新聞報道質量的方法,數據分析僅僅作為新聞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而數據新聞徹底回到了數據本身。[8]米爾科·洛倫茲(M Lorenz)提出數據新聞報道四步驟:挖掘數據-過濾數據-數據可視化-新聞報道制作完成,每一步都代表對數據的不同處理,數據貫穿新聞報道全過程。[9]因此,數據新聞生產就是對數據的挖掘、分析、處理和呈現,這意味著數據新聞關注的不僅僅是單向度的信息生產——即那種基于對不確定性消除的信息生產,而是更著力于發現、分析、闡釋,甚至預測社會生活中的某些具有普泛性、影響力,卻藏匿于表面化、海量的數據之下的深度關聯和未來趨勢。
3.新聞生產價值——客觀認知與民主參與
在當代新聞報道中,對數據的使用本身就應歸功于普遍的民主化過程,而開放數據則彰顯了社會民主的提升,因此,數據新聞一開始就體現了對民主價值的開掘:首先,數據新聞提升了“客觀認識價值”,如果我們把新聞視為一種知識生產,那么數據新聞能夠提供比傳統新聞更為準確、客觀的知識,從而幫助大眾正確認識現實社會,正如羅杰斯所說:“與其把數據奉為真理或只追求其表面價值,還不如把它們當做一種補充材料,來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某一新聞選題的初衷。”[10]其次,數據新聞拓展了“大眾參與價值”,一方面,生產主體的多元化超越了科層制組織的局限性,將廣泛的非專業新聞工作者卷入數據新聞生產過程,尤其是其他領域的專家以及普通公眾;另一方面,數據新聞的互動性傳播為提升大眾政治參與提供了新的平臺和途徑。[11]再次,數據新聞彰顯了“民主監督價值”,數據新聞是基于一些開源數據的挖掘、分析和呈現,其中關涉對大量政府行為、行政管理和社會發展概況的反映和評價,這客觀強化了對政府的監督,更好實現了新聞的社會責任。[12]盡管“數據鴻溝”帶來的信息不平等,以及各國政府為追求信息安全而實行的數據限制、封鎖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礙著數據新聞民主價值的發揮,但是,數據新聞至少在有限范圍內已經表現出一種有效的民主價值了。
三、新傳播:面向用戶的傳播
確切地說,數據新聞開拓了一條面向用戶的傳播路徑——它不僅可以將數據轉化為新聞生產的資源和內容,更可以依托數據確定和設計新聞傳播的方向和形式,充分滿足新傳播革命語境下用戶對信息精準性、信息可視化和信息互動性的訴求。
1.精準性傳播
數據挖掘與分析不僅可以為數據新聞提供豐富的內容和素材,而且可以為數據新聞的傳播提供精準的用戶信息。通過對用戶接受習慣、使用行為、興趣愛好、個體特征等數據的分析,傳播者可以對用戶進行“點對點”的新聞信息推送,實現精準傳播,提升傳播效率,滿足用戶的個性化新聞訴求。
2.可視化傳播
從靜態信息圖示到交互式數據圖示,再到動態數據圖示,以及多媒體互動模式,數據新聞正在構建一種可視化傳播方式。通過計算機圖形、圖像處理,各種形象、直觀的視覺化元素成為數據新聞的有效載體,它們將龐冗繁復的數據轉化為簡單、易讀,具有審美價值的可視化信息,用戶不僅可以便捷地獲取和解讀數據新聞中包含的信息和意義,而且可以獲得豐富的審美體驗。
3.互動性傳播
在數據新聞的傳播過程中,數據與用戶有著深刻的關聯,用戶既是數據的接受者也是數據生產者和傳播者。雖然不是所有在線數據新聞都是互動的,但從美國的《紐約時報》(nytimes.com)、英國的《衛報》(guardian.co.uk)、英國的 BBC(bbc.co.uk)、德國的《明鏡周報》(spiegel.de)等展示的數據新聞都可以看出,互動性越來越成為數據新聞的魅力所在。互動性不斷結構化傳播過程,形成了用戶與數據新聞工作者的持續對話,從而構成一個延續的傳播序列。數據新聞的互動性常常決定這一序列的傳播時間、傳播范圍和傳播影響力,這種互動性可以分為“客體互動性”(比如《衛報》2010年關于伊拉克戰爭傷亡報道)、“線性互動性”(比如《衛報》的“解讀騷亂”)和高層次的“建構互動性”(比如《衛報》的“紀念撒切爾夫人”報道)。在這種互動傳播過程中,用戶可以自由選擇瀏覽數據的路徑,對新聞作出獨立判斷,甚至更改新聞內容。
四、結語
數據新聞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深刻的技術催化和行業調整動因:首先,新傳播革命為數據新聞的生產提供了技術支持——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革新及其在新聞編輯部的應用是數據新聞產生的重要原因,[13]它使得數據的挖掘、分析和可視化呈現成為可能,拓展了新聞來源、新聞素材、新聞呈現方式和傳播交流渠道,并催生了基于用戶數據分析的定制化新聞。其次,“數據開放決定數據新聞”。[14]國內不少學者從“大數據”視角剖析數據新聞,2013年,CNKI收錄的31篇研究數據新聞的論文中有15篇標題出現了“大數據”一詞,這充分說明開放數據,尤其是“大數據”的涌現成為數據新聞產生與發展的直接動因。再次,數據新聞也是媒體組織探索專業主義的新聞生產方式,應對科層制媒介生產方式被新媒體賦權運動消解的一種路徑。為了應對信息的過剩、透明、異質化、網絡化等帶來的沖擊,專業新聞生產召喚一種持續的創新機制,[15]數據新聞代表了一種從理念、實踐到傳播的嶄新新聞業嘗試——一方面,拓展新聞生產的專業性和價值,基于數據挖掘去呈現結構化的信息,以期反映社會生活的重大相面;另一方面,通過一種社會化的生產方式,將多元主體納入數據新聞的生產和互動過程,探索面向受眾新聞傳播方式。
注釋:
[1]蘇宏元,陳娟.從計算到數據新聞:計算機輔助報道的起源、發展、現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10)
[2]Mair J, Keeble R. (Edited), Data Journalism: Mapping the Future,UK:Abramis Academic Publishing. 2013
[3][15]Gynnild Astrid, “Journalism innovation leads to innovation journalism:The impact of 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 on changing mindsets”,Journalism. 2014, Vol. 15(6)
[4][5]方潔,顏冬.全球視野下的“數據新聞”理念與實踐[J].國際新聞界,2013(6)
[6]鄭若琪.英國《衛報》:以開放式新聞構建數字化商業模式[J].南方電視學刊,2012(6);章戈浩.作為開放新聞的數據新聞——英國《衛報》的數據新聞實踐[J].新聞記者,2013(6)
[7]劉義昆.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新聞生產: 現狀、影響與反思 [J].現代傳播,2014(11): 103-106;劉義昆,盧志坤.數據新聞的中國實踐與中外差異[J].中國出版,2014(20)
[8]Gray J, Chambers L and Bounegru L, 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O’Reilly Media, Sebastopol, 2012
[9]Lorenz, Mirko, “Data driven journalism: What is there to learn?”,Presented at IJ-7 Innovation Journalism Conference,Stanford, CA, 7-9 June 2010.
[10][14][英]西蒙·羅杰斯.數據新聞大趨勢:釋放可視化報道的力量[M].岳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11]Fenton Natalie (edited), New Media, Old news: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0
[12]James T. Hamilton, and Fred Turner , “Accountability through Algorithm: Developing the Field of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In Report from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Summer Workshop, Stanford, CA. 2009
[13]陳虹,秦靜.數據新聞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趨勢[J].編輯之友,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