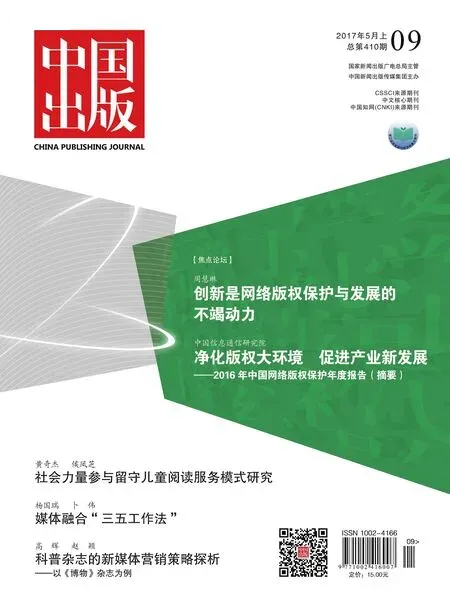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綏遠報紙期刊對綏遠文學的影響
□文│劉志中
綏遠原為我國一個省級行政區,清代因有綏遠將軍駐守歸化,在其東北建綏遠城,后兩城合稱歸綏。1914年稱綏遠特別區,1928年改稱綏遠省,省會為歸綏(今呼和浩特市)。1954年撤銷省級建制,歸并到內蒙古自治區。原綏遠地區其所轄范圍為以歸綏為中心,東到烏蘭察布市興和縣,西到今天的烏海市,現在也常籠統地稱為內蒙古西部地區。綏遠地區位于偏遠的西北,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后。但自民國時期起,這里也逐漸出現了一些報紙期刊,宣傳進步思想文化,與內地加強了聯系。這些報紙期刊也對綏遠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官方和民間共同推動報刊發展
據忒莫勒先生考證,內蒙古西部地區最早的漢文報紙是《歸綏日報》和《牗報》,約在1913年初印行,其后又出現過《一報》等10余種小報,但都存續時間不長。[1]到1918年,《西北實業報》創刊,這份由綏遠總商會主辦的鉛印報紙,對開四版,刊載內容除時政要聞、經濟、評論之外,還有小說、文苑、新劇欄等文藝性的欄目,最多時能夠每日發行七八百份,在當時有較大的影響。
1919年,在北平學習的綏遠籍學生創辦了《綏遠旅京學會半月刊》(后改稱《綏遠旅平學會學刊》),這是綏遠地區第一份期刊,它雖然在北平印刷,但“以增進同學感情,促進地方文化,探討學問,批評時政為宗旨”,撰稿者都為綏遠籍人,刊載內容也多與綏遠有關。這份綜合性刊物一直堅持到1937年才被迫停刊。
1925年,馮玉祥出任西北邊防督辦,駐守包頭,關注綏遠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在他的支持下,綏遠文化界開始活躍起來。共產黨員蔣聽松、胡英初受李大釗委派,在包頭創辦了《西北民報》,以西北邊防督辦公署機關報的名義出版。該報有政論性欄目《先鋒》,綜合性欄目《樂園》,還有文藝副刊《火坑》。受馮玉祥進步思想影響,在綏遠都統李鳴鐘和教育廳廳長沙明遠的推動下,綏遠通俗教育講演所創辦了《綏遠通俗日報》,綏遠教育廳出版了《綏遠教育季刊》和《綏遠月刊》。
1928年綏遠改為省級建制,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創辦了《綏遠蒙文周報》,一年后改為《綏遠蒙文半月刊》。1930年,綏遠省政府創辦了《綏遠日報》作為自己的機關報。此時,屬于省政府系統的報紙有《綏遠日報》《綏遠社會日報》《綏遠蒙文半月刊》《綏遠省政府公報》《綏遠省政府年刊》等近20種刊物;屬于國民黨省黨部系統的報刊有《綏遠民國日報》《綏遠朝報》《蒙文周報》《綏遠西北日報》等,加上各地黨部的《包頭日報》《包頭通訊》《武川周報》等報,共有20多種,此外還有屬于軍隊系統的一些報刊。其中《綏遠民國日報》《綏遠日報》《綏遠朝報》等影響較大的報紙,日銷量可以超過一千份。[2]
有些報紙還采取了蒙漢文合刊的形式,“《綏遠蒙文半月刊》和《蒙文周報》是國民黨報刊中采用‘蒙漢合璧’形式的代表”。[3]在官方報紙活躍的同時,也有一些民間報刊出現,但多為曇花一現,持續時間不長。到1935年《何梅協定》簽署后,國民黨系統的報刊多數關閉,僅有3家未公開實際身份的報紙仍在出刊。至1937年日軍攻占歸綏,綏遠地區的報刊自然無法再辦,有少數轉移到陜壩地區堅持下來。
除了報紙副刊,還有一些是以單行本或期刊形式來發行的文學刊物,如以油印、鉛印形式發行的有《火坑》《燕然》《血星》等。但它們與報紙副刊的聯系相當緊密,撰稿者也多是副刊的投稿人。
二、推動了當地的文化發展
綏遠地區的這些報紙期刊,對于開啟民智、發展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報道時政要聞、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之外,它們還多辦有文藝副刊,登載文學作品,反映時代的心聲和人民的愿望。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綏遠成為日軍向西侵略的主要目標,報紙期刊在宣傳抗日方面也發揮出了戰斗力。盡管有些報紙是隸屬于國民黨省黨部系統的,但綏遠地區離國民黨的統治中心較遠,加之傅作義與南京政府有矛盾,并未在文化方面對左翼力量進行過多的壓制,綏遠的左翼文學就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間。著名報人楊令德早年加入了國民黨,但他與共產黨人的關系也很好,對左翼文學多有扶持。總體來說,綏遠報刊上的文學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對國內外著名作家的介紹。對國外著名作家的譯介,有高爾基、普希金、托爾斯泰、囂俄(雨果)、莫泊桑、歌德等人,對國內著名作家的介紹,有魯迅、廬隱、劉半農、巴金、孫伏園、沈從文、宋之的等。可以說,這時的綏遠文藝界已經與內地文藝界有了較多的聯系,有時會直接參與到最前沿的文藝評論和思想論爭中。如楊令德1928年在《火坑》上刊載文章,評論沈從文的小說集《蜜柑》。《綏遠民國日報》的“十字街頭”副刊,則在1934年8月連續刊發了趙守謙的4篇評論廬隱小說的文章。魯迅逝世后,綏遠文學界也發表了不少悼念文章。
參與國內的文學運動。綏遠報刊上有一些對國內詩歌創作的宏觀分析,使得綏遠文學溶入現代中國文學中,成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章葉頻的《現在詩壇兩種流派的斗爭》批評了當時風行一時的新月詩派和以戴望舒為代表的象征主義詩歌,認為它們表現了過多的傷感、頹廢和幻滅,嚴重脫離現實,只能到“愛和死的夢的王國逡巡”。而章氏極力贊同的,則是中國詩歌會所倡導的現實主義的大眾化的詩歌。在《一九三五年中國詩壇》一文中,章葉頻認為,在1932年9月之后,原來的注重形式的、唯美的和傷感情調的詩逐漸被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所代替。他介紹了當年刊出的詩歌刊物以及一些詩人出版的詩集,指出了詩歌“必須要反映時代的精神和人民的心聲”的發展方向。
除了這些評論文字,綏遠文學界還更直接地參與到國內的文學運動中。在左聯影響下,國內詩歌界的進步詩人成立了中國詩歌會,又在北平、天津、廣州、河北等地成立了分會。綏遠塞原社也積極響應,組織了“塞原社詩歌研究會”,開展新詩歌運動。他們通過左聯與青島、廣州等地的中國詩歌會取得聯系,交流信息,互寄刊物,互相投稿,還在綏遠出售了部分詩人的詩集。這些文學活動使綏遠文學界能夠緊貼全國詩歌創作的血脈,在詩歌創作技巧、題材、文學的戰斗性功能等方面,形成一致的看法,促使綏遠的創作者們從“為藝術而藝術”的狹小天地里走出來,寫出了一批反映大眾生活的現實主義詩歌。
三、為社會時政發聲
綏遠報紙期刊作為文學載體,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當地文學的發展,其體現出以下特點。
能夠迅速及時地反映時代生活的熱點,發出有力的聲音。盡管由于政治力量分散、經濟實力不足等諸多原因導致了很多刊物存世時間不長,但由眾多報刊團結起來的文化界人士,在綏遠形成了推動文化發展的合力。
“九·一八事變”之后,綏遠成為抗日前線,因此這里的抗日宣傳活動一直很活躍。早在1932年,蘇謙益、馬映光、劉洪河等人即著文討論革命文學的任務。到1936年,章葉頻、馬映光等人又在《綏遠西北日報》的《塞風》副刊上撰寫文章參與國防文學的討論。章葉頻認為,要把正義的力量團結起來,“無論你是民族主義者、唯美主義者、自然主義者、浪漫主義者與蝴蝶鴛鴦派、禮拜六派以及最進步的現實主義者,只要你不賣國、不做漢奸,認為抗日救亡是我們民族當前的急務,你就是同一戰線上的戰友,你就可以加入這個戰線,把你的筆桿用作抗日反漢奸的工具,來對準共同的敵人”。[4]馬映光認為,“國防文藝在這國防最前線的綏遠,可以說是僅展開了初期的運動……愛國民眾和抗敵軍人的救國熱情……都是我們最好的主題……國防文藝的題材雖然是多方面的,都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使民眾了解正確的國防的意義,促進抗戰救國的決心,形成普遍的一致的、堅強的抵抗侵略的陣營,這是我們文藝青年目前應負的使命”。[5]
1936年在《綏遠西北日報》上又出現了《邊防文壘》副刊,王毅然主編,這是在傅作義綏東抗戰后創刊的,其目的在“開辟文化荒地,集中國防第一線上的文化戰士,使荒蕪的塞外,成為一個文化燦爛的國度,并聯合后方大眾,配合著前線戰士的步調,一致向前抗敵,使這個僅存的國防線得到鋼鐵般的堅固”。這個副刊每期都有時局評論,發表的一些抗日救亡內容的詩歌也受到歡迎,如陳一之的《誰說好人不當兵》,在當時綏東抗戰取得勝利的背景下引發了強烈反響。
抨擊時政,指斥不良風氣。綏遠早期創辦《一報》的王定圻即是因為針砭時政而遭人忌恨,在反袁活動中被槍殺。楊令德在1934年的一篇隨筆中,以宋末襄陽主將投降一事做比,指斥湯玉麟賣國求榮。楊植霖的《開刀只有幾日了》對當局年年下禁毒令,但卻有令不行、形同虛設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不滿。《綏遠旅平學會會刊》刊有起生的文章《由武川第二區區長仝致珍逃跑說到綏遠政治》,仝致珍因貪腐事敗露而逃跑,但縣政府僅將其撤職了事。有些文章還涉及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如《綏遠旅平學會學刊》上登載的張遐民的《綏遠省鈔價格跌落的因果及今后整理的管見》一文,即對綏遠紙鈔不斷貶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今后進行整改的意見。
《寫在李主席就職之后》則對綏遠政府治理匪患不力提出了嚴厲批評,并認為應該標本兼治,一面要處理匪首,另一面也要消除貧民為匪的根源,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另有《對包頭公安局的一點意見》《向包頭司法當局進一言》《為減輕綏民負擔進一言》等文章,從題目上就可以見出其指向。這些文章雖不像魯迅的雜文那樣犀利,但也是談論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對時政有進言,對不良風氣有批判。
培養和凝聚了創作隊伍,提高了文學創作水平。綏遠地區在20世紀20年代戰亂頻仍,“城頭變幻大王旗”是常有的事,遂使得民生凋敝,也成為文化沙漠。綏遠進步作家的文學活動和創作成績極大地改變了這種文化落后的狀況。得益于楊令德等早期報人的支持,文學界利用報紙副刊的形式發展文學。早期給《火坑》副刊投稿的作者,形成了較為松散的火坑社,后來又以《塞原》副刊為中心形成了塞原社,其他的文學社團還有心波社、燕然社、綏中文藝研究會、挺進社、小喇叭社等,圍繞在這些社團周圍的活躍作者達30多人,盡管他們內部有時會有對文學的不同看法,但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會以大局為重,團結在一起。他們成立的“綏遠文藝界抗敵協會”即是證明。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