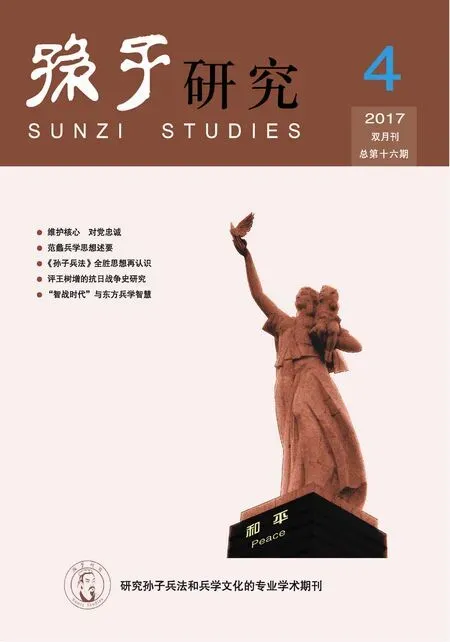鄭國人的空城計(jì)
鄭國人的空城計(jì)
空城計(jì)是三十六計(jì)之一,一般人都知道諸葛亮的空城計(jì),但很少有人知道比諸葛亮早700年的鄭國人的空城計(jì)。
鄭國是春秋時(shí)期十二諸侯之一,在今河南省新鄭市一帶。鄭國的開國之君是周宣王的弟弟季友,本封于陜西的西都畿內(nèi),周都東遷以后,鄭武公亦東遷鄭國到今河南,故稱“新鄭”。鄭國南靠楚國,北鄰中原諸侯。楚國是所謂“蠻夷”,不服從周的領(lǐng)導(dǎo),所以經(jīng)常侵犯別國,且有問鼎中原之勢(shì)。鄭國夾在楚國和晉國等國之間,是春秋時(shí)期發(fā)生戰(zhàn)爭最多的地方。
公元前666年,楚國的宰相“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左傳·莊公二十八年》),這比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早了150年,其出兵規(guī)模在當(dāng)時(shí)是罕見的。子元以斗御強(qiáng)、斗梧、耿直不必為前軍,以斗班、王孫游殿后,自己將中軍。楚軍之所以出動(dòng)如此大的兵力,主要是為應(yīng)對(duì)中原諸侯增援鄭國。
楚軍進(jìn)入鄭國遠(yuǎn)郊的“桔柣之門”,并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楚軍繼續(xù)進(jìn)軍,進(jìn)入鄭國都城外郭的“純門”,到達(dá)了郭內(nèi)的“逵市”,鄭國人仍無動(dòng)靜。市場上的人對(duì)楚軍的侵入似乎并不在意。鄭國人在楚軍到來后的平靜,讓楚軍感到意外和震驚。再往里走就是鄭國的內(nèi)城大門了。為了防御敵軍的入侵,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國家用的都是懸著的閘門。看看鄭都的城門“懸門不發(fā)”,連城門都不關(guān),這時(shí)從城里走出來一些人,他們邊走邊談,都說的是楚語。這讓楚軍大生疑惑,子元怕城中有伏兵,不敢進(jìn)城。他說:“鄭有人焉。”杜預(yù)注此說:“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jìn)。”這和諸葛亮的空城計(jì)是相同的,子元就很像是司馬懿,說不定諸葛亮之計(jì)就是從《左傳》中學(xué)來的。子元不敢貿(mào)然進(jìn)入鄭國都城,他退兵暫駐郊外。
而這時(shí)城內(nèi)的鄭國人,一方面密切注視城外的楚軍動(dòng)向,一方面在抓緊時(shí)間做著逃往桐丘城的準(zhǔn)備,桐丘在今河南許昌市東。鄭國自知無法抵抗楚國的入侵,早在探知楚軍侵鄭后,就派人向各國求救兵,在救兵未到之前,鄭國人冒險(xiǎn)了用空城計(jì),還真把楚帥子元嚇唬住了。
楚軍駐在鄭城郊外,偵探報(bào)告諸侯救鄭國的大兵來到。子元怕受鄭國和諸侯的內(nèi)外夾擊,夜間就下令撤兵而去。這時(shí)鄭國人正想趁天尚未明奔桐丘,忽然,“諜告曰:楚幕有烏。”鄭國人知道這是烏鴉到楚軍的營地吃食,說明楚軍已撤走,才停止了“奔桐丘”的準(zhǔn)備。
孫子論兵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yuǎn),遠(yuǎn)而示之近。……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空城計(jì)實(shí)際是虛而示之實(shí),不能而示之能,緊張而示之閑暇。鄭國人用此計(jì)糊弄了楚國人不足一天,諸侯救兵一到,鄭國就不怕了。楚國宰相子元自知不敵多國聯(lián)軍,所以也就退兵而去了。
(名崗 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