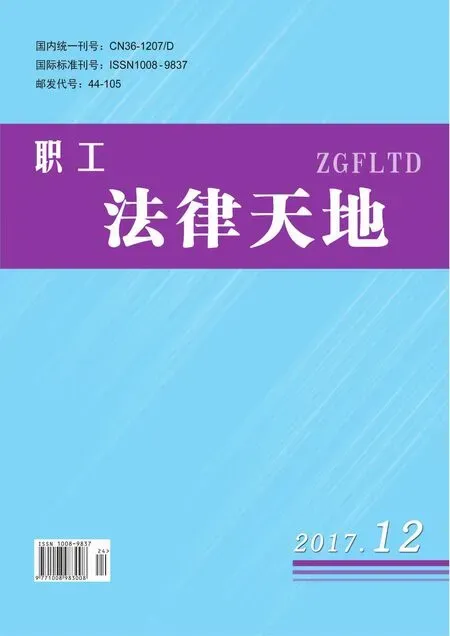淺談不當得利的法律制度
——以A公司不當得利糾紛案為例
王其委
(317200 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 浙江 天臺)
淺談不當得利的法律制度
——以A公司不當得利糾紛案為例
王其委
(317200 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 浙江 天臺)
不當得利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嚴格的構成要件及適用范圍,不能作為當事人在其他具體民事法律關系中缺少證據時的請求權基礎。借貸糾紛案件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被駁回后,當事人又以不當得利為由另行起訴主張權利的,不予支持。
不當得利;企業(yè)借貸;民事法律關系;請求權基礎
案情簡介
原告A公司系經營普通貨運,金屬材料、建筑裝潢材料、五金交電、機電設備的批發(fā)、零售的公司。被告B公司系經營房屋工程建筑、建筑安裝、工廠生產設備安裝、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筑裝飾、園林綠化;苗木、裝潢材料(不含化學危險品)、建筑材料、建筑機械銷售的公司。2012年12月11日,A公司將350000元款項匯入B公司銀行賬戶,2013年1月31日,A公司將800000元款項匯入B公司賬戶,上述兩筆款項的轉賬憑證中用途均載明為往來款。2014年10月17日,原告向寧波市鄞州區(qū)人民法院以企業(yè)借貸糾紛為由起訴被告,2015年2月7日,寧波市鄞州區(qū)人民法院作出(2014)甬鄞商初字第1779號民事判決,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對該判決不服向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5年6月9日,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甬商終字第358號民事判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現原告以不當得利為由向本院起訴,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返還不當得利的款項人民幣1150000元及孳息(其中350000元的孳息自2012年12月11日開始起算;800000元的孳息自2013年1月31日開始起算,均計算至不當得利款項還清之日止)。本案經本院審理,依法駁回了原告A公司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原告A公司起訴稱:原告通過開立在寧波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州支行的賬戶分別于2012年12月11日、2013年1月31日向被告以轉賬方式匯款350000元、800000元,上述款項合計人民幣1150000元。原告原本認為該款項系原告借給被告的借款,其應予以歸還,但雖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歸還,故原告于2014年10月17日以企業(yè)借貸糾紛為由向寧波市鄞州區(qū)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返還上述款項。鄞州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原告僅憑銀行匯款這一事實尚不足以證明雙方存在借貸關系,故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借款的訴訟請求。后原告上訴至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原告認為,被告B公司收到原告的1150000元款項是事實,既然被告不承認其寧波分公司與原告之間存在借貸關系,被告應對其取得原告1150000元款項的合法根據作出說明并提交相應證據,但被告在一審、二審期間均未對其取得該1150000元款項的合法根據作出說明,也未提交相應的證據。故原告與被告之間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債權債務關系,既然被告既不承認與原告存在借貸關系又無法對其取得原告1150000元款項的合法根據作出說明,則該1150000元款項應認定為系被告的不當得利,并應賠償原告相應的損失。故原告起訴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還不當得利的款項人民幣1150000元及孳息(其中350000元的孳息自2012年12月11日開始起算;800000元的孳息自2013年1月31日開始起算,均計算至不當得利款項還清之日止)。
被告B公司辯稱:一、2014年10月17日,原告曾以企業(yè)借貸起訴,駁回訴訟請求后,現已同一事實、理由和證據起訴,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則,依法應駁回原告的起訴。二、本案的舉證責任應由原告承擔。不當得利無法律上的給付原因,并非單純的消極事實,應當由本案的原告對給付欠缺原因的具體情形予以舉證,并不能因為答辯人否認是借款而發(fā)生舉證責任上的倒置。三、原告在民間借貸的主張不被支持后,以不當得利起訴不應得到支持。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被告B公司收到原告A公司的1150000元款項是否系不當得利?
而在上述爭議焦點中,不當得利欠缺法律上的給付原因由原、被告哪一方承擔舉證責任是雙方的爭議之一。原告認為,被告B公司收到原告的1150000元款項是事實,既然被告不承認其與原告之間存在借貸關系,被告應對其取得原告1150000元款項的合法根據作出說明并提交相應證據,但被告在一審、二審期間均未對其取得該1150000元款項的合法根據作出說明,也未提交相應的證據。故原告與被告之間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債權債務關系,既然被告既不承認與原告存在借貸關系又無法對其取得原告1150000元款項的合法根據作出說明,則該1150000元款項應認定為系被告B公司的不當得利。也就是說,原告認為不當得利欠缺法律上的給付原因的舉證責任由被告B公司承擔。我們認為,“誰主張、誰舉證”系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而現行法律并未對不當得利規(guī)定除外的舉證規(guī)則,因此仍應將該原則視為分配舉證責任的基礎性因素;且本案中不當得利請求權人(即原告)系控制財產資源的變動主體,在付款時完全基于其意思表示控制財產變動,故應由原告就欠缺給付原因的具體情形承擔舉證責任更為合理。而本案所涉1150000元原告曾以企業(yè)借貸糾紛為由向法院起訴,后因證據不足而敗訴,故本案所涉1150000元并不存在欠缺法律上的給付原因;且原告在本案中亦沒有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給付被告1150000元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故原告所主張的其給付被告1150000元系不當得利的請求不能成立。
不當得利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嚴格的構成要件及適用范圍,不能作為當事人在其他具體民事法律關系中缺少證據時的請求權基礎。借貸糾紛案件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被駁回后,當事人又以不當得利為由另行起訴主張權利的,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原主張與被告形成企業(yè)借貸關系,后因證據不足被駁回訴訟請求,現原告以不當得利另行起訴,但上述事實并不因此導致原、被告之間法律關系本身發(fā)生了變化,即并不存在法律關系由此轉化為不當得利,由此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原告所陳述的由借貸法律關系轉化為不當得利法律關系。故原告在借貸關系得不到支持后,以不當得利進行訴訟無事實與法律依據,依法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為此,本案在一、二審中以相同的觀點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