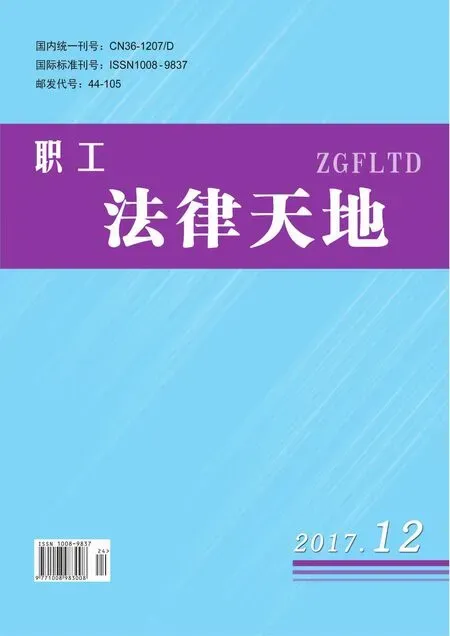《鹿特丹規則》之海運履約方制度評析
劉 昶
(201306 上海海事大學 上海)
《鹿特丹規則》之海運履約方制度評析
劉 昶
(201306 上海海事大學 上海)
2008年12月,《聯合國全程或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下文之中簡稱《鹿特丹規則》)于紐約聯合國大會通過。其中,為達成擴大公約覆蓋面的目的,本公約將為承運人所委托,履行前者在運輸合同下相關義務的其他方亦囊括至其適用范圍,使之依公約的規制對貨方承負責任。對比借鑒《漢堡規則》“實際承運人”制度,本公約開創性地在海上貨運法律中啟用“履約方”、“海運履約方”的新概念,并規定了一系列完備的海運履約方制度。本文通過評析海運履約方制度,闡述了海運履約方的責任, 對海運履約方的責任期間、歸責原則以及連帶賠償責任制度設計進行具體闡述。
鹿特丹規則;海運履約方;實際承運人
一、研究背景
貿易全球化的進程使得其載體——國際航運業也隨之產生了爆炸式的變化。國際標準化趨勢下集裝箱貿易的繁榮,運輸方式由單式運輸發展為多式聯運,國際海運實踐中的“Hook to hook”、“Port to port”擴展到了“Door to door”,這使得參與整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履行過程中的主體越來越多的參與其中。過去的承運人免責制度設計顯然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國際貿易中層出不窮的糾紛。
《鹿特丹規則》與三大公約相比,自然出現了許多新的變革,涉及層面紛繁且廣博。因此,自起草至通過的數十年進程之中,一直有著極高的關注度,就公約本身國內外各學術及實務界對其褒貶不一,公約在短時間內亦難以獲得使之生效的法定簽署國數量,達成需要各方漫長的溝通乃至妥協。其中,“海運履約方”責任制度是該公約的一大亮點,為改善國際海運中各種司法認識不一致的狀況提供了很好的解決途徑,亦為我國《海商法》革新和海運實務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借鑒意義。本設計初衷是解決國際海運中紛繁復雜的法律關系,是平行于承運人制度的一個新型制度,以及與之配套的一系列具體賠償機制。 鑒于我國港口經營人不明確的法律地位以及責任限制上存在的諸多爭議,海運履約方制度對我國《海商法》的完善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海運履約方制度對國際海運立法及我國海商事立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以及深遠的影響。
二、《鹿特丹規則》下海運履約方制度設計
《鹿特丹規則》所創造的海運履約方相關的賠償制度有著前所未有的創新深度,其中,該概念下深度囊括了部分未將船舶作為運輸工具而對其他運輸環節負責的人。對于廣大承運人來講,該項創舉通過國際公約的方式打破了相對性原則的限制,衍生出與之責任地位平行的其他賠償方,使得托運人獲得了更寬廣的獲賠渠道,從而使得有關維權體系完善化。基于合同相對性原則限制的突破,使得本應排除于合同外的第三方,通過法律規制或者雙方意思自治,在擁有有關項下的所有或部分之權利的同時也負擔對應之義務。
有關制度設計方面,首先,《鹿特丹規則》第十二條,直截了當地對承運人責任期間做出詳盡闡述。即以承運人、履約方以運輸為目的而接納貨物作為起算點,將貨物交付至收貨人為終點。其次,公約第十九條中,專門涉及到海運履約方的責任期間,這其中,表述清晰地指定了相關的三個期間。此處可將承運人和海運履約方的責任區間做出對比,承運人需要依照合同要求對于全程運輸負責,而后者僅需對自己負責運輸的路段貨損予以負責。最后,根據前文的概念闡述,在相關的實踐中分為實際履行和承諾履行,而后者的情況下也必須在相應期間內負責;然而,在這個設定之下,會出現人貨分離的情形,即貨物并非在承諾履行一方下,反而由實際履行的海運履約方所控制。由此推斷,后段責任期間處于一個真空期,貨主在實踐中面臨兩難的困境。承諾履行的內涵如何界定的問題亟待解決。
在歸責原則上,通過對鹿特丹規則的綜合立體分析,以及對于第十七條有關賠償責任基礎的規定,不難得出結論,新公約中適用于承運人和海運履約方的歸責原則,其獨創性在于,堅持公平調劑各方利益的原則,汲取之前責任制度的科學性部分,創立符合新世紀航運業發展的前景的責任制度以及歸責原則。
公約十七條所建立的歸責體系非常細致入微,基本是按照以下的流程:貨方率先提交兩項結合的初步舉證環節,然后由承運人舉證其本人無過錯或者公約所確切闡述出的免責原因,此環節達成后,舉證責任再次落回符合尋常舉證邏輯的索賠貨方之上,由其證明對應第四款或者第五款中的任何一條。新的歸責體系為承托雙方建立了充分的博弈平臺。
有關承運人與海運履約方之間的賠償責任關系上,公約在第十八條中,采用條款詳細規范了承運人所負的相關轉承責任。嚴格的無過錯責任制適用于以上情況,即不管承運人在其責任期間內有無過錯,一旦滿足違反公約對于相關義務規制的條件,轉承責任旋即觸發,賠償責任轉為承運人負擔。
首先,盡管在海運履約方的責任方面,公約做出了特殊規定,然而承運人依舊不可免除對履約方承擔責任,此類做法亦是考量了相對性原則的限制而產生。其次,公約所制定的轉承責任,同時充分考慮到了經濟效率的問題。一般來說,在世界海上運輸實踐中,承運人通常不親自履行全部貨運的任務,而是選擇將義務轉交與第三方分工履行。出于以上的原因,鹿特丹規則做出了承運人轉承責任的條款。類似的編纂思想亦能在公約第十九條第三款中發現。
三、結論
隨著海上貨物運輸情況日益復雜,三大公約以及其他國際國內海運立法的滯后性在應對實踐中的諸多問題上產生了重重爭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臺的《鹿特丹規則》是一部與時俱進、力圖實現各國海運法統一的新的國際海運公約。我們應該積極研究和借鑒《鹿特丹規則》,尤其是最具創新的海運履約方制度。本文建議,我國不加入公約,僅部分接受海運履約方制度,科學地借鑒靈活地運用,以解決出現的實際承運人制度和港口經營人制度問題,進而完善我國的海商法律制度,促進我國海運事業更好的發展。
[1]胡正良,《鹿特丹規則》影響與對策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朱曾杰,郭瑜,《鹿特丹規則釋義》,[M],商務出版社,2011.
劉昶(1994~ ),性別:男,學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