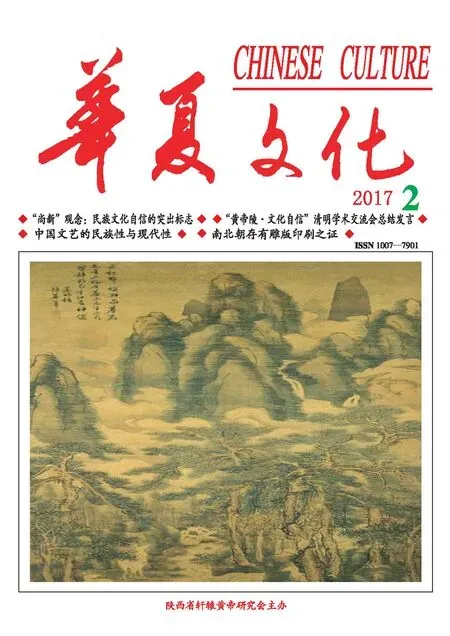清明節與寒食節的糾葛
□ 梁麗紅
清明節與寒食節的糾葛
□ 梁麗紅
國務院于2006年5月20日正式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清明節便名列其中,其重要的文化價值可見一斑。但不管是與人交談,還是課堂教學,我發現為數不少的人以今天的民俗為準,認定清明節就是寒食節,甚至把二者的來歷都當成是一樣的,謬之甚遠。
一、 清明與寒食的起源
清明,夏歷二十四節氣之一,其由來已久,《逸周書·時訓》就有記載:“春分之日玄鳥至……清明之日萍始生……。”一般在農歷三月初一前后(公歷4月4-6日),《歷書》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歲時百問》亦云:“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故謂之清明。”據上可知,“清明”一名源起于物候變化,是對自然界景致貼切的描繪。也有學者認為“清明”源于“清明風”,《國語》中記載,一年中共有“八風”,東南風叫清明風,屬巽,即“陽氣上升,萬物齊巽”(雨竹《漫話清明節與寒食節》,《神州》2012年第10期)。不論哪種說法,我們都有理由相信清明初始僅僅是一個農業節氣,用于區分時序,指導農事,與節日毫不相干。今天所流行的許多諺語:“清明前后,種瓜種豆”、“清明忙種麥,谷雨種大田”等亦可資佐證。
寒食,顧名思義,吃冷食,又稱為“禁煙節”。關于寒食節的起源目前尚無定論,主要有以下五種說法:周代禁火說、古代改火說、紀念介子推說、山戎習俗說、求雨說,后兩種說法立論薄弱,支持者少;前三種說法爭論激烈,支持者眾。細細梳理現有論述,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主張周代禁火說與古代改火說的多為歷史學家;主張紀念介子推說的多為民俗學家。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歷史學家用史料說話,理性闡述,而民俗學家則從民眾的情感出發,感性解讀。面對學術界熾熱的爭論到底該何去何從?
查閱史料可知,關于介子推的記載最早見于《左傳》僖公廿四年,但云“遂隱而死”,并非焚死。此后的《呂氏春秋·介立》、《史記·晉世家》也未見焚死的記載。《莊子·盜跖》中首次出現了“抱木而燔死”的說法,到了西漢時期,劉向的《新序·節士》詳細地描繪了介子推被焚死的過程,之后此說不斷被延續和豐富。據此,裘錫圭先生說:“這顯然是為了解釋寒食的起源而編造出來的。”確實,從關于介子推記載的演變可以看出,其故事并非完全真實的,而是層累地造成的,但能否因此就否認寒食的起源與介子推故事的密切關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七夕節的起源一樣,不能因為否認牛郎織女故事的真實性,就否認七夕節起源于此。一般說來,節日產生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自上而下的,通過政令規定某月某日是某某節日;一種是自下而上的,由部分民眾自發組織產生,后蔓延至更廣闊的地域,最終得到朝廷或政府的認可。查閱史料可知,周舉、曹操、石勒、孝文帝等統治者均先后禁斷過寒食,故可推測寒食節當屬于自下而上興起的,故而才會一再被朝廷禁止。作為民眾自發組織產生的節日,感性自然多于理性,普通民眾決不會去查閱史料辨別介子推的故事是真是假,只會依據個人喜好進行傳播,甚至加入一些個人的意識。對此,張勃說:“介子推傳說,作為民眾對于社會過程的闡釋和解讀,是民眾主體在其心理作用下,在一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之中進行的,是在集體無意識和個體有意識的互動中加工和創作的結果。與此同時,它的傳承和播布也是一個或多個時代、區域、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不斷篩選優化的結果,其中融匯了一個地域或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審美意識、道德觀念和政治理想。”(張勃《寒食節起源新論》,《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民眾創造一種方式對一個符合自己價值觀的英雄進行紀念是極有可能的。另,據史料記載,早期寒食之地基本局限于以太原郡為中心的并州地區,而介子推是晉國人,傳說其被焚死在介休,二者空間上吻合。如果是因為改火或者禁火而寒食,為何關于寒食的早期記載未見于其他地區?這難以講通。再次,關于介子推的傳說成熟于西漢,而現存關于寒食的最早記載也出現于西漢。桓譚《新論·離事》記載:“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二者時間上也契合。綜上所述,寒食節的起源必與紀念介子推有關,史書記載具體日期的不同及時間長短的差異只能說明寒食節形成的初期還不具穩定性,時常發生變動。
二、 清明與寒食的融合
一個是節氣,用于區分時序,指導農事;一個是節日,用于紀念先賢,表達哀思,它們是如何相互融合,以至于今人極易將其混為一談的呢?據楊琳先生考證,唐朝以前清明基本還僅僅是作為節氣存在的,“沒有形成節日的規模和氣氛,沒有形成全民遵從的禮俗和持續不斷的傳統,因而還不能稱為節日。”(楊琳《清明節考源》,《尋根》1996年第2期)而寒食自西漢時期出現伊始,也僅局限于以太原郡為中心的并州地區,其典型的民俗事象便是禁煙、吃冷食,抑或在某些地區還有祭祀介子推的習俗,《后漢書·周舉傳》記載“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口的大遷徙,寒食節開始得到廣泛的傳播,祭祀介子推慢慢演變為祭祀先人,至唐朝時期,唐玄宗的一道圣旨將寒食上墳祭祖定為“恒式”。《通典》卷五十二記載:“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于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余饌任于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甚至還為此全國放假,《唐會要》卷八十二記載:“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為假’。至大歷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準元日節,前后各給三日。’”這一舉動更推動了寒食祭祖的擴大化,于是乎,到了寒食人人上墳,家家祭祖,蔚成風氣。但由于在禁煙的寒食節上墳祭祖,無法焚燒紙錢,不少人擔心“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王建《寒食行》)于是,民眾越來越傾向于在可以用火且與寒食時間相近的清明上墳祭祖,焚燒紙錢,清明便與寒食有了最初的交融。唐詩中常見對寒食民俗事象的描述,如“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雖也有稱清明的,如“寂寞清明日,蕭條司馬家”,但此時寒食的稱謂還處于主導地位,“到后世,禁火寒食的習俗因紀念對象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及思想情感關系甚淺而日漸淡漠,清明祭祖則因符合民情物望而喧賓奪主,延續至今。”(楊琳《清明節考源》,《尋根》1996年第2期)寒食節將掃墓、祭祖等節日習俗讓渡給清明后,又隨著禁煙、吃冷食等陋俗的淡化,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而清明則從農時節氣蛻變為一個肅穆的節日。另外,清明出游踏青的習俗則是繼承了上巳節的傳統,因此,清明具有雙重性。
綜上,清明本為一個農業節氣,由于時間與寒食節相近,到唐朝時開始逐漸侵占寒食節的掃墓、飲食等節日習俗,后來隨著寒食節的式微,清明一躍成為一個重要的節日。寒食節則起源于介子推的傳說,早期主要在并州地區流行,后輻射至更遠的地區,其主要習俗是禁煙、吃冷食,至唐朝時才增加了上墳祭祖的習俗,但此習俗不久便被清明侵占,至宋代以后,隨著禁煙習俗的淡化,寒食節也慢慢被清明節取代,故而今人多只知清明,而不知寒食。歷史是動態的,在綿延的歷史長河中,不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習俗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所實踐的,都是其不斷演變的結果。
(作者:廣東省廣州市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郵編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