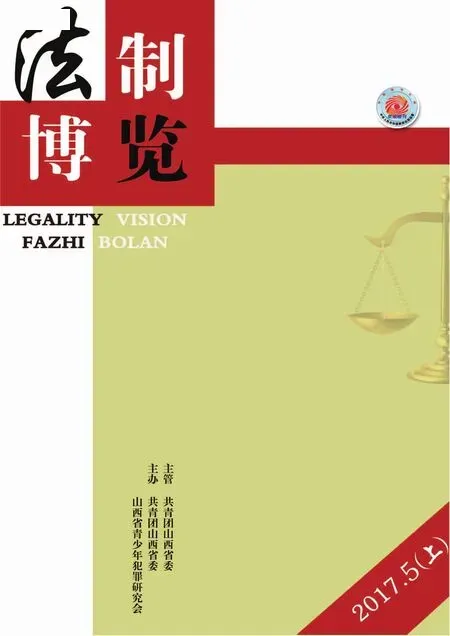“刑九”和新司法解釋下的自偵工作研究*
馬 群 馬 碩
安徽省蕭縣人民檢察院,安徽 蕭縣 235200
?
“刑九”和新司法解釋下的自偵工作研究*
馬 群 馬 碩
安徽省蕭縣人民檢察院,安徽 蕭縣 2352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的頒行對我國的貪污賄賂犯罪的懲治與預(yù)防是一個(gè)新的契機(jī)和起點(diǎn),為了更好地解釋和適用《刑九》,“兩高”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guān)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以下簡稱《解釋》)。最新《解釋》的出臺(tái)給司法實(shí)踐中許多沒有定性的案件帶來有法可依的根據(jù)。然而由于受到歷史局限、人文社會(huì)、立法技術(shù)、理論瓶頸等各方面的影響,也使得這次刑法的修正和解釋飽受詬病。
貪污賄賂;法律適用;自偵工作
《解釋》明確了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標(biāo)準(zhǔn),貪污罪、受賄罪“概括數(shù)額+彈性情節(jié)”基本內(nèi)涵,貪污罪、受賄罪判處終身監(jiān)禁,不得減刑、假釋的適用原則,賄賂范圍、為他人謀取利益、累計(jì)受賄數(shù)額、受賄主觀故意的認(rèn)定規(guī)則,行賄罪情節(jié)較輕的相關(guān)依據(jù),以及罰金刑適用等問題,從以上內(nèi)容可以看出我國從嚴(yán)懲治腐敗的刑事政策。
由于立法者認(rèn)識活動(dòng)的局限性,懲治貪污賄賂犯罪這項(xiàng)巨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追本溯源背后充斥著大量人文因素。《解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過度寬泛,原則性較強(qiáng),而實(shí)用性不足。本文作者寄希望于通過自己的理論研究,撥開貪污賄賂犯罪的重重迷霧,探尋法律的真諦。
一、對《刑九》和《解釋》關(guān)于貪污賄賂犯罪規(guī)定的審視
《刑九》對此次刑法的修正和解釋,學(xué)術(shù)界褒貶不一。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用一種理性的態(tài)度正視《解釋》所折射的刑法理念和人文情懷。
(一)構(gòu)建以情節(jié)和數(shù)額并重的受賄犯罪評價(jià)體系
《解釋》修改了貪污、受賄犯罪的法定刑,改變了原來的量刑區(qū)間,貪污、受賄犯罪三檔法定刑的數(shù)額起點(diǎn)也相應(yīng)提高。《刑九》和《解釋》的出臺(tái),重構(gòu)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標(biāo)準(zhǔn),建立“具體數(shù)額+彈性情節(jié)的量刑化模式”。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diǎn)的上調(diào),一度引起學(xué)術(shù)界和業(yè)務(wù)界質(zhì)疑。認(rèn)為貪污賄賂犯罪與盜竊罪、詐騙罪同為非法占有財(cái)物的犯罪,都屬于財(cái)產(chǎn)型犯罪,一般主體盜竊、詐騙千元就可以入罪,而貪污受賄罪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卻要上調(diào)幾十倍,這種人為造成的迥異,會(huì)造成司法實(shí)踐因?yàn)樯矸莶煌谭ㄓ挟悾痉ê螐恼勂穑慨?dāng)然,我們應(yīng)當(dāng)用理性的思維評價(jià)這次刑法的修改。
第一,情節(jié)與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較為全面反映賄賂犯罪的客觀要件。傳統(tǒng)的計(jì)贓論罪觀念和做法需要改變,并確立數(shù)額與情節(jié)分列的二元結(jié)構(gòu)模式,這樣有利于懲治形形色色的貪污賄賂犯罪。
第二,情節(jié)標(biāo)準(zhǔn)的權(quán)重在貪污賄賂犯罪中的比重將會(huì)不斷變大。《解釋》中針對沒有達(dá)到相應(yīng)法定的數(shù)額起點(diǎn),但只要符合相應(yīng)彈性量刑情節(jié)的腐敗分子也應(yīng)當(dāng)適用相應(yīng)檔次的法定刑。
第三,刑法原理和具體犯罪內(nèi)在規(guī)律決定者貪污賄賂犯罪與財(cái)產(chǎn)性犯罪之間的差異。貪污賄賂犯罪自身存在內(nèi)在規(guī)律性決定著其不可能與普通的盜竊、詐騙犯罪適用相同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如果人為地消除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或者金錢犯罪行為類型之間的罪刑關(guān)系與刑法階梯,有違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的刑法原則。盜竊罪與詐騙罪同樣屬于竊取、騙取型犯罪,而兩罪的起刑點(diǎn)不同,法定刑卻是完全一致的。貪污、受賄罪自身內(nèi)在規(guī)律決定其呈現(xiàn)的實(shí)際規(guī)模與樣態(tài)與盜竊罪、詐騙罪不同。
《解釋》確立了一個(gè)相對合理的“具體數(shù)額+彈性情節(jié)”定罪量刑模式,這樣的規(guī)定解決了司法實(shí)踐中的法律適用問題,在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得不到有效遏制的同時(shí),更為我們的規(guī)范化辦案帶來契機(jī)。
(二)職務(wù)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biāo)準(zhǔn)“全國統(tǒng)一”的模式體現(xiàn)公正司法的理念
在《解釋》出臺(tái)以前,上述三罪的定罪量刑標(biāo)準(zhǔn)先由司法解釋規(guī)定一定的“量刑區(qū)間”,再由各地區(qū)根據(jù)本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各地區(qū)的特殊情況,制定符合自身要求的特殊化標(biāo)準(zhǔn)。《解釋》出臺(tái)以后,上述三種罪名改為全國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這種規(guī)定剛問世,實(shí)務(wù)界和學(xué)術(shù)界都有不同的呼聲,認(rèn)為這種做法人為地規(guī)避地區(qū)差異,各地區(qū)司法資源的不平衡必定導(dǎo)致司法公正的缺失和退化。
筆者認(rèn)為,《解釋》所規(guī)定的全國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符合刑事立法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法治國家建設(shè)的根本要求。由于各地經(jīng)濟(jì)差距的縮小,定罪量刑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的“地域區(qū)間”所賴以存在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逐漸削弱并將消失殆盡;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的“地域區(qū)間”會(huì)給司法實(shí)踐適用法律帶來沖突;職務(wù)犯罪的特定身份要求只有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的全國一盤棋,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司法公正;職務(wù)犯罪采取全國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是大勢所趨,時(shí)代潮流。
二、對《刑九》及最新《解釋》對貪污賄賂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的爭議性規(guī)定
關(guān)于貪污賄賂犯罪適用法律最新的司法解釋,在司法實(shí)踐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同時(shí),也存在一些爭議性的規(guī)定,甚至于飽受詬病。
(一)賄賂范圍界定的應(yīng)然意義和范疇
《解釋》把賄賂的范圍由傳統(tǒng)意義上的“財(cái)物”重新界定為“財(cái)物和財(cái)產(chǎn)性的利益”。《解釋》第十二條明確規(guī)定了賄賂犯罪中“財(cái)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cái)產(chǎn)性利益。這一擴(kuò)張性的解釋符合司法實(shí)踐對賄賂范圍的迫切要求。《解釋》除了界定賄賂的范圍,還定義了兩種財(cái)產(chǎn)性利益的計(jì)量模式。
關(guān)于物質(zhì)數(shù)額認(rèn)定,這次刑法的修改并沒明確界定。其中《解釋》第十二條規(guī)定,房屋裝修、債務(wù)免除等物質(zhì)利益可以折算為貨幣的要進(jìn)行折算,但對如何折算為貨幣認(rèn)定賄賂數(shù)額卻沒有指明。對會(huì)員服務(wù)、旅游又強(qiáng)調(diào)其犯罪數(shù)額以實(shí)際支付或者應(yīng)當(dāng)支付的數(shù)額計(jì)算。這是否就意味著房屋裝修、債務(wù)免除等物質(zhì)利益不能以實(shí)際支付和應(yīng)當(dāng)支付的數(shù)額計(jì)算,只能進(jìn)行折算。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于物質(zhì)利益的數(shù)額認(rèn)定,能查清實(shí)際支付貨幣數(shù)額的以查清的數(shù)額為依據(jù),不能查清的以市場價(jià)格判斷支付貨幣的數(shù)額。而對物質(zhì)利益的折算,一般做法是依據(jù)市場價(jià)格計(jì)算應(yīng)當(dāng)支付的貨幣數(shù)額。折算規(guī)則與“實(shí)際支付+應(yīng)當(dāng)支付”規(guī)則在法律適用中的混亂,與法律解釋的正當(dāng)性、科學(xué)性、合理性的要求相比就變得遙不可及了。財(cái)產(chǎn)性利益屬于金錢、貨幣變換而成的、輸送給受賄人的利益享受或者擁有,雖然形式上不具有一般性賄賂的貨幣、物品、財(cái)產(chǎn)的直接樣態(tài),但內(nèi)容上仍然無法擺脫貨幣利益經(jīng)中間環(huán)節(jié)周轉(zhuǎn)而成的賄賂本質(zhì)。[2]
關(guān)于“性賄賂”是否入刑一直是業(yè)務(wù)界和輿論界爭議較大的問題。“性賄賂”是指給公務(wù)人員提供性服務(wù)作為謀取非法利益籌碼的行為。“性賄賂”充其量是一種失范行為,理應(yīng)屬于道德領(lǐng)域的范疇。如果承認(rèn)性賄賂的成立,那么是否意味著變相承認(rèn)性的可買賣性呢?筆者認(rèn)為“性賄賂”仍然停留在應(yīng)然層面,在現(xiàn)階段尚不滿足入罪的條件和基礎(chǔ)。可以把其作為一種量刑的情節(jié)進(jìn)行考慮。《解釋》對以上問題沒有明確回答,無疑成為此次修法的一大遺憾。
(二)終身監(jiān)禁的法理分析
終身監(jiān)禁作為本次修正案的一大亮點(diǎn)首次入刑。其是否是情緒化立法的產(chǎn)物?貪污賄賂犯罪是否符合刑法學(xué)限制減刑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nèi)ド钊胩接懞脱芯俊?/p>
首先,對非暴力型犯罪施行終身監(jiān)禁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其次,終身監(jiān)禁不具有代替死刑的功能。控制和減少死刑適用并最終廢除死刑是我國刑事立法的必然趨勢,也是與國際接軌的戰(zhàn)略舉措。再次,終身監(jiān)禁不具備刑罰的正當(dāng)性,不利于刑罰的法律效果、社會(huì)效果的實(shí)現(xiàn)。終身監(jiān)禁起不到教育改造的功能,還會(huì)導(dǎo)致再次犯罪的可能,懲治貪污賄賂犯罪不在于無期徒刑懲治犯罪的效果,在于刑罰執(zhí)行的效果,對腐敗分子的震懾效應(yīng)。
(三)財(cái)產(chǎn)刑的配置問題
財(cái)產(chǎn)刑的適用在以往的刑事立法中被忽視,在犯罪分子固有的犯罪成本降低的情況下,以小額代價(jià)獲得大額利益,就會(huì)鋌而走險(xiǎn),追逐犯罪所得。《刑九》增加貪污賄賂犯罪財(cái)產(chǎn)刑的適用,有利于在打擊犯罪分子囂張的氣焰。
《刑九》中附加刑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罪刑均衡配置的合理化要求。配置附加刑一般是出于刑事理論均衡的考量,但眾所周知,附加刑可以獨(dú)立適用。此次財(cái)產(chǎn)刑的配置是附屬主刑之后適用的,沒有給其單獨(dú)適用的余地。如對情節(jié)輕微的賄賂犯罪,在符合有關(guān)刑罰規(guī)定和刑事政策的情況下,對罪犯可單獨(dú)適用財(cái)產(chǎn)刑。刑罰的合理配置要求它們各司其職,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節(jié)約司法資源,如果只是一味強(qiáng)化主刑的適用力度,忽視附加刑的適用條件,難免有越俎代庖之嫌。
三、《刑九》及其《解釋》在司法實(shí)踐中的適用中出現(xiàn)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一)立案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大幅度提高,給賄賂犯罪的立案帶來挑戰(zhàn)。勢必放縱一些規(guī)避法律的受賄行為。比如某鄉(xiāng)鎮(zhèn)醫(yī)務(wù)人員受賄案中,醫(yī)務(wù)人員黃某每次從醫(yī)藥代表手中拿到賄賂款都分給其他醫(yī)師,其他人并不清楚錢的來源,黃某要對贓款總額承擔(dān)責(zé)任,而其他人只對自己分得的部分承擔(dān)責(zé)任。這樣因?yàn)閿?shù)額達(dá)不到較大,情節(jié)也達(dá)不到較重,就難以對其定罪量刑。[3]
(二)給傳統(tǒng)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帶來挑戰(zhàn)。由于行賄人與受賄人建立攻守同盟,給我們的偵查帶來難度。《解釋》規(guī)定行賄數(shù)額雖然達(dá)不到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但具有向負(fù)有食品、藥品、安全生產(chǎn)、環(huán)境保護(hù)等監(jiān)督管理職責(zé)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實(shí)施非法活動(dòng)的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zé)任。
(三)新司法解釋的適用效力面臨挑戰(zhàn)。在新司法解釋公布之日的前一段時(shí)間,已經(jīng)立案偵查的案件,立案標(biāo)準(zhǔn)、偵查計(jì)劃都是按照舊刑法實(shí)施的,而且都是經(jīng)過批準(zhǔn)逮捕程序的,按照從舊兼從輕的刑法原則,就應(yīng)該適用新的司法解釋,以前的案件就面臨撤銷案件、不起訴的困境,浪費(fèi)了有限的司法資源。
“刑九”和新的司法解釋的出臺(tái)給我們的自偵工作帶來較大考驗(yàn),如何讓其在新時(shí)期司法改革的時(shí)代潮流中經(jīng)受住歷史的檢驗(yàn),。就需要我們在辦理貪污賄賂案件中不斷提高專業(yè)化預(yù)審、精細(xì)化初查、規(guī)范化執(zhí)法的水平。讓法學(xué)理論與司法實(shí)踐有機(jī)結(jié)合,使法律法規(guī)更好地服務(wù)于司法實(shí)務(wù)。
[1]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guān)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共計(jì)20條,涉及10個(gè)罪名.
[2]劉憲權(quán).貪污賄賂犯罪最新定罪量刑標(biāo)準(zhǔn)體系化評析[J].法學(xué),2016(5):90.
[3]該案是筆者所在單位辦理的賄賂案件.
D924;D
A
2095-4379-(2017)13-0050-02 作者簡介:馬群(1971-),男,漢族,安徽靈璧人,研究生,安徽省蕭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研究方向:刑事法學(xué);馬碩(1989-),男,漢族,安徽埇橋人,研究生,安徽省蕭縣人民檢察院,調(diào)研室負(fù)責(zé)人,研究方向:刑法學(xué)。
安徽省檢察院2016年度檢察理論研究課題(項(xiàng)目號:AJ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