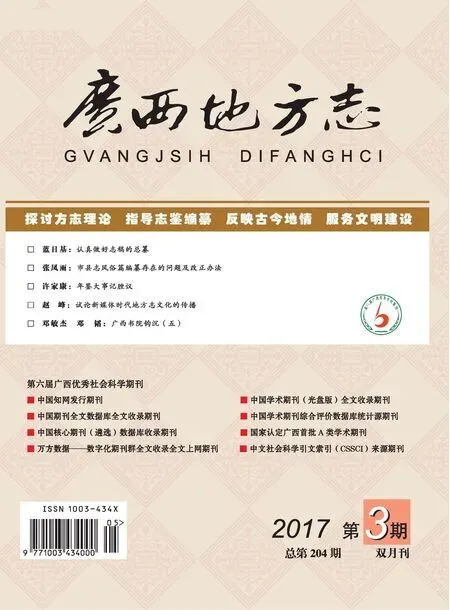市縣志風俗篇編纂存在的問題及改正辦法
張鳳雨
(河北省武強縣地方志辦公室,河北 衡水 053300)
市縣志風俗篇編纂存在的問題及改正辦法
張鳳雨
(河北省武強縣地方志辦公室,河北 衡水 053300)
兩輪修志以來,許多志書風俗篇編纂存在問題:生產習俗記述的是農業生產,有的記述物候節令,生產習俗應記述農業、商業、手工業一些獨特的生產習俗事象;出行習俗記述的是交通工具;飲食習俗多記述的是生活水平或食品制做工藝,應記述各地什么時候食用什么食品;志書風俗篇不記述風尚,而記述的新風尚是一些各類型的好人好事,既不是風尚也不是習俗。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改正辦法。
市縣志;風俗;問題
目前市縣志風俗篇編纂仍存在著許多記述內容上的問題,并且相當普遍或形成慣例,成為志書弊病。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編纂者繼承模仿多,開拓創新少,別人這樣記述我也這樣記述,缺乏獨立思考和仔細研究,造成志書內容上的誤區。因此,有必要對志書風俗篇編纂進一步研究探討,分析和認識存在問題,尋求更科學的記述內容和編纂方法,使志書質量不斷提高。
一、許多志書生產習俗記述的都是農業生產
如《濱州地區志(1979~2000)》[1]濱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濱州地區志(1979~2000)[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記述生產習俗:“境內為黃河三角洲平原地區,向以農業為主。70年代末,陸續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各家各戶自行安排生產,起早貪黑,精耕細作。農忙時節,全家上陣。有的家庭或缺牲畜,或農具不全,農民相互協作。農民種植觀念發生變化,既種糧食作物,亦種經濟作物。80年代中期,出現‘種棉熱’。80年代后期,種植果品、蔬菜者增多。90年代起,農業逐步實現機械化,耕、播用拖拉機,收用脫粒機、收割機,澆用深水泵、噴灌機,運輸用機動三輪車、農用汽車,傳統的農具木犁、耙、耬、鋤、鐮、獸力車、小推車等逐漸失去作用。以往農民憑經驗種田,這時期開始注重種植技術,選良種,巧施肥,慎用藥,重收貯,由靠力氣吃飯,變為靠科學致富。90年代中后期,農民跟著市場種地成為時尚,市場需要啥種啥,優質麥、彩色棉、無公害蔬菜等應運而生。特色農業、訂單農業、綠色農業、土地規模化經營、種植加工銷售一體化等已露端倪。”再如《景縣志(1986~2003)》[2]景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景縣志(1986~2003)[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記述生產習俗分為:“土地”“種子 ”“ 肥 料 ”“機具 ”“作 物 ”“ 播 種期 ”“農 活”等 條 目也完全是記述農業生產的事。這樣記述形成與農業篇重復又遺漏了生產習俗內容。還有的志書生產習俗記述的主要是物候節令。如《萬全縣志(1989—2005)》[1]萬全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萬全縣志(1989—2005)[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記述農牧習俗:“萬全地處塞外,無霜期短,農田作物多為一年一季。耕作慣例為,清明開犁,栽蒜種麥,有‘大蒜清明不在家,入伏不在地’和‘小暑吃大麥,大暑吃小麥’的說法。谷雨開始種大田,立夏忙于種雜田。農諺‘小滿不滿,種田不管’‘小滿前后安瓜點豆’和夏至不種高山黍,還有60天(生長期)的小糜黍。萬全降雨量偏少,十年九旱,且多遭冰雹。萬全人勤勞吃苦,種植上精耕細作。有‘谷鋤一寸賽如下糞,鋤濕鋤頭有火,鋤干鋤頭有水,鋤摟八遍八米二糠,天旱不忘鋤田,雨澇不忘澆園’等農事諺語……”在志書篇目體例結構中,物候節令和農事諺語等自然有地方記述,況且這些實質上屬于生產科技方面內容,不是習俗,不應該記在這里。
普遍的生產習俗與農業篇更接近些,這里只記述一些獨特的生產習俗現象。如一些地方新米收獲要吃“新米飯”;拜蠶神;庭院不種杏樹,謂“人幸它不杏(幸)它杏人不幸”;種山藥(紅薯)根沖南,謂“根沖南山藥甜,根沖北山藥黑”;在場里收糧食要沖著家的方向等。此外,“生產”是“人們利用生產工具改變勞動對象以適合自己需要的過程”[2]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1727.。還應該包括商貿業、手工業(五行八作)等的習俗,如工業手工匠的祭祖師;拜師;木工做完一件家具后要在出廠前往里邊撒一些刨花,認為否則“不留后”;商貿業的開張、聲幌、廣告等。這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產習俗”。
二、有些志書出行習俗記述的是交通工具
如《大城縣志(1989~2006)》[3]大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大城縣志(1989~2006)[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民俗篇記述出行習俗:“1989年后,大城公路建設快速發展,至2006年,全縣實現村村通公路,人們出行更加方便。主要交通工具由自行車為主發展為自行車(電動車)、摩托車和面包車。此外農用拖拉機、三輪車也往往成為農民出行的交通工具。”然后分題列舉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的各種牌子、興衰變化,至2006年全縣有私人小轎車、面包車9959部等。《萬全縣志(1989—2005)》第二十六編《民情民俗》第一章《生活習俗》第四節《交通習俗》記述:“1989年以來,萬全境內柏油公路不斷增加,到2005年達到329.76公里,1998年在全市率先實現鄉鄉通油路,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出行。代步工具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隨后設列“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火車”四目記述交通工具。這些根本不是什么習俗,都應該是交通運輸篇記述的事情。
出行習俗應記述與出行相關的習慣事象。從許多古典詩詞上看,古人迎來送往講究頗多。如“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唐李白:《贈汪倫》)的踏歌送行;“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唐王維:《送元二使安溪》)的設酒踐行;“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北朝樂府《鼓角橫吹曲》)中的折柳送別;“唱徹《陽關》淚未干”(宋辛棄疾:《鷓鴣天·送人》)中的唱《陽關三疊》送行。而如今一些地方親人出門遠行或者歸來,出行習俗豐富多彩。如人們外出謀事、求學,臨走向親友辭行,今多電話告知。親友于臨行前邀請吃飯,謂餞行。家人于前一日包餃子,也有邀親友一起吃的,有“出門餃子進門面”之說。餃子如元寶狀,意寓出門發財。進門吃面條,取“扯不斷”多留在家之意。舊時啟程出門一般要選吉日,普遍流行的是農歷逢三六九日,謂“三六九,往外走”。一般初一、初五、十五不出門。今多不計較這些。出門前打點行裝,有“家窮富路”“飽捎干糧,熱捎衣裳”之說。舊時送行一般送至村口,今多送至汽車站、火車站、飛機場,稱“送站”。一些入學子女,家長有的送到學校。出行者到達目的地后給家人打電話。游子回鄉,舊時一般在村口迎候,也有出迎數十里的。今多到汽車站、火車站、飛機場“接站”,幫拿東西,一路說笑到家。到家后設酒飯款待,名“接風洗塵”。回家者多帶回禮物,分送家中各人。行人問路下車施禮,有“見人不施禮,多走十拉里”之說。
三、許多志書飲食習俗記述的是生活水平
如《青縣志(1978—2008)》[1]青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青縣志(1978—2008)[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第五章《民俗》第一節《生活習俗》記述飲食習俗:“80年代初,人們主食以玉米面食品為主,冬季蔬菜主要是土豆、大白菜;夏季蔬菜品種較多。一般家中待客時才做一些米飯、面食及肉菜。80年代中期,蔬菜品種逐漸增多,主食以大米、白面食品為主。90年代后,設施蔬菜逐步興起,只有夏季有的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粗糧細做食品和部分野菜成為餐桌上的調劑食品……”有些飲食習俗記述的是食品制作工藝。如《赤城縣志(1991—2007)》[2]赤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赤城縣志(1991—2007)[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第三編《人口》第四章《民情習俗》第一節《餐飲習俗》將記述各種食品的制做方法,稱之為“飲食習俗”。如“玉米面饸饹:制作方法:選精細玉米面,與曬干的榆樹內皮加工的細面和在一起,揉筋道,用饸饹床壓在開水鍋內煮熟撈出,澆上酸菜湯便可食用。特點:滑溜可口。進入21世紀,傳統吃法逐漸消失,改用機器壓玉米面饸饹(稱鋼絲面)。放鍋內灑點水,蒸熟,再下入開水鍋煮軟,撈出澆湯,頂替傳統吃法。”其下依次為玉米涼粉、玉米粥、玉米面餅、莜面窩窩、山藥粥、黃糕、折餅、艾糕等食品做法的逐條介紹。
飲食習俗應記述什么時候食用什么食品。飲食食品質地、蔬菜品類多寡是生活水平內容;制作工藝應屬于工業、藝術范疇;在特定時間食用特定飯菜才是習俗。如起五更吃餃子,端午節吃粽子,早晚多喝粥,食用蒸饅頭、烙餅、蒸包子等才是飲食習俗。
四、新風尚(文明新風)記述的好人好事既不是風尚也不是習俗
風尚即一地居民的精神風貌。在風俗篇所記述的“風俗”,是由風尚與習俗兩部分構成的。《詞源》解釋風俗為:“一地方長期形成的風尚、習慣。”《辭海》解釋為:“歷代相沿積久而形成的風尚、習俗。”其“風尚”《辭海》解釋為“風格;氣節。猶風氣。”表現為因受不同地理環境的影響而形成了不同地域人們特有的氣質、操守、風格特征和神韻。屬于地域文化精神特質、精神風貌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內容。如燕趙尚武,吳越尚文;上海人的善于精明估算;北方人的直率;南方人的精明;東北人的淳樸、粗獷;山東人的豪爽等。簡言之,“風尚”即人們的精神風貌,其“習慣”即“習俗”。《說文解字》曰:“俗,習也。”魏晉阮籍《樂論》認為:“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3]中文百科在線《樂論》。既由習慣而成俗。意為某一種行為屢次、經常地重復,習以為慣,便演變成為“俗”。簡言之,“習俗”即人們的社會生活習慣。
新風尚應該是指新時期人的性格、精神風貌、思想意識,表現為集中概括,如互助互濟、尊老愛幼等,公而忘私、共產主義風格等精神風尚。但只能簡述、概括其精神實質,不應該包含一些好人好事的記述、具體的好人好事表現為一些偶然的現象。習俗是指在人民生活中經常重復著的事象,因此一些好人好事是不能稱作“習俗”的。而有些志書在風俗篇記述好人好事,誤認為是“新風尚”。如《宣化縣志(1989—2006)》[4]宣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宣化縣志(1989—2006)[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第四編《居民》第八章《民俗》設第八節《文明新風》,以“廉政勤政”“舍身愛護公有財物”“見義勇為”“希望工程育出新希望”“自學自理”五目,記述王世忠、要涌、尚明、李文英、武明悅、韓秀花、劉江春等好人好事。也就是說根據風尚定義,一些好人好事的精神實質屬于“風尚”范疇,其具體事例既不算“風尚”也不算“習俗”,應記入精神文明篇章。第二輪志書仍有必要記述風尚。一是風尚是地方志的傳統篇目,無論是省通志還是州府縣志無一例外,志書編修是在傳統舊志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而來,風俗篇目及內容并沒有排斥的理由。二是風尚是風俗的一部分,人們大多公認和使用“風俗”為篇名稱,如果不設類目記述風尚,就不能稱其為“風俗”篇。三是一地居民的風尚特征仍然存在,各具特色,是風俗之“本”,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是志書應記述的內容。四是“移風易俗”,風尚也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圣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1]漢書:第二十八卷下《地理志》[A].蕭魯陽.二十五史:點校本[M].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368.風俗與其他地情一樣,具有強烈鮮明的地域性、時代性。近二三十年間,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各地風尚特征也發生一定變化,這同樣是志書應該記述的內容。
首輪志書即有記述風尚的影子,如《奉賢縣志》[2]奉賢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奉賢縣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于風俗志下設《風尚》和《新風尚》節。二輪志書風俗篇卻不見風尚內容記述。筆者參與編修《武強縣志(1988—2007)》,認識到上述問題,于第三編《居民》第四章《風俗》設第一節《風尚》,下設“傳統風尚”“引述舊志記載風尚”“新風尚”“不正之風”4個條目。
K29
B
1003-434X(2017)03-0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