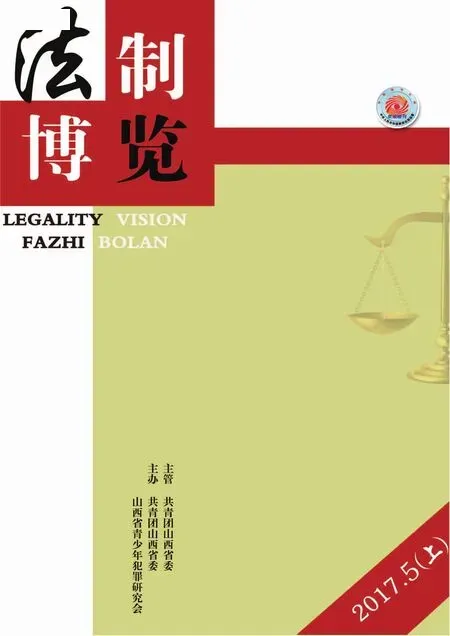論薩維尼與蒂堡關于法典立法的幾點不同
熊漢宸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
論薩維尼與蒂堡關于法典立法的幾點不同
熊漢宸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當下,面對國內部門法的不斷完善以及民法總則重修草案的提交審議,中國啟動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已成為關乎法學界甚至幾代中國人的夙愿。然而,早在200多年前,圍繞著法國大革命及拿破侖對于歐洲政治舞臺的巨變,德國作為反拿陣營中的一員以不斷高漲的民族意識激起了以蒂堡為代表的推崇德國法典化的學者的心,然而薩維尼卻提出了駁斥并將兩人的觀點歸結為“學派的論戰”,自此硝煙未歇。本文通過剖析兩人(兩種學派)對于德國制定統一民法典的不同觀點,回顧當時國內局勢、歐洲形勢下的這場立法革命,在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環境下汲取前人寶貴經驗。
法國大革命;民法典;法典化;歷史法學派
一、關于論戰的核心背景
18世紀后半葉到19世紀初,德國不像浪漫激昂的法國一般經歷了啟蒙思想紅酒的迷醉掀起革命的浪潮,相反,德意志人民在經濟尚處于落后的狀況下善思辨,少實踐,他們向往自由民主但從不倡導革命,不只是因為德意志人民先天懶散,而是因為德國在名義上從來都不是一個具有統一綱領統一意識的帝國,更像是一個極為松散的政治聯盟。在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運動與俾斯麥發動統一戰爭之前,德意志自13世紀以來都是封建割據,哪怕是后來的德意志聯邦。1815年,隨著拿破侖戰時德國的接連慘敗,德意志各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德意志人民要求實現國家統一的斗爭不斷高漲,群眾民族情感迅速迸發,德意志民族主義從文化領域蔓延至政治領域。學者余建華認為:“民族主義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在民族意識的基礎上形成地對本民族至高無上的忠誠和熱愛,是關于民族和民族問題的理論政策,以及在這種理論政策指導或影響下的追求。”恰恰,薩維尼和蒂博就是因為此等情感走上了這樣的道路。不難看出,好比我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后的民族覺醒一樣,此時的德國也正經歷著相同的摸索,在此我們也能感同身受當年兩大法學家對于國家法救亡圖存的爭論。
作為歷史法學派理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薩維尼絕對能稱得上是19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家,當然,良好的法學素養及優越的生活背景給了這位英才幾十年后撼動法學界的強大勇氣。18世紀后半葉,薩維尼出生于一個望族后裔家庭,年少父母雙亡,作為一筆巨大財富的唯一繼承人,薩維尼在監護人—帝國法院處理法官諾伊拉特的督導下,開始學習法律。1795年,薩維尼就讀于馬爾堡大學主修刑法后輾轉哥廷根大學與胡果相識。畢業后,他長期從事刑法學教育,在1803年,用短短五個月的時間著書《論所有權》,聲名大噪。緊接著,拿破侖與普魯士交戰讓這位心懷民族國家情感的青年再也按耐不住了。1814、1815年,作者寫下了《論立法及法學的當代使命》、《歷史法學時評》兩部鴻篇巨著,雖篇幅不長,但作者在其中已經饒有建樹地明確闡釋歷史法學派對于民族國家立法和當下德國立法環境的特點。
《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這本書是在啟蒙運動后,法國大革命前的思潮彌漫于整個歐洲大陸的情況下,薩維尼針對法學家蒂堡法典化理論的駁斥。1803年,《法國民法典》由法國大革命孕育而生,它像是民族國家擺脫封建勢力的“紅寶書”一般,是周邊國家紛紛效仿。德國無一例外也處于在這種漫無邊境的四分五裂的狀態下,蒂堡以極高的個人聲望與學術功底順應了當時這一民眾呼聲較高的潮流,撰寫出《論制定一部德意志統一民法典的重要性》,呼吁統一民法典的制定,希望借法典化的效力促進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打破長期以來封建割據的局面。此時,薩維尼針對此提出截然相對反的觀點,他認為此時的德國,既不具備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觀上講,也沒有一步伐點的生命力所堪憑恃的社會—歷史基礎。文章至此,我們不妨討論一下薩氏的觀點究竟與蒂堡有哪些不同。
二、薩維尼與蒂堡思想的不同
(一)法的起源(淵源)不同
蒂堡認為當下的德國在歐洲大陸亦應當有一部統一的法典,這是一個國家結束封建割據,消除桎梏的紐帶。蒂堡以秉持的理想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傳統自然法學說加之一腔愛國熱情奮筆疾書了《論制定一部德意志統一民法典的重要性》一文。在這長達15頁的書稿中,蒂堡認為“過去一年,德意志人已經從長時間的沉睡中蘇醒過來,社會各階層都以一種空前的團結同仇敵愾。”這是制定統一各國民法典的土壤,在這片土壤中,“小邦與世隔絕,是以微弱的一己之力試圖完成那些不可思議的任務。”在蒂堡眼中,眼下的德國社會雖獲自由,但各邦的習慣法與根深蒂固的羅馬法根本未讓所有的民眾得到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歸屬感和自由感。因此,他所想向世人呈現的是不摻雜各邦恣意的,為全德意志共有的統一的制定法典,可謂是在全德人理智上建立的詳盡的、明智的、包羅萬象,完全根據人民的需求來規范的民事制度。著有《比較法總論》的茨維格特教授也將這種法律的產生叫做“一種超脫國家的法”。蒂堡一邊褒揚著人的理性,反對舊制度的“野蠻、原始”。但在另一邊,薩維尼對此卻賦予一種新的界定。“所謂的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與生活方式的規則形式”,法的起源是如同語言文字一般蘊藏在歷史中,而發的功用和價值,也正在于表現和褒揚民族情感與民族意識。如果將法律看作維護國家統一,促進各邦趨同的工具的話,則規律“如一種乖戾專擅之物,而與民族兩相背離。”在薩氏看來,拋卻民族拋卻歷史地立法是不符合法律本身的規律的,也就是說法律的淵源指向了民族自發的漸進演化而不是立法者的有意識的創造。
(二)法律形式的選擇不同
顯而易見,薩維尼針對蒂堡的論戰并不是僅僅聲討其法的起源究竟為何。在《論制定一部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翻譯有所不同)中,蒂堡已將立法的藍圖設計的一覽無余。“對于每一項立法,我們能夠且必須提出兩點要求,即該立法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要完全。”毫無疑問,這句話是出自一位熾熱的法典化擁護者之筆。不僅如此,蒂堡對此見解做了如下支撐:(1)當下全部的法律雜亂無章,如同大雜燴,各城邦的法律、城邦內的法律都不同存在地充滿了矛盾與否定,不僅無法解決實際問題,更會造成德意志人民之間的隔閡。(2)各種法律的不完全、不完善性迫使人民在日常解決法律問題時不由自主地繼承《羅馬法》,而法學家對于羅馬法則解釋各有不同,很難活生生地存在于法官和律師頭腦中。(3)我們若沒有自己的法典,則會因繼受羅馬法而喪失本國法律的穩定性,依賴于羅馬與巴黎的法律文化甚至政治文化,這是一種充滿屈辱和壓迫的做法。更何況羅馬法本身所帶來的尤士丁尼法典般的晦澀化、片段化根本無法讓嚴謹的德國人去理解。相反,薩維尼一直都是習慣法的堅定追隨者,他反對在此時立法,反對法典化,反對政治對于法律的“綁架”尤其是反對將國家主權的意識迫使法律不得不走向工具的道路。
在談到制定民法典條件時,薩維尼用了一種假設與派出的方法堅定地認為即使需要制定法典,此時甚至未來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制定一部新法典,不可能完全拋棄舊有的東西,對應保留的部分需要加以考察。在內容上,“如果一個時代,條件尚不具備,則不可能以這種方式,經由立法來確定其諸種法律概念,如若經行此事,則其效果對于后續時代不無傷害。”在《我們的立法使命》一章中,薩維尼更提到當下德國的立法技術與能力問題,他以民法中的婚姻與財產為不同調整對象的代表,通過分析法律政治因素和法律技術因素兩方面內容認為此時開展的立法活動應當先明確諸多的法律概念與關系,語言須邏輯縝密,考慮問題須詳盡無遺,而目前,制定這樣一部法典的時代從來沒有到來。
(三)法律保護的對象不同
在《制定法規定與法律匯編》一章中,作者薩維尼以奧古斯都大帝時代的Lex Julia et Papia Poppea(帕比安的尤利法)為例,強調自古以來所有立法的活動都是掌權者為保護其私權的一項利益活動,這是受到強制力保障的“國家理性”的影響,即維護統治階級意志的行為,并不是維護一個國家法律民族性的做法,這種做法無疑是對法律造成有害的扭曲和腐敗。法律所要汲取的營養應當蘊含在民族道德中,借此道德的力量,法律即可達甄圓融之境。這樣看來,我們暫且不管蒂堡究竟是不是國家公權力集團法律制定的游說之人,但至少,薩維尼從“民族性”這一角度揭示了法律是社會意識的產物,在民族中有機生長的,而非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所造就的。深刻強調了立法的意義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在保護什么?
三、結語
兩位偉大的法學家的爭論造就時代文明的火花四濺,用兩種不同的理論肩負著國家安定、復興的希望,在此,本人深深體會到文章開篇中薩維尼指出的兩人恒久不變的相同的出發點。在先后拜讀完兩位大家之作后,本人并沒有并且也沒有這個資格去評頭論足或一較誰的高低,但此時此刻,我更深的感受是兩種不同的聲音似乎都可以征服我的內心。在論戰后世的幾十年內,德國人民在思索中實踐,在實踐中尋求真理,雖然歷史選擇了《德國民法典》這一統一德意志帝國的私法,看似寵幸了蒂堡的觀點,但不難看出,在這其中短短的幾十年,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已悄然發生著變化,似乎《德國民法典》的形式并沒有完全如蒂堡呼吁的那樣盡善盡美,乃至今日,很多內容也是在歷史中得到反復地修正與更新。因此,在這場論戰中,沒有輸贏,只有思想的光輝對于法學界恩寵般地照耀,讓后世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1]K·茨威格特 H·克茨著,潘漢典等譯.比較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A·F·J蒂堡,傅廣宇譯.論制定一部德意志統一民法典之必要性[J].比較法研究,2008(3).
[3]黎四奇.對薩維尼“民族精神”的解讀與評價[J].德國研究,2006(2).
[4]薛軍.蒂堡對薩維尼的論戰及其歷史遺產[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D
A
2095-4379-(2017)13-0102-02 作者簡介:熊漢宸(1991-),陜西西安人,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