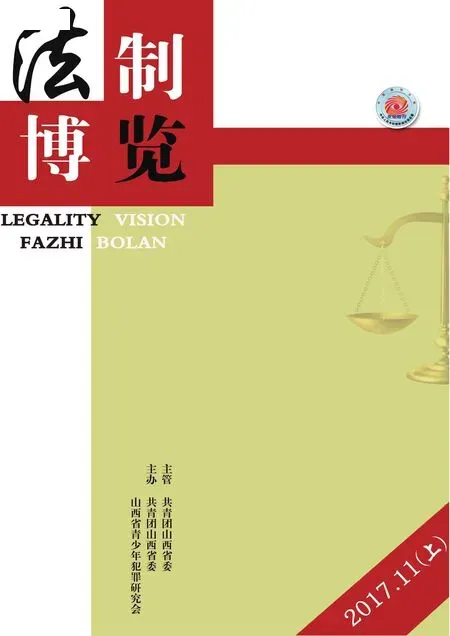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的價值及反思
趙 寧
中共貴陽市委黨校,貴州 貴陽 550001
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的價值及反思
趙 寧
中共貴陽市委黨校,貴州 貴陽 550001
《立法法》的修改,意味著中央和地方立法權的重新配置,在此背景下,關注地方政府立法權的擴張,確保地方政府立法權在合法范圍內獲得確立,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順利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有效推進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及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大有裨益。
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價值;反思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對《立法法》進行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修改。本次《立法法》所做的大幅度修改被認為是執政黨對“法治”的重視達到新高度的重要體現,也是“法治中國”宏偉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次修改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設區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政府規章,這一地方政府立法權限的重大突破,“意味著地方自主的增強。作為國家核心權力的立法權的下放,對于設區的市而言,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反映了中央和省級地方在部分事務控制上的相對松動,拓展了地方事務的自主決定空間。”①《立法法》修改后,學界和實務屆競相爭論的是此次修改是否能夠確保憲法確認的法制統一原則獲得有效實現,使地方立法權下放走出以往“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困境,在推進立法主體多元化的同時,維護法制統一。
一、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的價值
第一,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是全面實施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5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舉措有力、成就豐碩、經驗豐富,開辟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的新境界,凝聚起了全社會最廣泛的法治共識。”②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法治共識”便是立法對于安邦治國、推進改革的重要性。新中國建立以來,伴隨著前兩次地方立法權的“放”與“限”,地方政府立法權的邊界劃定到“較大的市”,而此次修改,進一步擴了地方政府立法權的范圍,使設區的市的人民政府獲得規章制定權。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的軌跡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對國家治理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入,對依法治國理念的持續推進。此次修改之前,地方政府為了能夠及時高效的適用國家及地方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往往采取頒布“紅頭文件”的方式,這些“紅頭文件”又叫做“行政規范性文件”,本質上是地方政府為實現有效治理而出臺的各種行政指令和政治安排,不屬于廣義的法律的范疇。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隨意性較強、缺乏公眾監督等問題,加之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的權威性,效力層級也較低,因而社會認可度較低。隨著依法治國的逐步深入,在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關系的歷史流變中,以地方政府立法權的規范化行使來控制地方決策恣意,突破“集權與分權是政治理想中的兩極”③的傳統觀念,立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實現立法權限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動態平衡,消解政治體制改革和權力關系發展間有可能出現的不協調,是實現“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的有力保障。
第二,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是實現立法創新的大勢所趨。在我的政治體制和立法構架中,作為單一制下相對分權的地方立法,只有在“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情況下才能獲得執行力,尤其是地方政府規章,還不得與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對地方政府立法權進行必要的憲法控制,是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需要,也是促進立法規范化發展的需要。但是,這并不說明立法必須墨守成規,正好相反,立法的生命力在于在憲法控制的范圍以內進行不斷創新的嘗試。這種嘗試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80年代,“深圳市針對收取土地使用費進行了試點,并于1988年1月在全國范圍內首次頒布實施《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該條例對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出讓和用于抵押作了明確的規定,進而助推了1988年憲法第10條修正案的出臺,使得國有土地有償轉讓制度開始在全國獲得確立。”④事實上,從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偉大歷程不難看出,采取“試驗田”的方法積蓄持續創新的力量,是促成改革的重要方式,在立法方面也不例外。毋庸置疑的是,地方政府作為法治創新的主體之一,在推動法治發展,實現法治社會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每一步法治創新的舉動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進行,在此過程中取得的有益經驗,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央立法提供了制度藍本,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我國的立法體制具有相當程度的包容心和開放性。
二、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的反思
在對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的價值作出肯定的同時,對這一擴張趨向也應深入分析其實質,進行深刻反思,對其中有可能存在的問題加以關注,避免出現“一放就亂”的局面。
首先,明確地方政府立法權和事權的區別,避免因二者混淆而加重地方政府的負擔。“在央地關系制度化格局下,只有在上位法關于某個事項的地方立法禁止或上位法保留的前提下,將此事項對地方開放,方可形成地方事權擴大。”⑤然而,從立法技術和規范層面上將,《立法法》關于設區的市的立法權的規定并未明確上位法禁止或上位法保留,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法法》的規定僅就地方政府立法權進行,而與事權下放并無關聯,換言之,《立法法》順應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與歷史文化保護三個方面對地方政府立法進行支持,促成地方政府立法權的下放,而與地方政府事權的變更無關。
其次,以規范化的立法保證地方政府的立法質量,避免出現立法資源的浪費。《立法法》修改之后,傳來部分擔憂的聲音,人們擔心由于地方立法人員欠缺必要的專業素質以及地方立法的監督缺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立法的質量難以獲得保證,進而出現立法資源的浪費。事實上,地方政府立法技術和質量的提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這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或許會伴隨著中國法治創新的心酸和眼淚,但這一切,都不足以對地方政府立法權的擴張加以否定。正相反,隨著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相信規范化的地方政府立法必將成為現實。
再次,地方政府立法并不意味著地方保護主義的抬頭,正相反,在中央的安排和統一調控以及憲法控制下,地方政府立法是滿足利益訴求多樣化的必然舉措,是抑制地方保護主義的基本措施。對于那些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張將會導致忽略弱勢群體的訴求、權力尋租,甚至造成改革動力匱乏的擔憂,其出發點都是維護國家法制統一。但是,應該清楚的認識到,地方政府立法權實際上是對社會利益的再次分配,雖然每一次利益分配必將是各方利益主體殊死搏斗的過程,但是只要在國家憲法的統一控制以及各層級的上位法的約束下,地方政府立法必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而不能逾越,因此,地方保護主義的生長空間仍然十分有限。
三、總結
根據現代法治國家的發展軌跡,立法權再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中處于核心地方,立法權的配置不但關系央地關系,更與社會法治發展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立法法》明確將三方面的立法權限下放給設區的市人民政府,對滿足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實現立法透明、公開、民主,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①秦小建.立法賦權、決策控制與地方治理的法治轉型[J].法學,2017(6).
②人民網.以法治求長治久安——<法治中國>政論專題片引起熱議[EB/OL].[2017-08-21].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7-08/20/nw.D110000renmrb_20170820_2-02.htm.
③陳新民.中國行政法學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115.
④鐘志勇.<立法法>修改后我國地方政府立法權擴大化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6.
⑤秦小建.立法賦權、決策控制與地方治理的法治轉型[J].法學,2017(6).
D927
A
2095-4379-(2017)31-0103-02
趙寧(1965-),任職于中共貴陽市委黨校法學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