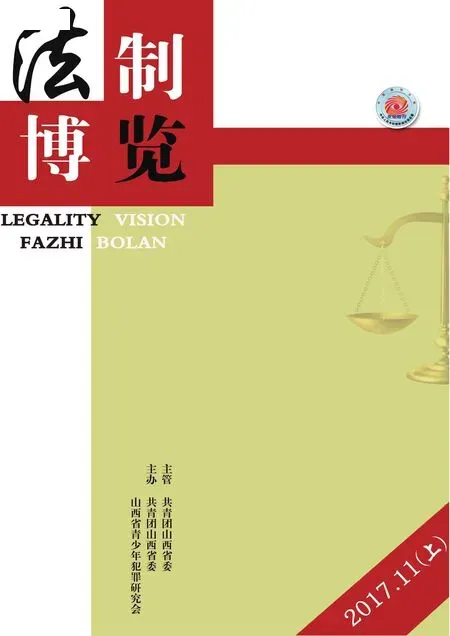夫妻相盜也為罪
楊 欣
天津市北辰區人民檢察院,天津 300400
夫妻相盜也為罪
楊 欣
天津市北辰區人民檢察院,天津 300400
夫妻共同財產能否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共同所有人對共同財產能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討論的重點之一。本文認為共同財產可以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并且只要妨礙了其他共同所有人行使所有權就能夠認定為“非法占有”。
盜竊;共同財產;數額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被告人李某,女,46歲。李某與丈夫感情不和,后李某搬出家中與王某分居并準備離婚。2001年8月20日,李某回到家中,將王某婚后創作的畫卷拿走。次日,王某發現畫卷不見了,便到所在地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經過分析認為是王某所為,公安機關找到李某后,李某承認畫卷是自己拿走的,但拒絕說明去向。2002年8月24日法院判決李某與王某離婚。經鑒定,上述畫卷價值人民幣200萬元。
二、案件存在的爭議
此案在處理過程中,關于李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不能用刑事法律來調整,應當用民事法律來調整。李某拿走的畫卷是王某在婚姻存續期間創作所得,應當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夫妻雙方對其均有所有權,均可以合法占有,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
第二十一條規定:一方將夫妻共同財產非法隱藏、轉移拒不交出的,或非法變賣、毀損的,分割財產時,對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的一方,應予以少分或不分。因此,李某的行為應當是隱藏并拒不交出共同財產,屬于《婚姻法》調整的范疇,對于王某的損失,《婚姻法》也完全能夠給予足夠的補償,不應運用刑法手段。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理由是,畫卷在雙方未離婚時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對其都有保管的責任和權利,李某將畫卷秘密轉移,只是改變了保管的人和地,并沒有改變財物的所有權。但兩人離婚判決生效后,李某仍拒不說明畫卷的去向,對王某的財物繼續占有而拒不返還,其行為性質發生變化,構成侵占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我國《婚姻法》第十七條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二條進一步將“知識產權的收益”明確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實際取得或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財產性收益”。本案中,畫卷為王某個人創作所得,王某對其擁有當然的知識產權,案發時,該畫卷并未轉化成財產性收益,也沒有證據顯示其已經明確可以取得財產性收益(如已與他人達成買賣合同,則視為明確可轉化成財產性收益),因此,該畫卷不是夫妻共同財產。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15條:離婚時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歸一方所有,本案中的畫卷應當是王某的個人財產。李某以秘密竊取的手段,將王偉個人財產據為己有,其行為已經構成盜竊罪。
三、案件評析
筆者認為,李某的行為應當構成盜竊罪,但該畫卷并不是王某的個人財產,其仍然是夫妻共同財產。以上三種觀點均有不當之處。
首先,畫卷雖然是王某個人創作所得,但仍然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無論《婚姻法》還是《婚姻法》的相關司法解釋,所涉及的用語都是“知識產權”或“知識產權的收益”,并明確表示“離婚時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歸一方所有”,筆者并不否認王某對該畫卷享有當然的知識產權,問題的關鍵在于畫卷究竟是知識產權本身,還是僅僅是知識產權的載體?筆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一項附著在物上的權利,并不意味著物就是知識產權。本案中,附著在畫卷上的著作權歸王某個人所有,但著作權的載體——畫卷,卻歸夫妻雙方共同所有。無論畫卷上附著怎樣的權利,都改變不了畫卷作為一個物的本質,我國《婚姻法》第十七條也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生產、經營的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很顯然,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創作出來的畫卷,作為一個“物”,屬于《婚姻法》所說的“生產、經營的收益”,應當歸夫妻雙方共同所有。
第二,李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的理由前后矛盾。該觀點認為,李某的行為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是沒有任何瑕疵的,其僅僅是行使其對于共同財產的管理權,只是在離婚判決生效后其拒不返還王某個人財產時才構成侵占罪。僅僅因為婚姻關系不存在了,原屬于夫妻共同所有的畫卷就變成了王某個人所有,理由何在?如果離婚判決中將該共同所有的畫卷判歸李某個人所有呢?李某的行為又如何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要依據離婚判決來確定,顯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李某的行為確實屬于離婚時隱匿、轉移財產的行為,法院在判決離婚時也可以適當照顧王某的利益,但這并不意味著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在民事活動中發生的行為當然首先依據民法來調整,但當其已經符合《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的時候,就不能排除刑法的適用。所謂的罪刑法定原則不僅僅包括“法無明文不為罪”,也包括“法律有規定的,按照法律定罪處罰”。
那么,畫卷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如何能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呢?盜竊的數額如何認定?對于發生在家庭成員間的盜竊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理由何在?“法律不入家庭”該怎樣理解?
首先,夫妻共同財產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在我國是有法律依據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項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近親屬的財產,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的,處罰時也應當與在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所謂“自己家的財物”,不外乎家庭共有財產和夫妻共同財產,從司法解釋的意思來看,夫妻共同財產可以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只是處罰時與普通盜竊案件有區別而已。
其次,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均可合法占有,這并不代表對于共同所有的財物就不可能出現“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罪犯罪構成中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相對于被害人而言的,只要使被害人喪失了對財物的合法占有即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本案為例,李某與王某均可以行使對畫卷的占有,但其行使的前提是不能排除對方的占有,但李某私自將畫拿走并拒不說明去向,已經妨礙了王某行使其合法的占有,無論李某將畫卷拿走是出于何種目的,都只是犯罪動機的問題,不影響“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成立。反觀王某,在李某拿走畫卷之前,畫卷一直處于王某的保管之下,但其并沒有排除李某行使自己對畫卷的權利,因此李某才能順利在從家中取走畫卷。問題的關鍵不是誰拿了畫卷,而是不能阻礙對方的占有。
第三,李某拿走畫卷的方式為秘密竊取。有觀點認為,妻子從家中拿走雙方共有的財物,沒有任何人會認為是偷,其行為缺乏秘密性,筆者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盜竊罪中的“秘密”具有相對性,只要被害人沒有發覺或者行為人自己認為沒有人知道就可以稱為“秘密竊取”。實踐中經常看到這樣的例子,行為人利用偷配的鑰匙入室盜竊,鄰居誤認為是搬家公司的人,或者行為人夜間入室盜竊,以為主人熟睡而偷拿財物,實際主人只是出于恐懼而未敢出聲,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本案中,丈夫王某顯然不知道畫卷是被誰所拿,否則其也不會到公安機關報案,因此,李某的行為方式應當屬于“秘密竊取”。
第四,盜竊夫妻共同財產的數額可以認定為共有物價值的一半。共有分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兩種,按份共有的以比例確定每位共有人應有的份額,共同共有中各共有人平等在擁有共有物,沒有份額區別。夫妻共同財產屬共同共有,這就為司法實踐帶來了一個難題,盜竊夫妻共同財產的,如何確定盜竊數額。筆者認為,這一問題可以參照民法中對于共同共有物一般的處理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九十二條規定,共同共有的財產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按等份處理,我國《繼承法》中也規定,夫妻一方死亡后,應當先將雙方共有的財產等分,再將其中的一半作繼承處理,由此可見,在我國民事法律體系中,對沒有協議的共同財產原則上是按照等分處理的。因此,處理盜竊共同財產的刑事案件時也可以借鑒該原則,按等分處理盜竊數額。
D923.9
A
2095-4379-(2017)31-0127-02
楊欣,女,天津市北辰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