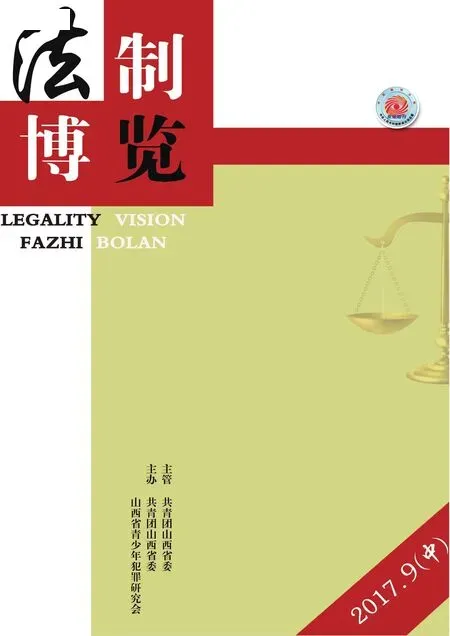配偶權法律問題探討
陳桂華
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
配偶權法律問題探討
陳桂華
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
配偶權是一種基本的身份權。我國《婚姻法》修正案尚未引入配偶權概念,有關配偶權法律問題,在學界和實務界一直存在爭議。文章分別從配偶權的概念,配偶權的法律屬性,配偶權的范圍及配偶權的救濟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并對完善我國相關立法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配偶權;身份權;忠實義務
一、配偶權的概念及法律屬性
(一)配偶權的概念
《元照英美法詞典》里“conjugal rights”一詞,翻譯過來就是婚姻權利或配偶權利,是指夫妻間相互享有的權利,尤指相伴、同居和性交的權利,但任何一方不得強制實施這些權利。配偶權的概念是英美法系國家率先提出并不斷予以完善的。英美法系國家認為,配偶權是指配偶之間要求對方陪伴、鐘愛和幫助的權利,如果上述權利被侵害,依據制定法或判例法則被認為是違法行為,侵害者要承擔經濟賠償的責任。美國的司法判例認為,配偶權包括兩層法律關系,一是基于配偶身份,在配偶之間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二是在夫妻與第三者之間可能產生的損害賠償法律關系。
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沒有配偶權概念,僅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中有配偶權的具體內容。例如,《德國民法典》第五節“婚姻的一般效力”中規定了配偶間的權利義務,其中包括同居義務、家事代理權、姓名權等。我國立法對配偶權的內涵沒有明確界定,學者們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婚姻存續權說。認為配偶權是存續婚姻的權利,是配偶之間要求對方陪伴、鐘愛和幫助的權利。二是身份說。認為配偶權是夫對妻及妻對夫的身份權,是基于夫妻身份而應當享有的配偶身份權利。三是基本身份權說。認為配偶權是指夫妻之間互為配偶的基本身份權,表明夫妻之間互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權利人專屬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負不得侵犯的義務。第一種觀點是從英美法系國家的學術專著引申而來,有其合理性,但過于寬泛。第二種觀點將配偶權歸結為一方對另一的權利,簡單明了,但做為概念界定不夠規范,沒有揭示事物的本質和特征。第三種觀點強調了配偶權的專屬性和支配性,忽視了配偶權的相對性。以上觀點從不同角度對配偶權進行了描述,雖有差異,但也有共同之處。我們認為,配偶權是夫妻基本身份權,是基于夫妻身份而產生的基本權利,是權利人享有專屬支配其身份利益的權利,對方及其他第三方負有不得侵犯的義務。
(二)配偶權的法律屬性
首先,配偶權是一種身份權。“身份”在拉丁語中是“status”,按照《元照英美法詞典》的解釋,在羅馬法上,該概念是指一個人的地位和身份。一個完全的羅馬市民必須享有自由身份、家族身份和市民身份。古代社會,身份的存在意味著等級的存在,身份成為確立社會成員地位和決定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身份界限被打破,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轉變,不同身份的人,法律地位平等。所以,與傳統的以相對人的人身為客體的身份權不同,現代意義的身份權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礎之上,基于身份而依法享有的以人身利益為客體的權利。
身份權屬于民事權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事權利根據其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不同,可以分為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兩大類。其中人身權利按其客體不同,又可以分為調整身份利益的身份權和調整人格利益的人格權。配偶權屬于民事權利體系中的人身權利,是人身權利中的身份權。狹義上的身份權,則指親屬身份權,包括配偶權、親權和其他親屬權。配偶權作為一種親屬身份權具有以下特點:其一,配偶權的主體具有特定性。配偶權的形成以夫妻身份關系為前提,配偶權只能由法律認可的婚姻形式中的當事人享有,婚姻關系終止則配偶權隨之終止。其二,配偶權的客體是配偶的身份利益,即配偶之間相互陪伴、鐘愛和幫助的利益,不直接表現為財產利益。其三,配偶權的內容具有雙重性,即權利義務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權的實現需要雙方同時履行和協調配合,配偶雙方既是權利主體,又是義務主體。
其次,配偶權具有雙重屬性。配偶權既是相對權,也是絕對權。根據民事權利的效力范圍不同,民事權利可以分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是指其效力及于一切人的權利,其義務主體是不特定的任何人。絕對權的主要特點在于,權利人可向任何人主張權利,權利人不須借助義務人的行為就可實現其權利。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是指其效力及于特定人的權利,即義務人為特定人的權利。相對權的主體必須通過特定義務人的履行義務的行為才能實現其權利。配偶權具有相對權和絕對權的法律屬性,是基于婚姻關系具有對內和對外兩種效力。對內效力是指,配偶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在特定的男女之間,彼此的權利義務屬于相對權的范疇。為了維護配偶雙方的利益和婚姻關系的穩定,各國皆以法定的形式規定了配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其中配偶之間的同居、忠實等權利的實現需要他方的積極作為,同時,配偶一方不得強制實現其配偶相對權。對外效力是指,配偶權具有對配偶以外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配偶以外的第三人均負有不得侵犯配偶權的不作為義務,不得實施干擾、妨害、侵犯配偶權的行為。配偶權的兩種屬性,決定其法律保護的方式和力度會有所不同。對絕對權的侵害,由侵權法保護。
二、配偶權的范圍
配偶權是基本身份權,是基于法律規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產生的,配偶權作為基本身份權還包括諸多派生的身份權,是一系列權利的集合。關于配偶權的范圍,我國學者主要有以下觀點:其一,認為配偶身份權包括同居的權利和義務、忠實義務、夫妻姓名權、夫妻人身自由權、婚姻住所決定權、生育權、撫養權、日常家事代理權、財產管理權、監護權、失蹤或死亡宣告申請權、遺產繼承權等。其二,將配偶權的范圍限定在配偶關系存續期間的夫妻人身關系,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配偶身份權不包括配偶人格權和財產性權利,僅包括同居權利義務、忠實權利義務、婚姻住所決定權、家事代理權。其三,認為配偶權的范圍僅指夫妻之間的忠實權利義務。
第一類配偶權范圍過于寬泛,不僅包括夫妻人身權還包括夫妻財產權。很多國家法律中沒有配偶權的具體概念,但在“婚姻效力”中會規定夫妻的權利和義務,而且通常將婚姻的效力分為夫妻人身關系和夫妻財產關系兩部分進行規制。兩種法律關系的性質和地位不同,人身關系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關系,財產關系從屬于人身關系。配偶權是一種基于身份利益而產生的權利,表現為一系列具有人身性質的權利集合。而夫妻財產關系,不直接體現人身屬性,反應的是夫妻在經濟層面的結合。第三類配偶權范圍是最狹義角度的一種界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忠實權利義務是其核心權利義務,但是夫妻人身關系的內涵是多方面的,除了忠實權利義務外,還有其他的權利義務。相比較而言,第二種配偶權的范圍比較合理,它充分反映了配偶權的屬性。婚姻關系的締結,改變了當事人單身生活的狀態,進入共同的婚姻生活,配偶人格權和配偶身份權發生分離。夫妻姓名權、人身自由權、生育權等屬于配偶人格權范疇,由人格法進行規范和調整。反應配偶身份的同居權利義務、忠實權利義務,住所選擇權、家事代理權等則反映了配偶權的內容:
第一,同居權。同居是婚姻自然屬性的體現。同居既是配偶雙方的權利,也是配偶雙方的義務。同居的身份利益是由配偶雙方共同支配、相互配合而實現。同居權利義務主要包括:夫妻性生活,夫妻共同寢食,夫妻相互協助等。同居義務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免除:一是因正當理由而暫時中止同居義務。例如,因工作學習離開原住所的,不構成同居義務的違反。中止事由消失后,同居義務自行恢復。二是因法定事由而中止同居義務。很多國家對此有相應立法,例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法典》第1353條第2款規定:“夫妻一方對他方在建立共同生活后所提出的請求,如顯然為濫用其權利或者婚姻已破裂時,無承諾的義務”。也就說,夫妻同居義務的履行,以自愿協商為原則,一方不可以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而脅迫對方,甚至采用暴力手段。
第二,忠實權利和義務。狹義的忠實義務是指配偶性生活排他的專屬義務,要求配偶雙方互負貞操忠實義務,不為婚外性生活。廣義的貞操義務還包括不得惡意遺棄對方以及不得為第三人利益犧牲、損害配偶一方的利益。夫妻互負忠實義務是婚姻關系最本質的要求,婚姻關系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配偶雙方的互相忠實。我國婚姻法修正案第4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并在該法第46條規定了夫妻違反忠實義務而導致離婚的,過錯方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婚姻住所決定權。婚姻住所決定權是指夫妻選擇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權利。現代各國關于住所決定權的立法,主要有四種立法模式:一是婚姻住所商定權。即婚姻住所決定權屬于當事人雙方,雙方協商確定住所。例如《法國民法典》第215條規定:“家庭住所”即作此規定。二是婚姻住所自由選擇權。即婚姻住所由配偶雙方選擇確定,夫妻各方都有選擇居住地點的自由,如前蘇聯的相關規定。三是婚姻住所的丈夫決定權。即婚姻住所由丈夫決定,妻子隨丈夫居住。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條第2款的規定。四是婚姻住所由丈夫提供,妻子有居住的權利。例如英國1976年的《婚姻住房法》及《婚姻程序及財產法》就是這種立法例。
第四,日常事務代理權。夫妻日常家務代理權即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權代理他方行使實施日常事務的權利,也就是說夫妻一方所代表家庭作出的實施日常事務的行為則視為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他方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并且夫妻雙方都應對其行為承擔連帶責任。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規定。例如,瑞士民法第163條第2款規定,妻超越代理范圍的行為,在不能為第三人所識別時,夫應承擔責任。
三、完善我國配偶權制度的思考
(一)明確配偶權法律屬性,完善配偶權具體內容
如上所述,配偶權是一種雙重屬性的權利,既是相對權,也是絕對權。然而在我國法律上缺乏對于配偶權屬性的明確界定,以至于實踐中遇到具體問題時不能妥善解決,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三者侵權問題。同時,需要在立法上明確配偶權具體內容。構建同居權利義務、忠實權利義務、婚姻住所決定權以及家事代理權權等配偶權的權利體系。首先,在立法中應明確規定同居權利與義務,該項權利由夫妻雙方共同享有,一方拒絕履行同居義務的,另一方不得采取違法手段強迫其履行義務,同時對終止同居義務的法定事由加以規定。對無故拒絕履行同居義務的行為,可以作為構成遺棄或離婚的理由,權利方可以要求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其次,我國現行《婚姻法》修正案對忠實義務是以倡導性的規范形式加以規定的,筆者認為,應在夫妻人身關系中對夫妻忠實義務做出明確規定,任何一方違反該性法定義務,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最后,立法中應該進一步明確婚姻住所決定權和家事代理權。婚后住所的確定,應該本著夫妻雙方協商一致的原則,對婚姻住所作出規定。
(二)完善配偶權法律救濟
“有權利必有救濟”是權利的核心要素,權利體現了人的某種要求,而救濟則是這種要求得以實現的手段。《婚姻法》第46條規定:“因與他人重婚或同居致使離婚的,受害方可向過錯方提出損害賠償”。該條款可看做是對于侵害配偶權的救濟方式的規定。但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對當事人對于侵害配偶權的救濟請求作出了限制性規定。例如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當事人不起訴離婚而單獨提出損害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當事人以違反夫妻忠實義務的內容而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外,婚姻法雖然規定了無過錯方可向有過錯方提出侵權損害賠償,但是該項規定是以離婚為前提條件的。再者,我國婚姻法僅規定了出軌方應當對侵犯配偶權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對于第三者卻沒有相應的處罰規定。這足以看出我國現行法律對于配偶權救濟措施的缺失。鑒于此,亟待需要進一步完善現行立法。
首先,進一步完善配偶之間的侵權救濟。明確規定配偶之間侵權的民事責任承擔方式,在配偶受害方不以離婚為前提而提起訴訟時,可按《侵權責任法》要求配偶出軌方賠償配偶受害方人格權、財產權的損失,要求其承擔賠禮道歉、停止侵害等責任。同時,對出軌一方侵害配偶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做出明確規定。其次,對第三者侵犯配偶權的行為作出規范。可以借鑒國外相關法律,結合我國具體司法實踐,做如下完善:其一,立法上對“第三者”作出界定。第三者是指明知他人有合法配偶,仍愿意與其發生并保持性關系的人。但如果配偶出軌方隱瞞自己的婚姻關系致使第三人不知情的,則不應認定其為第三者。其二,明確第三者侵犯配偶權的具體情形。目前可認定為第三者插足的具體情形為:通奸、重婚及非法同居等。其三,明確規定第三者與配偶出軌方對于侵犯配偶權的行為負連帶責任。最后,明確規定第三者侵犯配偶權應承擔的具體民事責任方式。
[1]薛波.元照英美法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3]威廉·丁·歐德納爾,大衛·A·瓊斯,顧培東,養遂全譯.美國婚姻與婚姻法[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
[4]裴樺.配偶權之權利屬性探究[J].法律與社會發展,2009(6):64.
D923.9
:A
:2095-4379-(2017)26-0075-03
陳桂華(1964-),女,漢族,山西人,博士,天津外國語大學,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經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