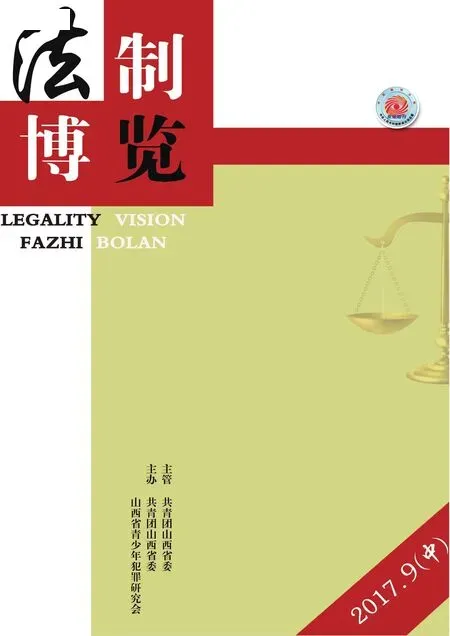涉外國家侵權案件中行為國進行司法管轄問題分析
蘭秀云
海軍大連艦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涉外國家侵權案件中行為國進行司法管轄問題分析
蘭秀云
海軍大連艦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國際社會對于涉外國家侵權案件中行為國是否可以行使管轄權有所爭論,通過對現僅存在的質疑進行分析,提出行為國行使管轄權的正當化依據。行為國行使管轄權有國際法上的依據,符合國際法原則,同時具有便利司法的優勢。
國家侵權;行為國;管轄權
美國學者戈爾丁有一句關于程序正義的名言:“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中的法官”。但是在以侵權行為國家為被告的涉外侵權糾紛中,由侵權行為國自己行使管轄權并不少見。是涉外國家侵權糾紛的特殊性使然,還是這樣的管轄實踐已然與正義、公平相反,抑或是戈爾丁的話本就以偏概全?
通常認為,國際司法機關對涉外性國家侵權糾紛有管轄權,糾紛相關國家如侵權行為發生地國、當事人國籍國以及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等也可以進行管轄。但是,作為案件當事人的侵權行為國對以自身為被告的該類案件是否享有管轄權,則具有一定的爭議。
一、爭議與質疑
對行為國以自己為被告的涉外侵權案件行使管轄權,主要存在以下質疑:
一是,由侵權行為國做出的判決最不可能實現。質疑聲音認為,因為行為國可能會從本國公共利益優先保護的角度直接摒棄或擱置該類判決從而使案件判決的執行變得不可實現。二是,侵權行為國國內法院受理以本國國家為被告的國際侵權案件時,多適用本國的國家賠償法或是國內民法,而對其他國家法律適用則不予考慮,將有可能形成不公正、對原告不利的判決。三是,受理以本國國家為被告的涉外侵權訴訟可能會受到一些限制。如許多國家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領域對外國人的訴權采取互惠原則,即一旦外國國家沒有給予本國國民起訴對方國家的機會,則外國國民也不可能在本國法院享有起訴權。
二、正當化依據
日本法院受理部分中國公民對日索賠之訴即是典型的行為國司法管轄案例。盡管日本法院關于案件審理結果的說辭是否正確值得商榷,但日本法院受理以自身為被告案件的行為本身卻并沒有受到質疑。
概括起來,行為國國內法院受理以本國為被告的國際侵權案件的重要依據是,正當的管轄權行使和案件審理的公正性。
(一)行為國對該類案件具有國際法上的管轄權
關于案件的管轄原則,一般有屬人管轄、屬地管轄、保護性管轄和普遍管轄。在以自身為被告的國際侵權案件中行為國行使司法管轄權,這是屬人管轄的體現。主權國家具有國際社會共同承認的獨立人格地位,這不僅體現在國際交往層面,在國內層面也同樣予以承認。國家法律人格獨立地位使得其在尋求“國籍國”救濟時,國籍國便與自身產生一定程度的重合。在涉外國家侵權糾紛中,國家作為行為主體,其“國籍國”也就是行為國本身得主張屬人管轄權,而不論國家侵權行為發生在何地。
(二)行為國對該類案件進行司法管轄符合“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的國際法原則
國際法上通常認為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國家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的案件。將涉外國家侵權案件交由行為國自己處理,并不違反“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原則。行為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受理以侵權行為國為被告案件,都將面臨對另一平等主權者行使管轄的問題,這無疑會引起行為國的不安,因為這不僅是對主權國家侵權行為的審理,審理過程中還可能涉及到國家機關具體運作情況和國家秘密,行為國出于對國家主權及國家利益的維護,都有理由拒絕其他國家對這類案件的管轄。行為國對他國行使司法管轄也還存在關于案件審理公正性的顧慮,因為他國對案件的管轄使得案件判決的公正性將受到包括國家關系、不同法律適用等因素在內的更多方面的影響。行為國對自身的國家機關行為進行調查審理既不會涉及侵犯國家主權的問題,也不用擔心受到不公正地審判,而且當涉及國家秘密時,可以更好地維護國家權益。
(三)行為國進行司法管轄符合便利司法原則
“原告就被告”是多數國家司法管轄權確立的一種重要原則,由被告所屬國行使管轄權有利于司法過程中許多活動的開展。行為國關于產生侵權行為的國家內部機構職能的了解和熟悉,可以在調查過程中節約司法資源,并且能夠得到更多第一手資料,推進案件審理進程。
涉外國家侵權案件交由行為國管轄,也可以使案件判決的執行得到更加完備的保障。涉及國家侵權的案件中,作為被告的行為國需要承擔責任的可能性較多,若排除行為國對這種案件的管轄權,行使管轄權國家法院的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將面另一定的阻力:不僅程序上的承認和執行方的認定需要確定,并且判決最終對行為國財產或者其他方式的執行將面臨國家執行豁免的抗辯。而直接由行為國管轄將行為國行使國家執行豁免的抗辯問題,無疑能有效避免判決的落空情形。因此可以看出,由行為國行使司法管轄權得以使案件判決的承認和執行進行順利,節約司法資源。
三、澄清與結論
由行為國進行對以自身為被告的涉外性侵權案件進行司法管轄,并不會必然影響導致非正義。
(一)由非侵權國家進行管轄同樣可導致裁判不能實現
前述質疑之一提到,侵權行為國可能以公共利益為由擱置自己作出的判決。但實際上,如果由侵權行為以外的國家進行管轄,作出裁判并予以執行,盡管此時不會遇到國內公共秩序保護問題,但有可能招致侵權行為國家出于公共秩序理由的抗辯,并且即使在該外國國家未提出抗辯情形下,執行國可能還會考慮到國際公共秩序而非判決予以擱置。所以,以此種滑坡理論來論證行為國行使管轄權合理性不具有說服力。
(二)可預見性賦予當事人的選擇權
前述質疑之二提到,在適用法律上的選擇性可能導致案件結果的不公正。但是,在涉及國家侵權的案件中,原告人往往可以選擇不同具有管轄權的法院進行案件的審理,通常考慮到行為國審理案件的便利及其對案件判決的執行等方面存在更多保障,可以使自己受到損害的權益得到救濟,因而對案件審理具有一定預見性。而從國家的利益需求,如政治承認、主導地位、世界貢獻、責任利益以及國家的榮譽和尊嚴等方面看,原告也能對裁判結果及執行產生預期。侵權行為國對自己管轄的以自身為被告的案件也同樣具有公正處理的動力和壓力。實際上,國際人權法的基本要求確認了外國人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應當得到各主權國家的尊重,這決定了即使外國人在行為國法院起訴該國,行為國法院同樣能做出不利于本國的侵權判決。鑒于國際社會的高度發展和融合度升高,新聞媒體發展迅速,行為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受到國際社會關注,行為國會積極依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進行公正審理維護本國國際形象。
(三)管轄權的分配與訴權的實現并非同一問題
簽署質疑提出,受理以本國國家為被告的涉外侵權訴訟可能會受到諸如互惠原則這樣的限制。但問題是,國家間的交往及立場與管轄權分配并非同一問題。這種情況下外國人的訴權得不到保障與行為國可否在作為被告的同時行使案件管轄權不存在直接聯系,而是由主權國家在行使管轄權上的一貫立場及其與其他國家之間交往情況決定。
中國一向秉持國家豁免原則,在涉及以我國作為被告的案件中,堅持國家豁免,不承認外國國家對以我國為被告的相關案件具有管轄權。同樣地,對于在我國法院提起的與外國主權國家相關的案件也不予受理。因而在遇到以我國作為被告的國際侵權案件時,我國法院應當積極主張管轄權,合理合法地行使管轄權,維護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形象。
[1]張磊.論外交保護中用盡當地救濟的法律地位與規則性質[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2).
[2]李華成.涉外國家侵權法律問題研究[D].武漢大學,2013.4.
D997.1
:A
:2095-4379-(2017)26-0180-02
蘭秀云(1993-),女,漢族,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軍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