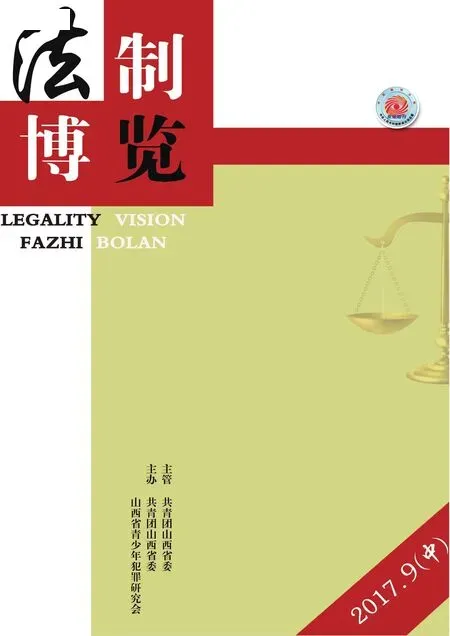淺析刑事案件的輕罪和解制度
陳華路
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重慶 400000
淺析刑事案件的輕罪和解制度
陳華路
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重慶 400000
刑事和解是一種新型的糾紛解決機制,與當前的“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十分吻合,適用刑事和解制度解決社會矛盾,特別是一些輕微的刑事犯罪,有利于節約司法成本,提高訴訟效率,促進社會和諧,對我國司法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輕罪和解;訴訟效益;立法構想
一、輕罪和解制度的概念
刑事和解,又稱犯罪人與被害人的和解,指在犯罪發生后,經由調停人使犯罪人與被害人直接商談、協商解決糾紛,其目的是為了恢復被犯罪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以及恢復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和睦關系,并最終為犯罪者回歸社會、平抑社會沖突而創造條件。①輕罪和解制度是刑事和解制度的一個分支,是當事人之間對刑事責任達成某種協議,對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得以減免,使輕罪案件得到和解。輕罪案件的當事人具有化解矛盾的良好基礎,由于犯罪情節輕微,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較小,且認罪、悔罪的態度好,對社會關系的損害程度較輕,受害方能夠獲得實際賠償;實踐中,將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判處拘役、管制和單處附加刑的案件屬于輕罪案件。
二、輕罪和解制度的產生原因
(一)順應世界司法制度的發展趨勢
“恢復性司法”作為一種新的刑事處理方式,已經成為了一種世界潮流,它的理念相繼被美國、英國、新西蘭等國家接受,并產生了多種實踐模式,其中一種實踐模式正是刑事案件的輕罪和解。因此,構建輕罪和解制度,是順應世界司法發展趨勢的需要。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對一些輕微刑事案件以和解的方式來解決,讓當事人化干戈為玉帛,有利于改造罪犯,有效遏止再犯率,從而減少社會沖突,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定,保障社會生活的和諧。
(三)實現法治文明的要求
刑罰的適用應當與人的本性相符合,尊重人的價值、尊嚴和各種權利。對那些罪行較輕的初犯、偶犯、過失犯和未成年罪犯以及確已悔罪不至于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盡可能放在社會上改造,增強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覺性,發揮社會和人民群眾在教育改造罪犯中的作用。
(四)提高訴訟效益的途徑
實踐表明,犯罪率不斷上升會給刑事司法系統造成極大壓力,如何有效的減少這一壓力,唯有通過增加司法資源和提高訴訟效率。但由于司法資源的投入始終是有限的,只有依靠于訴訟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以最少的司法資源(人力、財力、物力)取得最大的案件處理量顯得至關重要。因此,輕罪和解制度的產生,順應了訴訟經濟原則的要求,實現了訴訟效益的最大化。
三、輕罪和解制度的基礎
(一)具有傳統文化的基礎
時至今日,我國的很多傳統觀念仍然在老百姓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家丑不可外揚”“以和為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寧人”等等,在這種的文化背景下熏陶生長的人文素質,營造了和解解決大多數糾紛的社會環境,為和解制度的順利推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二)具有實踐經驗的基礎
法院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對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從本質上看,自訴案件的法官采取的就是一種輕罪和解的形式,只要被告人自覺履行了賠償責任,往往能夠作為酌定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公安機關受理的鄰里或熟人之間的輕微傷害案件,在公安機關的調解下,只要加害方積極賠償損失并獲得受害方諒解,受害方往往不再進行傷情鑒定,從而放棄追究對方的刑事責任,這種情況實際上就是輕罪和解的體現。
(三)具有法律依據的基礎
現行法律法規出臺了微罪不起訴制度,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明確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也有類似規定,將微罪不起訴的適用條件進行細化。實踐中,檢察機關從嚴把握適用微罪不起訴的刑事案件,對微罪不起訴的程序要求得十分嚴格。
四、輕罪和解制度的立法構想
(一)刑事實體法方面
現行的刑法中沒有明確規定輕罪和解的定義與適用,導致了實踐中缺乏輕罪和解作為從輕處罰或免除處理的法定事由。因此,為更好的順應“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將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推向更高的臺階,建議在刑事實體法體系中明確規定輕罪和解制度的確立及其法律上的內涵,以及明確規定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產生的法律后果。
(二)刑事程序法方面
為解決輕罪和解制度的程序性授權不明,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納入輕罪和解制度作為獨立的法律制度,劃分輕罪和解案件的適用范圍、法定步驟和程序等,然后在司法解釋中通過列舉性規定、排除性規定進一步細化和完善。
(三)和解協議的審查及其效力
和解協議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處置且最終將產生法律效果,因此必須由司法機關對協議的內容予以審查。司法機關應當對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目的性進行審查,即確保協議是在個人真實的意思基礎上達成,不得違背國家的法律法規,協議內容具有解決雙方當事人矛盾的目的。和解協議的效力體現在不同的案件訴訟環節,主要取決于和解協議達成的時間;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將和解協議作為微罪不起訴決定的重要參考因素;在審判階段,可以將和解協議作為減輕、免除處罰的實質理由;在執行階段的,可將成和解協議作為減刑、假釋的法定條件之一。
[注釋]
①陳浩然.理論刑法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3.
D925.2
:A
:2095-4379-(2017)26-0214-01
陳華路(1986-),女,漢族,重慶人,任職于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