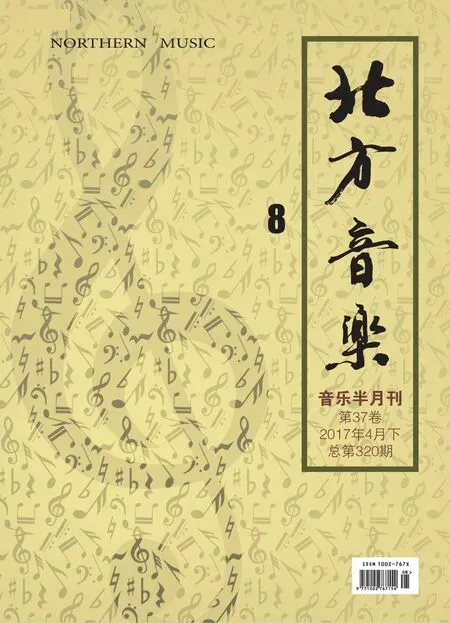黔東南臺江縣苗族古歌文化變遷及原因探析
單曉杰
(凱里學院音樂學院,貴州 凱里 556000)
黔東南臺江縣苗族古歌文化變遷及原因探析
單曉杰
(凱里學院音樂學院,貴州 凱里 556000)
流傳在臺江的苗族古歌既是苗族文化寶庫中一顆閃亮的珍珠,同時也是苗族歌海中的一顆明珠。它用詩一般的語言敘述了苗族的歷史,用生動的形象寄托著苗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苗族古歌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尷尬局面,因此,調查和研究文化變遷中的臺江縣苗族古歌便有了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以黔東南臺江縣苗族古歌為研究對象,揭示在當今社會語境中發生變遷的原因,以期為深入研究苗族文化的變遷提供必要的資料依據。
苗族古歌;傳承人;文化變遷;非物質文化遺產
美國著名音樂人類學家布魯諾·內特爾(Nettl Bruno)曾經指出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兩大宏觀領域:一為重構過去發生的事件,一為觀察現實中發生的變遷,即“文化變遷”。后者目前已經成為民族音樂學之“歷時”研究中極為顯要的領域。 “他們(社會人類學者)意識到變遷難以避免,因而把大量注意力放在‘文化變遷’的研究上,力圖在理解人文類型原有格局的前提下為社會——文化轉型提供合理的解釋。”所謂“文化變遷”,即指“文化的衍變和演進過程”,“文化變遷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在文化系統內部發生的,一是在文化系統的外部發生的,即在一個文化系統與另一個文化系統的接觸和碰撞中,以及文化系統的外部環境的變化中發生的。”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側重于后者。
本文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臺江縣西江苗族古歌藝人們的口述資料和筆者的田野體驗實踐,對該地區苗族古歌于當今時代的變遷狀況進行多方位、多層面的描述與分析,并以此來反觀苗族古歌這一歌種于當今時代的生存現狀。
一、臺江縣苗族古歌的分類
據貴州省臺江縣苗族文化保護委員會暨世界遺產申報委員會于2002年所提交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臺江《苗族古歌》與古歌文化”的申報書中定義到:苗族古歌和“古歌文化”是指“以口傳心記為傳承手段,以全體民族為傳承載體,以盤問對唱為媒介的集苗族世界觀、社會觀、宗教觀、倫理觀、價值觀、法制觀、審美觀和編年史為一體的大百科全書——包括‘開天辟地’、‘鑄日造月、‘蝴蝶媽媽’、‘洪水滔天’和‘跋山涉水’五部分內容的苗族創世詩史和以詩史為核心形成的包括文學藝術、宗教信仰、節日集會、風俗習慣等文化事象的具有空間同一、整體涵蓋特征的苗族非物質活態文化體系”。苗族古歌的作用主要是記敘苗族歷史,記載苗族先民對宇宙萬事萬物以及人類自身的認識。依照我們田野調查收集到的和目前已出版的古歌古詞,我們將苗族古歌分為四類:神話,如《開天辟地》;歷史類如《跋山涉水》;訴訟類如《議榔起義》;婚嫁類如《開親歌》。
二、臺江縣苗族古歌的文化變遷狀況
(一)傳承人的變化
音樂傳承人是一個樂種存續、發展乃至變遷的重要載體和關鍵因素,他們的社會身份、家族構成、受教育程度、價值觀、審美觀皆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著該樂種傳承發展的面貌。據唱古歌的老藝人介紹,解放前唱古歌的藝人都是沒有接受教育的文盲,然而解放后演唱古歌的大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如王安江老藝人經過38年的努力,將流傳于苗族民間的《開天辟地》、《跋山涉水》、《仰阿莎》、《喪亡歌》等12部苗族古歌搜集并整理出來,光古歌的手稿就有16冊,320頁。再如張定祥老藝人,他是苗族古歌第七代傳承人,自幼讀過私塾,輟學后跟隨伯父學習古歌,目前依舊從事古歌傳承工作,是著名的苗族古歌師,他還是施洞當地有名的苗醫,經常為附近村民行醫看病,尤其擅長跌打損傷方面的治療。由此看出,苗族古歌傳承人的受教育狀況已經不同于解放前,至少多數藝人能寫自己的名字或者一些簡單的字。
(二)演唱場合的變化
由于苗族是沒有文字記載的民族,所以苗族的傳承只能靠歷代人口口相傳。據田野調查發現,苗族古歌大多出現在民俗活動中,如民間節日、朋友聚會、婚喪嫁娶和鼓社祭等場合。在演唱古歌時有較為嚴格的禁忌,一般在祭祀祖宗、婚喪嫁娶、親友聚會和民間節日等場合演唱時,演唱者多數為中老年歌手和巫師等。朋友聚會時也是演唱古歌的一個重要場合。演唱時,主客雙方對面而坐,采用盤歌形式問答,一唱就是幾天幾夜。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出臺,2006年苗族古歌作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成功后引起了有關專家和學者的極大熱情。每當學者來當地進行田野調查時,都會邀請古歌藝人演唱苗族古歌進行錄音。在此種情況下,古歌藝人演唱的古歌不再是為祭祖、婚嫁和娛樂了,而改為專門為學者表演,成為他們調查和研究的對象。
除此之外,苗族古歌的演唱場合隨著政府的介入也悄然發生著變化。隨著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政府不錯過每一個民俗節日,每當此時他們將苗族的歌曲搬上舞臺進行展演或比賽以此吸引外來的游客。顯而易見,這些足以體現了苗族古歌在表演場合方面的變化。
(三)傳承渠道的變化
苗族古歌的傳承方式比較嚴謹,有祖先傳承、師徒傳承、家庭傳承和民俗傳承等幾種,其中以家庭傳承和民俗傳承為主。據劉永洪老藝人講,他母親是本村有名的歌師,能演唱很多古歌,八歲的時候他就跟著能歌善舞的母親學習各種苗歌調調,十四五時便跟著村里的人走街串寨去游方。在游方的過程中,只要聽說該村有歌師他都會前去討教。凡是施洞有節日對歌時,劉永洪都會參加,從中學到很多歌也結識了許多歌師。據筆者調查,像劉永洪老藝人這樣通過家庭傳承和民俗傳承來傳承古歌的藝人現在已經不多了。隨著經濟的發展,游方場合的減少,年輕人即使不會唱歌也一樣能找到心上人。因此苗族古歌已經面臨著頻臨失傳的尷尬境地。
此外,臺江縣文化部門為了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落到實處,每逢大型節日,政府部分都會召集各鄉鎮的古歌藝人在縣城進行匯演和傳承古歌的活動,這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苗族古歌的傳播,也促進了苗族古歌藝人之間的互相交流。
三、臺江縣苗族古歌變遷的原因分析
上述是臺江縣苗族古歌的變遷狀況,那么產生這種變遷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些學者總結出“任何社會文化的變遷,都是來自文化內部和外部各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社會文化的變化體現在作為社會文化表征的各種具體文化事項的變遷”。其實文化是整合了各個部分的文化,任何一個部分發生變化都會帶動其他部分的改變,因此,苗族古歌也是在其所依存的外部環境發生改變而進行變遷的,具體原因如下:
(一)新的謀生手段產生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說到,“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與地的姻緣固定了。”費老的這番描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臺江縣的真實寫照,但是隨著打工熱潮的到來,這種局面被打破了,很多年輕人不想跟父輩一樣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紛紛離開故土外出打工,由此致使古歌無人傳承。通過采訪當地藝人,有人就說起王安江先生,他將畢生心血放在收集整理苗族古歌上,總共整理出16冊古歌手稿共384000字,但由于沒有經濟來源,妻子、兒子、女兒相繼離他而去,他的一生是坎坷、悲壯的。所以大多數年輕人認為學唱古歌是賺不到錢的,為了維持生計只能選擇外出打工而不會留在家鄉種地。這就是年輕人不愿學習古歌的原因,也是苗族古歌傳承人日漸式微、青黃不接的原因之一。
(二)新的娛樂方式產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現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現在的苗族村寨幾乎每家每戶都有電視、錄像機等現代娛樂工具,足不出戶就能看到豐富多彩的娛樂節目,所以他們對本民族從古至今遺留下來的娛樂方式已不再感興趣,談情說愛也不再去游方場,苗族古歌賴以生存的民俗活動正在逐年遞減,甚至有的已經廢棄,傳統的苗族古歌正面臨著失去生存空間的危險。
現代苗族青年的審美觀已經改變,苗族古歌與流行音樂比起來,他們更傾向于后者,業余時間更多的是在聽流行音樂而不是花時間學習苗族古歌。所以,苗族古歌的傳承已經處于后繼無人的尷尬狀況。
(三)政治權利的介入
政府的介入也是影響苗族古歌變遷的一個原因。自從臺江縣苗族古歌于2006年申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并被當地政府納入當地旅游開發資源以后,其整體功能性就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據采訪的藝人告訴我們,如今除了政府讓他們進行表演和參加比賽外,在其他場合很少再演唱古歌了。就政府方面而言,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來形容是最為恰當的。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與經濟緊密相連的生動寫照,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各地以辦“節”的形式招商、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宣傳和打造整體形象的有效活動。這里的經濟是主要目的,文化是實現經濟的手段。
臺江縣政府利用每次的大型節日,將苗族古歌從民俗活動推向舞臺,此種形式下的古歌無論從演唱時間、演唱地點、演唱程序還是演唱目的和受眾人群都與民俗活動中有所不同。從表演時間來看,從前的古歌不受時間限制,無論白天還是晚上,只要有二三人都可圍在一起演唱,而如今古歌藝人只是在政府的安排下為專家學者演唱或者在大型的節日里組織上臺表演。從表演地點來看,從前的古歌是在特定的場合表演,或在家中或在村寨的某個地方,而如今的古歌是在政府的組織下到指定的地點去演唱。從演唱的程序來看,從前的古歌說唱結合,有吟唱也有道白,遇到難懂的地方演唱者唱完一句就解釋一句,而如今的古歌沒有道白也沒有解釋,唱的內容很多觀眾聽不懂。從受眾群對象看,從前的古歌只給村里人演唱,現在的古歌多數是給游客表演。由此可以看出,苗族古歌隨著政府的介入和旅游業的發展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四、結語
綜上所述,苗族古歌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這不僅是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也是受日新月異的生活變化的沖擊。苗族古歌為了適應這種沖擊,不斷做著調整和適應,這種調整雖然對古歌藝人來講有所不適,但為了古歌的傳承只能適應這種不同程度的變化。總之,苗族古歌的變遷既是社會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苗族與漢族之間相互融合的文化痕跡。此變遷對苗族文化的發展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其消極之處就是苗族古歌在政府介入之后失去了其特色和個性。若干年之后,文化的根本將何去何從,這是包括苗族古歌變遷在內的少數民族民歌文化變遷帶給我們的新課題。
[1]王銘銘.文化變遷與現代性的思考[J].民俗研究,1998(01):1-14.
[2]張應華.民間臨濟派道場音樂的文化傳統及變遷——湘黔交界北部侗族地區的再研究[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10(03):13.
[3]單曉杰.論苗族古歌與民俗的依附共生關系——以黔東南州苗族古歌為例[J].民族音樂,2012(06):24.
[4]王建朝.新疆和田地區“十二木卡姆”的當代變遷及其原因探析[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13(02):112.
[5]唐婷婷.現代文化場域中納西民歌之變遷[J].青海民族研究,2010(01):140.
[6]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08):74.
J648
A
單曉杰(1980—),女,山東濰坊人,凱里學院音樂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民族音樂理論。
本文受2016年度凱里學院苗族侗族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項課題一般課題“黔東南苗族古歌之存現原因探析”(項目編號:XTYB1631)、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貴州省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研究”(項目編號:16YJC760010)、2016年度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貴州省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研究”(項目編號:2016zd05)、2014年度凱里學院校級重點學科“音樂與舞蹈學”項目(項目編號:KZD2014010,課題名稱:黔東南臺江苗族古歌之文化變遷研究)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