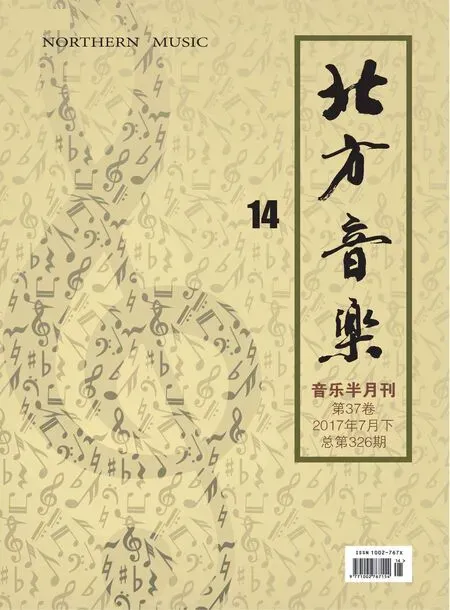歸屬·融合·延伸
——淺淡“豫莎劇”《約/束》中的人物塑造及音樂唱腔之特點
鄭 倩
(河南大學 藝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歸屬·融合·延伸
——淺淡“豫莎劇”《約/束》中的人物塑造及音樂唱腔之特點
鄭 倩
(河南大學 藝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豫劇是中國五大戲曲劇種之一,也是中國第一大地方劇種。莎士比亞是世界上公認的戲劇大家,他的作品在各個時代各個地區常被不同文化形式拿來演繹。當莎翁的戲劇遇上中國的豫劇,兩者碰撞會擦出什么樣的火花?臺灣豫劇團于 2009 年推出了第一部改編莎翁作品的豫莎劇——《約/束》可謂是一次成功的嘗試。本文將從豫莎劇《約/束》歸屬、融合、延伸的角度對劇中人物塑造及音樂唱腔進行分析,希望能對豫劇改編的學術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豫莎劇《約/束》;歸屬,融合;延伸
一、歸屬
《約/束》這個劇目是為戲曲演出撰寫的改編本。改編者刪去夏洛女兒與基督教徒私奔的次要情節,也刪去劇中小丑父子逗笑的片段,專注劇中的主線情節與第一副線的情節變化。前半場講述貴公子巴薩紐想追求富家女慕容天而囊中乏錢,經由好友安東尼的擔保向大食人夏洛借款,讓好友簽下一份“還不起就割一磅肉”的“奇葩”條約。后半場講述慕容天由于亡父遺囑的規定,必須讓求婚者在金匣、銀匣、鉛匣中選擇其一,而巴薩紐最終選對鉛匣,獲得慕容天的芳心,但又由于一枚定情戒指的“束縛”而引起了劇情波動。劇中的高潮法庭一場,主線副線合而為一,聰明的慕容天擊敗狠毒的猶太人夏洛,讓安東尼免除割肉之災。劇中一枚定情戒指的失而復得,更是副線劇情的引伸,將劇情推向圓滿結局。這個改編本的劇名,也正反映劇中兩大情節線的結合:一磅肉的條“約”,以及定情戒指的“束”縛。這出戲的唱段雖有偏離原文,作者對于情節的刪減及篇幅處理也曾引起爭議,但卻保留相當分量的莎劇精華,可算合適而充滿機智。
二、融合
豫劇(河南梆子)本應是傳統戲,而豫莎劇《約/束》這出戲卻巧妙借用西方戲劇的分場次形式進行演繹,采用序曲、第一場《選匣》、第二場《借貸》、第三場《定情》、第四場《改扮》、第五場《折辯》、第六場《判決》、第七場《致謝》、第八場《協議》、尾聲等西方劇場的戲劇模式。除此之外,在第二場《借貸》中,在夏洛的唱段中也加入了中國傳統文學載體《弟子規》“凡取與,貴分曉;與宜多,取宜少。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可見,《約/束》一劇具有將西方的戲劇與東方的戲曲、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突破性意義。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一個跨文化的戲劇作品,改編莎翁作品的難度在于:甚至要進入一個中國傳統歷史的程序制約,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四百多年前的古英文劇本,改編者要先用現代英文來理解,然后翻譯成中文,中文再轉換成戲曲的語言同時還要進入到豫劇去演繹。這種“莎劇改寫成豫劇又轉譯成英文”仍保留莎劇中“五步抑揚格”的形式也是本劇的特點。豫莎劇是在中國三百多種戲曲劇種當中,首次嘗試由真人扮演的豫劇程序,所以主創者曾一再強調必須是梆子腔、二六板式,還一定要有——“梆子”這個打擊樂器以及曲詞唱腔的音樂結構必須是“詩贊體”。莎翁的劇作之所以具有魅力,因為它是筆力萬鈞的戲劇,在他的著作中既有雙關語、諧音、游戲文字等,還有很多抑揚格五音步以及它的十四行詩、無韻詩,這些東西要轉換到我們中國的傳統戲曲語言里是需要做很多功夫去詮釋的。比如:我們必須要做一些“存神于型”。也就是說,把莎士比亞的精神搬過來,但是化用豫劇它所需要的十三道轍(一種押韻的韻部形式),把豫劇的唱詞按照“詩贊體”的格式來改編,還有莎翁的雙關語、諧意的、諧擬的曲筆,這些都是在改編的過程中必須要做調整的。
除了對于莎翁劇本改編的嘗試以外,臺灣豫劇團在角色跨行當方面也進行了突破性的挑戰。在《約/束》中飾演夏洛的是“臺灣豫劇皇后”王海玲,她從八歲便開始學唱豫劇,主攻花旦,兼學武旦。雖有少數反串,但也僅于小生、武生等,并未跨足凈角、丑角等角色。一般而言,花旦在學習的過程中多注重扇子功、手帕功,身姿靈活輕巧,道白明快清脆,唱腔多使“花腔”,移步常用“花梆”,以顯現嫵媚艷麗,嬌憨灑脫的風姿;而武旦常以身手矯健利落取勝,必須勤練各式翻、撲、跌、旋的功夫。而對于劇中角色轉換的挑戰,最大難題就在于聲腔的轉換,王海玲對此自述道:對于《約/束》這出戲我覺得最難的,大概就是「唱」了。在《約/束》中,由于跨行當的關系,對于角色的程序化必須有所創新與突破。在舞臺上成功塑造了一個具有復雜人性、心理轉折豐富的夏洛。而這個夏洛,是至今唯一一個在戲曲表演中由女性來扮演的;在全球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劇場演繹中,也是罕見的。在王海玲飾演的夏洛中,其唱白不免帶有“雌音”,也為夏洛一角增添了另一種特殊的風采與魅力。
三、延伸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徐亞湘在觀看《約/束》一劇后,他曾寫下“河南梆子在臺灣找到了安身立命的藝術位置,一部讓人覺得好看、欣喜的好戲,而非被河南梆子框架限制的劇種藝術,莎劇《威尼斯商人》成功地移植改編詮釋、劇種界限的模糊化與王海玲、蕭揚玲的精彩演出,讓豫劇在臺灣不再‘約束’”。豫莎劇《約/束》的成功上演開啟了一個戲曲新時代。在劇種界限模糊化趨勢的今天,正是臺灣豫劇藝術提升突破的最佳契機,只要不斷創作好作品,未來還保有多少豫劇元素,甚至還是不是豫劇,都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它是好戲。這一觀點的提出引起了與會者激烈的爭論或質疑,使大家對戲曲如何現代化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豫莎劇《約/束》以東方戲曲的形式詮釋了莎劇原著的精神,我想,這應該是豫劇在國際舞臺上一次極大的成功,既是兩岸共同創作的結晶,也是兩岸交流的成果。它的出現指明了戲劇創作者和生產者既要學習傳統,又要熟悉當代各種藝術樣式的表現語匯,還要努力尋找繼承與創新的最佳結合,以應對當代觀眾的文化心理。這,就是肩負著時代賦予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戲曲文化延伸使命的——豫劇!它,是田間的小調,也是殿堂的華章;它,是名家的藝術,也是百姓的生活;它,是厚重深邃的歷史,也是續向前行的未來!
J6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