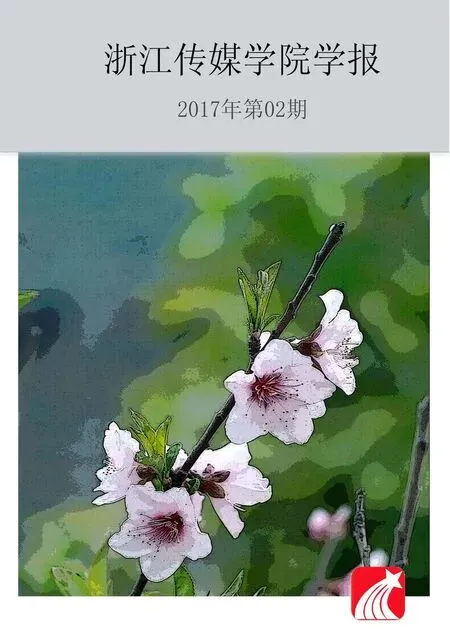沖擊與應對:互聯網時代的廣告法
姚志偉 王媛媛
沖擊與應對:互聯網時代的廣告法
姚志偉 王媛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修訂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應對網絡廣告興起給廣告法帶來的沖擊,這些沖擊主要包括:網絡廣告的海量性給廣告審查帶來的沖擊;網絡廣告經營、發布的低門檻給廣告登記制度帶來的沖擊;以及一些網絡廣告形式對用戶正常使用網絡造成侵擾等。修訂后的廣告法對上述沖擊做出了一些應對,例如將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主體,彌補了法律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將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對內容的義務由“核實”變為“核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網絡廣告經營者、發布者的負擔;規制網絡廣告發送、發布的形式,防止侵擾用戶,保障了用戶的權益。
新《廣告法》;網絡廣告;廣告發布
我國首部廣告法于1995年生效,歷經20載后,進行了首次修訂。2015年9月1日,修訂后的廣告法正式施行。此次廣告法的修訂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對廣告進入互聯網時代后,廣告法面臨的沖擊。國家工商總局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修訂草案)的說明》中,對廣告法修訂的必要性進行了闡述:“近年來,隨著我國廣告業迅速發展和互聯網廣泛應用,廣告發布的媒介和形式發生了較大變化,現行廣告法的有關規定過于原則,約束力不強,對一些新問題、新情況缺乏規范,已不能完全適應廣告業發展的客觀需要”。[1]本文將對原廣告法在互聯網時代面臨的沖擊*為表述方便,本文中將修訂案生效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以2015年9月1日為界限)稱為“原廣告法”,將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稱為“新廣告法”。和新廣告法對這些沖擊的應對進行研討。
一、互聯網時代原廣告法面臨的主要沖擊
(一)網絡廣告的海量性給廣告審查帶來的沖擊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廣告與傳統廣告相比,首先在廣告量上存在巨大的差別。在傳統廣告時代,一個廣告主體所面臨的廣告量是有限的;而在網絡廣告環境下,網絡廣告主體則面臨著海量的廣告。以全世界最大的網絡廣告平臺谷歌為例,其在2010年5月到2010年10月之間,發布的移動廣告就達到1000億條之巨。[2]而中國的某搜索引擎服務商,每日收到其廣告主向其系統投放的推廣物料達到4500萬次,物料存量累計達到30.4億次,每小時有近25%的廣告主更新物料。[3]
網絡廣告的海量性給廣告法中的廣告審查制度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原廣告法為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設定了嚴格的審查義務,*下文將詳述相關條文,此處略。要求其在廣告發布前查驗廣告證明文件及核實廣告內容。在傳統廣告時代,由于有限的廣告量,廣告審查所帶來的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和時間等。尚可接受。但是進入互聯網時代,面對著數以億計的廣告,如果還是采用傳統的人工事前審查模式,幾乎沒有哪個網絡廣告主體能夠承受。
(二)網絡廣告發布門檻降低帶來的沖擊
在傳統的廣告模式中,廣告主通常是有推銷需求的客戶,廣告經營者是廣告公司,廣告發布者是媒體;而在網絡時代,廣告經營和廣告發布的門檻都大大降低。從廣告制作、設計的角度來說,很多網絡廣告形式,例如社交媒體中的廣告,不再需要專門的設計和制作,簡潔的文字加圖片即可構成一則廣告,一般的廣告主自身完全可以完成。在發布廣告方面,網絡時代是所謂的自媒體時代,可供展示廣告的媒介大大增加,發布廣告的門檻降到極低。這一方面導致廣告主深度介入廣告發布,例如廣告主自己在社交媒體上運營推廣賬號,進行廣告營銷。這種情況下廣告主又兼具了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的角色,三者合一的方式使得傳統的主體三分法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進入網絡時代后,廣告發布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廣告發布的門檻大大降低。自媒體時代的興起,使得自然人成為重要的廣告發布主體。借助各種網絡技術和網絡平臺,例如論壇、微博、微信、博客、個人網站等,自然人可以非常便捷地發布廣告,并從中獲取利益,職業化的自然人廣告發布者也開始成為網絡廣告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對于自媒體廣告現狀的介紹,可參見林波、曾志森、曾學明:《“自媒體”廣告監管的初步思考》,載自《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13年第9期。自然人成為重要廣告發布主體,同樣給原廣告法造成重要沖擊。因為原廣告法中的廣告發布者只限定了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原廣告法第2條第四款規定:本法所稱廣告發布者,是指為廣告主或者廣告主委托的廣告經營者發布廣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法律和現實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同時也出現了巨大的監管真空。
(三)網絡廣告經營、發布的低門檻給廣告登記制度帶來的沖擊
原廣告法對廣告的經營、發布實行準入制度,采用登記的方式實行準入控制。這個登記程序主要有兩種:對于兼營廣告業務的事業單位,主要是媒體,發給《廣告經營許可證》;對于其他經營廣告*這里的經營廣告包括廣告法上的廣告經營和廣告發布。業務的單位和個人,發放工商營業執照,把廣告經營列入經營范圍。*《廣告管理條例》第6條規定:經營廣告業務的單位和個體工商戶(以下簡稱廣告經營者),應當按照本條例和有關法規的規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分別情況辦理審批登記手續:(1)專營廣告業務的企業,發給《企業法人營業執照》;(2)兼營廣告業務的事業單位,發給《廣告經營許可證》;(3)具備經營廣告業務能力的個體商戶,發給《營業執照》;(4)兼營廣告業務的企業,應當辦理經營范圍變更登記。這種登記準入制度,在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數量相對不多的情況下還具有可實現性,但在網絡時代則受到重大沖擊。
正如前文所言,網絡廣告經營、發布門檻極低,這使得網絡廣告經營、發布的主體數量極多,這無疑給廣告登記帶來巨大的困難。更為嚴重的是,網絡時代,個人可以通過微博、微信、BBS論壇等網絡平臺很輕松地發布廣告,要讓這些個人都必須在發布廣告前進行登記,顯然是一件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執法機關也根本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去監督這些個人遵守登記程序。
以上三點就是網絡廣告給原廣告法帶來的主要沖擊,*除此以外,沖擊還有:一些網絡廣告形式給用戶造成侵擾,例如垃圾郵件廣告、不能關閉的彈出廣告,干擾用戶正常使用網絡,侵犯用戶權益。上網的用戶對于這個現象會有比較明顯的感知,問題并不復雜,本文沒有展開論述。同時,有學者認為網絡廣告的無國界性會帶來法律適用方面的沖擊,因為任何網絡廣告都可以在互聯網上傳輸到全球任何一個網絡用戶,而各國廣告法又各不相同,在一國內合法的廣告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是非法的,這無疑會帶來法律適用的沖突,相關討論可參見陳志剛:《網絡廣告侵權行為的法律問題分析》,中國政法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陳煜、彭俊瑜:《探究網絡廣告之法律規制》,載自《網絡法律評論》2008年第1期。新的網絡廣告主體如廣告需求方平臺(DSP)、媒介方平臺(SSP)、廣告信息交換平臺(AD Exchange)等出現帶來的沖擊,新廣告法為應對這一沖擊,在第45條為這些新的網絡廣告主體進行了法律界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并為其設定了不同于廣告經營者、發布者的義務。對此,廣告法的修訂做了哪些應對呢?
二、新廣告法對網絡廣告沖擊的應對
應對網絡廣告發展給廣告法帶來的沖擊,正是此次廣告法修訂的重要目標之一。修訂后的廣告法也確實應對了這些沖擊,主要包括:將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范疇;把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對內容義務由“核實”變為“核對”;規制網絡廣告發送、發布的形式,防止侵擾用戶。*除此以外,新廣告法中(第五章法律責任部分除外),與網絡廣告相關的條款尚有第44條第一款:“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適用本法的各項規定。”該款主要是一個宣示性的規定,對于哪些互聯網的傳播形式屬于廣告,從而受到廣告法的規制,已在《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中明確,本文暫不討論。另外,相關條款還有第19條:“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音像出版單位、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以介紹健康、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廣告。”第36條:“廣告發布者向廣告主、廣告經營者提供的覆蓋率、收視率、點擊率、發行量等資料應當真實。”第40條:“在針對未成年人的大眾傳播媒介上不得發布醫療、藥品、保健食品、醫療器械、化妝品、酒類、美容廣告,以及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游戲廣告。”此外,還有第45條:“公共場所的管理者或者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對其明知或者應知的利用其場所或者信息傳輸、發布平臺發送、發布違法廣告的,應當予以制止。”
(一)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范疇
正如前文所言,網絡廣告發布的門檻極低,個人成為重要的廣告發布主體,而原廣告法中的廣告發布者只限定了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法律和現實出現了嚴重的脫節,暴露出巨大的監管真空。為應對這一沖擊,此次廣告法修訂將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范疇,新廣告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本法所稱廣告發布者,是指為廣告主或者廣告主委托的廣告經營者發布廣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這一條的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以下簡稱: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解讀》中是這樣解釋的:“1994年的廣告法規定,廣告發布者只能是法人或者其他立法組織。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等的發展,一些自媒體也成為廣告發布渠道,自然人也可以成為廣告發布者,因而此次修改將廣告發布者的范圍擴大到了自然人。”[1](6)可見,將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的概念,其目的正是應對網絡時代自然人發布廣告給原廣告法帶來的沖擊。
新廣告法將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的概念后,使得廣告發布者的概念適應了網絡時代廣告發展的趨勢,填補了之前的監管真空。但接下來的問題是,作為自然人的廣告發布者,是否應受到與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同樣的監管?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原廣告法和新廣告法關于廣告登記的規定。原廣告法第26條規定:“從事廣告經營的,應當具有必要的專業技術人員、制作設備,并依法辦理公司或者廣告經營登記,方可從事廣告活動。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單位的廣告業務,應當由其專門從事廣告業務的機構辦理,并依法辦理兼營廣告的登記。”新廣告法將這一條修改如下:“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單位從事廣告發布業務的,應當設有專門從事廣告業務的機構,配備必要的人員,具有與發布廣告相適應的場所、設備,并向縣級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廣告發布登記。”對這個修改,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的解讀是:“按照這一修改,對于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單位以外的從事廣告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無論是廣告經營者還是廣告發布者,都不再需要進行專門的廣告經營登記。”[1](6)
不再需要進行專門的廣告經營登記,按照筆者的理解,也就是放開了廣告的經營、發布準入門檻,不再對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單位外的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做特殊資質要求,這無疑順應了網絡廣告發展的潮流,*在海量的網絡廣告發布者面前,傳統的具有一定門檻的廣告經營(發布)登記制度很難再實行。不對網絡廣告規定專門的登記程序,取消準入門檻的規定,在廣告法的修訂過程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從歷次征求意見稿的變化可以看出。國務院法制辦征求意見稿對該條表述為:“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單位、互聯網站從事廣告發布業務的,應當依法辦理廣告發布登記。”也就是說互聯網站要與電臺、電視臺、報刊一樣辦理廣告登記。準入門檻取消是在全國人大一審后公布的征求意見稿中,“互聯網站”的表述被刪除了,從而取消了準入門檻。一審修改后,二審和三審中沒有再發生變化。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按照這一條,自然人無需去辦理專門的廣告發布登記手續,那么自然人是否還需要辦理工商登記手續呢?按照原廣告法配套規則的監管要求,自然人從事廣告經營都必須進行工商登記。*參見《廣告管理條例》第6條第三項的規定。從現實情況來看,要求海量的網絡廣告發布自然人進行登記,是十分困難的,也必將極大地提高自然人進入網絡廣告發布的門檻。可資參考的是,在網絡商品銷售領域,法律并沒有強制要求作為自然人的網絡商品交易者進行工商登記,而是以第三方交易平臺的實名認證來替代。*《網絡交易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從事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經營者,應當依法辦理工商登記。從事網絡商品交易的自然人,應當通過第三方交易平臺開展經營活動,并向第三方交易平臺提交其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證明、有效聯系方式等真實身份信息。具備登記注冊條件的,依法辦理工商登記。”如果借鑒網絡交易領域的做法,不強制要求自然人做工商登記,那也需要考慮采取怎樣的替代性措施,這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二)廣告經營者、發布者審查義務的變化
原廣告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依據法律、行政法規查驗有關證明文件,核實廣告內容。對內容不實或者證明文件不全的廣告,廣告經營者不得提供設計、制作、代理服務,廣告發布者不得發布。”新廣告法對這一條做了重要修改,改為:“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依據法律、行政法規查驗有關證明文件,核對廣告內容。對內容不符或者證明文件不全的廣告,廣告經營者不得提供設計、制作、代理服務,廣告發布者不得發布。”
與原廣告法相比,新廣告法在廣告經營者、發布者審查義務上有兩個重要的變化:第一,對廣告內容的審查由“核實”改為“核對”;第二,不得發布的廣告由“內容不實”改為“內容不符”。兩字之變,明確了廣告經營者、發布者對于廣告內容的審查義務為形式審查義務。對這個形式審查義務,我們做兩點討論:
其一,形式審核義務意味著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應由廣告主來負責。與原廣告法相比,新廣告法明確了由廣告主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負責,其中第4條第二款規定:“廣告主應當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負責”。
新增廣告主對廣告內容真實性負責的條款,是與廣告經營者、發布者對廣告內容審核義務的變化相適應的,即廣告主是廣告內容真實性的負責人,廣告經營者、發布者僅承擔“核對”的形式審查義務。這樣規定的合理性在于,只有廣告主才真正了解其產品或服務與廣告宣傳的對應性(即廣告的真實性),*全國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在對第4條的解讀中指出“廣告主是一切廣告活動的最初發起者,應由其保證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解讀》,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頁。作為第三方的廣告經營者、發布者實際上很難去核實廣告的真實性。這個核實的義務,在廣告已經海量化的網絡廣告時代,更是難以實現。所以,由“核實”改為“核對”,既符合行業自身規律,也順應了網絡廣告行業發展的趨勢。
其二,形式審查義務的關鍵詞在于“核對”,這個“核對”應作何理解?筆者認為,新廣告法中的“核對”對應的是“不符”,正如原廣告法中的“核實”對應的是“不實”。這里的“符”是指廣告內容與廣告主所提供證明文件的相符性,即一致性。“核對”義務是指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應審核廣告內容與廣告主所提供的證明文件是否相符。例如廣告主在廣告內容中聲稱其產品有國家發明專利并提供了專利證書,廣告經營者、發布者應審查這個專利證書與其廣告聲稱內容的一致性,包括專利號、專利類型的對應性等。
除了審核廣告內容與廣告主提供文件的一致性外,廣告經營者、發布者不再審查廣告內容本身的真實性。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按照新廣告法第四條第二款,是由廣告主負責的。
(三)規制網絡廣告發送、發布的形式,防止侵擾用戶
在網絡廣告時代,一些惡劣的網絡廣告形式,如頻繁的垃圾廣告郵件和無法關閉的彈窗廣告,都對網絡用戶造成了侵擾,侵害了用戶的權益。對此問題,新廣告法也有所應對。
新廣告法第43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當事人同意或者請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發送廣告,也不得以電子信息方式向其發送廣告。以電子信息方式發送廣告的,應當明示發送者的真實身份和聯系方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絕繼續接收的方式。”第44條第二款規定:“利用互聯網發布、發送廣告,不得影響用戶正常使用網絡。在互聯網頁面以彈出等形式發布的廣告,應當顯著標明關閉標志,確保一鍵關閉。”
先看第43條,該條第一款設定了向住宅、交通工具等及以電子信息方式發送廣告的前提:需經當事人的同意或請求。第二款則規定了以電子信息方式發送廣告還必須履行兩個義務:其一,明示發送者的真實身份和聯系方式;其二,向接收者提供拒絕接收的方式。
從立法沿革來看,第43條部分繼承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和201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第7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未經電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電子信息接收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固定電話、移動電話或者個人電子郵箱發送商業性電子信息。”《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下文簡稱“消法”)第29條第三款規定:“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從條文內容來看,廣告法第43條明顯是繼承“決定”和“消法”的規定而來,但也有重要的變化。“決定”和“消法”都規定了接收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繼續發送商業性信息,廣告法第43條則沒有了此規定。作為替代,第43條要求發送者向接收者提供拒絕接受的方式,同時明示發送者的真實身份和聯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當事人明確表示拒絕,不得繼續發送”的規定在廣告法修訂草案中曾有過出現,但最后通過的修訂案刪除了該規定。對這一過程的詳細介紹可參見:司曉等《新廣告法亮點述評》,http://www.tisi.org/Article/lists/id/3917.html?ADTAG=Online.wx.center.D,2017年2月6日。該文進一步認為,刪除“當事人明確表示拒絕,不得繼續發送”的規定意味著“為互聯網廣告的曝光量預留空間,兼顧行業發展的正常秩序和業態需求,在用戶權益與市場活力之間做出了平衡選擇。”
對于第43條的條文規定,尚有兩個問題需要明確:第一,該條所保護的對象,即條文中所言的“當事人”是僅指自然人,還是包括法人及其他組織?按照全國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的觀點,該條中的“當事人”僅指自然人,該條之設計目的是防止不良廣告對個人私人空間和私生活的侵擾。[1](96)“私人空間”、“私生活”這樣的概念顯然僅對自然人有意義,而不涉及法人和其他組織。
第二,“以電子信息方式發送廣告”包含哪些種類的廣告。新廣告法中并沒有對“電子信息”或“電子信息方式”進行界定。從立法沿革來看,“決定”第7條已經開始使用“電子信息接收者”這一概念,從立法繼承性的角度而言,可以合理推斷廣告法第43條電子信息的概念由此而來。“決定”同樣沒有清晰界定“電子信息”的概念,但從其條文表述來看,該條的“電子信息”指通過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和電子郵箱發送的信息。*“決定”第7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未經電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電子信息接收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固定電話、移動電話或者個人電子郵箱發送商業性電子信息。雖然該條中沒有明確“電子信息”或“電子信息接收者”的概念,但從最后一句“不得向其固定電話、移動電話或者個人電子郵箱發送商業性電子信息”,可以反推出“電子信息”在該條中指通過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和電子郵箱發送的信息。按照全國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對廣告法的解讀,第43條廣告法中“電子信息方式”的涵蓋面遠大于“決定”,“不僅包括電話、短信、傳真,而且包括通過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平臺、應用軟件等方式發送廣告的行為。”[1](97)
就第44條而言,先一般性地規定網絡廣告不得影響用戶的正常使用,然后針對彈出式廣告,具體規定必須顯著標明關閉標志,并且確保一鍵關閉。對于第44條,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何謂彈出式廣告?按照國際互聯網廣告行業組織——互動廣告局(the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簡稱IAB)的定義,是指利用瀏覽器,在用戶瀏覽網絡時,開啟一個新的窗口呈現廣告。[4]從這個概念出發,彈出式廣告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其開啟具有自動性,往往是應用戶的某個行為(例如打開一個網站)自動激活,這一個過程即所謂的“彈出”;二是廣告呈現的頁面是一個新的窗口,這個新窗口獨立于用戶原有的瀏覽頁面,因此也可以獨立關閉,而不影響原有的瀏覽頁面。從這個彈出式廣告的概念出發,如果廣告是融合于用戶原有瀏覽頁面內的,不屬于彈出式廣告,不應受到第44條的規制。*當然,從立法語言來看,第44條用的是“在互聯網頁面以彈出等形式發布的廣告”,這里的“等”可以涵蓋除彈出廣告外的其他網絡廣告形式。筆者認為應嚴格把握這個“等”字,不能做擴大解釋。“一鍵關閉”的對象應是影響到用戶正常使用網絡、非基于用戶意志打開(自動彈出)、可以在不影響用戶原有瀏覽頁面的情況下獨立關閉。融入頁面的廣告(例如網頁固定位廣告)不能因為這個“等”字的存在而納入第44條的規制范圍。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如果這些融入頁面的網絡廣告也要一鍵關閉,那么從公平的角度,是否應要求報紙頁面中的廣告也能“一鍵關閉”呢?這顯然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參見司曉等《新廣告法亮點述評》,http://www.tisi.org/Article/lists/id/3917.html?ADTAG=Online.wx.center.D,2017年2月6日。
三、結 語
此次廣告法的修訂,應對了網絡廣告帶來的沖擊,并且解決了一些問題,例如自然人納入廣告發布者主體,彌補了法律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將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對內容義務由“核實”變為“核對”,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網絡廣告經營者、發布者的負擔;規制網絡廣告發送、發布的形式,防止侵擾用戶,保障了用戶的權益。
當然,廣告法作為整個廣告領域的基本法,不可能規定得過細。同時,由于引入很多新的概念和規則,很多問題也尚待進一步明確。例如自然人經營廣告是否必須辦理工商登記?電子信息廣告的外延應包括哪些形式?這些問題的解答可能需要在后續的立法中明確。新廣告法的配套規則中已有專門針對網絡廣告的部門規章——《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作為新廣告法的配套法規,該辦法在新廣告法規則的基礎上,做出了進一步的細化,新廣告法遺留的問題已在該辦法中得到明確。*《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于2016年9月1日正式實施。
[1]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212.
[2]騰訊科技.谷歌移動廣告量超3000億條5個月增1000億[EB/OL].http://finance.qq.com/a/20101019/003141.htm,2017-02-07.
[3]陳晨,趙玉瑾.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廣告審核責任的再思考[EB/OL].http://unt.cssn.cn/fx/fx_jjfx/201508/t20150810_2113108.shtml,2017-02-07.
[4]IAB.Pop-upGuidelines[EB/OL].http://www.iab.net/guidelines/508676/508767/1461,2017-02-06.
[責任編輯:詹小路]
本文系2014年廣東省普通高校創新強校特色創新類項目“網絡廣告市場知識產權問題研究”的研究成果。
姚志偉,男,副教授,法學博士。(廣東金融學院 法律系,廣東 廣州,510521) 王媛媛,女,碩士研究生。(暨南大學 法學院,廣東 廣州,510632)
D922.8
A
1008-6552(2017)02-01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