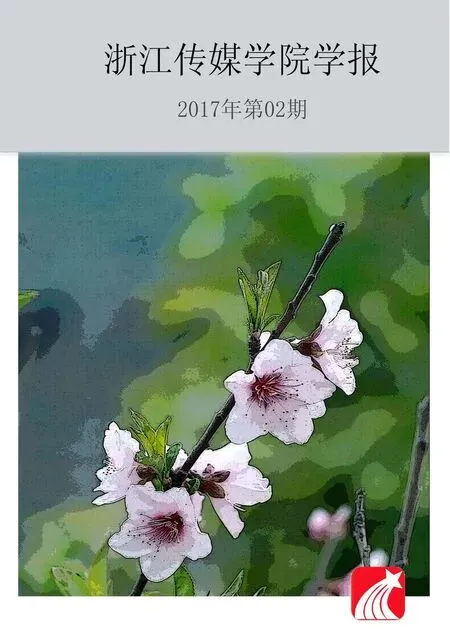游記《奇石》中的“飛散”探究
錢建偉
游記《奇石》中的“飛散”探究
錢建偉
美國記者彼得·海斯勒的新書《奇石》跨越12年,用外來者的眼光描述了來自中國、美國、日本、尼泊爾以及埃及5個國家的24個故事。旅行、遷徙、探尋乃至逃離的人們在文化上同化、被同化,或者形成混合狀態。書中所述的各國故事很好地闡釋了后殖民研究中的飛散概念,以及作者在無形中流露出的帝國飛散視角;有關中國當今改革變遷中人們的故事亦闡明了“故土飛散”這一概念:處于時代變革中的中國人雖未流落他國,卻在故土上同樣演繹著背離傳統、文化混合以及繁榮衍生的飛散主題。
同化;混合狀態;帝國飛散;故土飛散
英語中的“飛散”(diaspora)一詞最早是指猶太人的大流散,離開本國去他國生活和工作,而后泛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追溯其希臘語詞源,飛散指“種子或花粉‘散播開來’,植物得以繁衍”。[1]由此,傳統意義上的飛散必是由遷徙、移民等導致,與背井離鄉的流亡者有關,敘述其在新舊環境與文化中所面對的文化沖突與混合、對身份的探究以及尋根等概念。流亡者跨越地域、民族,在至少兩種文化的夾縫中懷念故土,抑或融入新文化環境,再或在二者中竭力尋求平衡。流亡作家們通過“個人史或是家庭史來寫民族史和族群史”[2]敘述漂泊與苦難,重生與融合。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對俄羅斯的塑造,托尼·莫里森對非洲移民的描述,卡勒德·胡塞尼離開、重回祖國阿富汗又再次回歸到美國的“家”中的經歷等,都是如此。
作為后殖民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飛散除了關注從殖民地流亡到歐美發達國家的人民外,也關注流向第三世界的歐美“帝國飛散者”[1](117)。理論家們關注飛散的文化性和政治性,討論流亡者的話語權、自我與他者等概念。無論是討論殖民者統治的優越感還是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后殖民飛散研究都更具政治性。
然而在當今社會背景下,上述飛散概念仍有其狹隘之處。本文通過細讀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譽為“研究現代中國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國旅居生活12年的美國記者彼得·海斯勒新書《奇石》,并對其中來自5個國家的故事分析對比,試圖說明海斯勒無時無刻不體現于書中的“帝國飛散”視角;同時,本文通過分析書中所述那些生活在故土(從未離開故土,或是離開又回歸故土),卻在時代變革下同樣經歷著文化沖擊、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生活著的中國人的故事,試圖對后殖民飛散理論稍作補充,提出“故土飛散”這一概念,這類“流亡者們”沒有背井離鄉,卻同樣或懷念過往,或敬畏未來,抑或在摸索中尋求某種出路。
一、帝國飛散:放逐中對美國的再造
飛散向來有傳統派(社會學、人類學派)和后現代派(文學、文化研究派)之分。傳統派貼近現實,研究飛散群體的類別及特征,而后現代派更注重精神意識層面的飛散探究。根據科恩在《全球飛散:概論》中的傳統派分法,飛散群體應包括“受害飛散群(如曾受迫害的亞美尼亞人)、勞工飛散群(因勞務輸出而到國外工作的群體)、帝國飛散群(因帝國主義擴張而去第三世界國家的歐洲人)、商貿飛散群(因貿易、商業活動而到其它國家的商務人士)、文化飛散(如在加勒比地區存在的混合型文化)”。[1](116)在后殖民理論中,這些由前宗主國即歐美國家流向第三世界的帝國飛散人群通過“游記、歷史著作或傳記等敘述……基于殖民秩序的優越感……或是表達……對受壓迫民族的極大同情感,及對西方帝國主義思想的莫大的憎恨感”。[3]如此定義下的帝國飛散群要么是意圖去同化曾經被壓迫的民族,要么就是去揭露自身的黑暗面,而和被壓迫民族并肩站在一起。作為強勢的一方,他們不需要像第三世界飛散群體(或叫前殖民地飛散群體,即由前殖民地國家移居至西方國家的人口)那樣面對漂泊與苦難、抉擇是否應該銘記故土文化、卑躬屈膝地融入新世界、進行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等問題,而是更多地關注他們自己所帶來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他們保持自身的優越感,充當本國文化“傳教士”的角色;他們主動被第三世界同化,徹徹底底地成為他們所同情的民族中的一員;他們在這種掙扎中逐漸成為“混血兒”。面對這些選擇,他們總是掌握著主動權,這一點尤為重要。在當今科技全面聯通全球的大環境下,帝國飛散群體體現出更為豐富且復雜的特征,值得進一步對其思索與探究。
海斯勒在《奇石》的序言中提到:“我盡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來者的視角融合在一起。”[4]這其中的“盡可能”包含著嘗試與無奈:嘗試用公平客觀的角度去敘述,不戴有色眼鏡,不用作為一個來自發達國家的優越視角去看待他所處國家的人與事,可他又無奈于這種嘗試極有可能以失敗告終。筆者認為,海斯勒的嘗試無可挑剔,但是書中仍隨處可見他作為美國人、一個外來者的視角——帝國飛散的視角。他選取的事例、在故事中與人們的對話、他的行為舉止都是一種由上往下的優越視角。然而,在中國十多年的生活又讓他主動接受被同化,成為一個文化上的混合者。他恰好成為上述的“混血兒”。
《奇石》是一本主要關于中國的書,也包括來自日本、埃及、尼泊爾和美國西部的幾個故事。作為駐外記者的海斯勒游歷這些國家和地區,以外來者的身份觀察,極力采用融合的視角,卻無時無刻不顯示著其美國國民性。他的身上保留著傳統的帝國飛散者的特性。海斯勒1996年加入美國和平隊來到中國,然而,對于和平隊的指導手冊,他卻沒有什么好感:“美國人對于發展中世界國家的看法相當古板”,[4](177)這些國家或是需要被拯救,或是令人感到恐懼。美國優于這些國家,隊員們似乎如若不充當那里的救世主,那就應該對那里的荒蠻落后感到膽戰心驚。盡管海斯勒已經認識到這種觀點不當,但他還是未能克制自己的優越感。2000年,北京為申辦奧運會而在胡同里修建的公共廁所被海斯勒戲稱為“奧林匹克衛生間”[4](28),這種在海斯勒看來極具戲劇性——“仿佛是一道光從奧林匹斯山直接照耀到這條窄小的巷子,隨后留下了一座宏偉的建筑”[4](15)。如果考慮到奧林匹克廁所便利的現代化設施,對居住在胡同里的人們生活的改善,早已將這種便利視為尋常的海斯勒應該就不會如此描述了吧。在丹東的旅館遭遇小偷,海斯勒完全忘記了在美國“誰都不會去追他們”[4](394)的意識,“我使勁地揍他……朝他揮舞著拳頭”[4](392),“我尤其記得自己無與倫比的憤怒,憤怒的程度現在都讓我害怕不已”[4](394)。做筆錄時面對警察的質疑——為什么似乎很瘦弱的小偷,只顧狂奔而逃,從不還手?海斯勒產生不安:“既然他已經丟下了我的財物,我為什么還會對他一頓猛揍?他為什么絲毫沒有反抗?”[4](402)令海斯勒不安的,或許正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外國人的身份對中國底層人們的威懾力。“徒步長城”和“甲骨文”兩個故事里,中國人不懂得保護本國文化遺產:沒有人潛心研究作為祖國象征的長城,百姓隨意毀壞長城遺址;在文革中被迫害的研究甲骨文的陳夢家,甚至差點放棄博大精深的漢字而采用拉丁字母等等。與中國人相反,這些事情里,都有肩負著拯救使命的歐美人出現:日復一日沿長城做徒步野外考察的石彬倫,沿長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4](49)并成立“國際長城之友協會”的英國地理學家威廉·林賽、編輯陳夢家網站的匈牙利人Imre Galambos。中國人對本國傳統文化的“淺薄意識”被他批駁,歐美人的“執著與睿智形象”也隨之樹立起來。
中國之外,在尼泊爾從事志愿工作的和平隊隊員納吉夫,在落后的山區為當地修建水利設施,利用美國辛苦募捐而來的錢修建學校,從事有機農業。“當地的人們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會淚流滿面……把他看作是恒河之源的濕婆神。老人們一邊擰水龍頭一邊說道‘這都是他賜給我們的。’”[4](56)來自發達國家的納吉夫和當地人合作,也會被評價為“這么一個美國人竟敢如此信賴卡納馬嘉這么一個沒怎么讀過書的人”[4](61)。納吉夫的父母20世紀70年代從印度移民到美國定居,屬于吠舍階級,但是在尼泊爾,人們只將他看作美國人。他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幫助,是偉大的援助之舉,卻也是優越階級才能辦到的。混跡于日本黑道的美國人杰克·阿德爾斯坦,“扮演犯罪報道記者的角色”[4](210),在險象環生的黑社會里混得如魚得水,其原因正如黑幫中人所述:“他不用考慮那樣的禁忌或者界線……如果他是日本人,現在早就沒命了”。[4](209)外來者,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外來者”之牌,總是這些人的護身符。
海斯勒和這些進入他國的歐美人都自愿遠離家鄉,將自己放逐,他們旅行、工作、融入當地的生活,他們看似在竭力隱去自身的帝國性,卻無時無刻不在他們看待當地事物的眼光和他們的行動中體現著他們作為帝國飛散者的優越性。這些記述在書中的故事,時刻暗示著:這是些奇聞,它們與我們歐美國家的事情不同,我們國家的事情恰恰是這些怪事的反面。他們在放逐中不斷地重塑祖國形象,實現著對故土帝國的再造。
然而,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帝國飛散者,海斯勒及其記錄的帝國飛散群體雖在無意識情況下體現出自身的優越感,但他們又能主動地融入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接受當地同化,模仿并采用當地的方式做事,逐漸將自身塑造為“混血兒”。這從和平隊的創建目的中就可見一斑:“和平隊從一開始就被描述成對外事務的幫手,不過他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培養美國人對于外部世界的認識”,[4](185)“它變成了唯一教會美國人拋掉國民性格的政府機構”,[4](177)這些歐美人在異國他鄉看著一個個異于自己的他者在自己面前展現,他們努力了解當地,了解即是獲知,是明白,在一定的積累之后,這種了解逐漸被內在化,最終在某種情形下,他們的言行便和當地的人們趨于一致。“奇石”一節故事中多次體現了這一點。和平隊志愿者麥克·高提格就儼然成為了一個被中國人稱贊的喝酒好手,他甚至學會了像四川的農民們那樣用牙齒打開啤酒瓶蓋,[4](182)即使后來回到美國,成為由哥倫比亞大學負責主辦的《亞洲法律》雜志總編輯后,“他臉上依然帶著一絲源于中國的表情——略顯震驚、不知所措、難以適應”。[4](187)在4次大小交通事故之后,海斯勒完全學會了中國人處理事故的方式。屢次損壞汽車出租公司的捷達汽車之后,他起初的不安與誠心誠意愿意賠款的心態逐漸演變為“我是他們的老顧客”這種中國人慣用的貪圖便宜的心態,然后讓事情不了了之。原本認為交通事故后應該按正規手續理賠的海斯勒,更學會了像中國人一樣“通常在大街上用現金當場解決問題”,[4](238)在大街上討價還價,氣勢洶洶,理直氣壯。十多年之后,海斯勒載著大量的中國家具回到美國西部落基山小鎮,同樣回去的,還有他在中國養成的生活習慣和一些思想理念。“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謀劃,在中國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這種習性越發糟糕,因為那里的每個人似乎都活在當下”,[4](342)他更將在落基山偏僻小鎮落戶視為在實現自己“中國版的美國夢”。[4](345)或許正是從中國人順從地面對生活的角度出發,美國鈾旯灣鎮的故事才能被提倡環保與健康的發達國家的人們所理解。環保人士宣稱鈾污染會引發肺癌等諸多疾病,鈾旯灣鎮人們卻熱愛著那里的生活,喜歡戶外運動,堅決否認鈾會危害健康,即使在被政府強迫搬離之后仍每年回來舉行野餐聚會,懷念當年生活的美好。
正如海斯勒在序言中提到的發明了“創造性口吃”的美籍華人牛康民一樣,這些帝國飛散者們在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內在了的異國文化思想中生活著。他們用優越的眼光審視他鄉事物,隱約地對那些他們眼中奇怪的事情說著“不”,甚至時不時地充當起拯救他人的使命。但他們對當地文化探究得越深入,也就越容易被同化,進而開始無意識地模仿,直至在某些方面成為當地文化中的一員。外來者的身份和“本地人”的身份相融合,在必要時刻巧妙利用,帝國飛散者們比第三世界飛散者們在自身身份重新定位上更具主動性,他們心甘情愿地成為“混血兒”。
二、故土飛散:飛散理論的縱軸
顛覆傳統理論中飛散群體必須是背井離鄉的,故土飛散者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家園,有的甚至從未跨出國門,卻同樣遭遇多種文化沖擊。在科技,尤其是通訊手段如此發達的今天,不同國家民族間的交流更加便捷與頻繁。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增強,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突然大量涌入,對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造成極大的沖擊。他們的生活、精神狀態發生巨大而迅速的變化,他們處在本國傳統與外來思想的夾縫中,面臨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他們被迫跨出本國傳統生活幾千年來早已設定好的人生軌跡,帶著無盡的迷茫重新摸索人生道路。與傳統的第三世界飛散群體相比,他們在本國土地上面對著上述種種問題,本文在此將這類人定義為“故土飛散群”。這些人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生活在自己的家園故土,卻同傳統的飛散群體一樣要面對文化沖擊、重新審視自我并尋求文化認同出路的現象,這即是本文要提出的概念:故土飛散。
故土飛散可謂對諸多飛散概念的補充,也可以說是飛散概念里的一條縱軸。借用數學上的三維坐標來說明:如果說傳統概念里的第三世界飛散群強調人們地域上的流動,是橫向的散播,像是在一個二維的平面上平移,關注的只是位置的變化;那么故土飛散研究的則是人們精神、文化以及思想因時間而引起的變化,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一地域的人們因時代變化,不斷受外來文化影響而導致的對自身文化的重構。故土飛散就像是三維坐標里的縱軸,為傳統的飛散概念引入時間變化的因素。它強調人們在某一既定地域上所遇到的因時代變遷和外來文化沖擊而導致的一系列思想、文化上的改變。故土飛散所說的時間,更強調當下與將來,強調當今的全球化背景,它與童明在《飛散的文化和文學》一文中提到的時間性不同:
飛散者的根是文化的根,也是歷史的根。許多飛散群體以其民族經歷的歷史災難作為力量的凝聚。……在后殖民的世界上,殖民歷史的種種創痛回憶幽靈似的隨飛散者旅行;飛散者在西方國家的生活經歷有時提供條件,促成受壓迫情緒復現,以暗恐心理形式出現。[4](10)
童明所述飛散者的“時間性”或“歷史”指飛散者的文化根源,是過去的經歷,往往是悲慘的、災難性的苦難經歷,強調的是過去的經歷對現在的影響。故土飛散強調的時間概念與此不同。故土飛散的“時間”是指現在和將來的時間,注重在外來思想的沖擊下,人們或盲目迎新,或失去自我方向,或摸索著尋求平衡的過程。《奇石》這本書中有關中國的故事尤能闡釋這一概念。
2011年海斯勒的《尋路中國》出版時,柴靜就曾稱贊海斯勒寫出了我們當今中國人所熟視無睹的中國,以及一種親切的酸楚感——“那個酸楚就是劇變的實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不管你知不知覺,承不承認”。[5]“酸楚”正是處在改革與發展中的中國人內心的真實寫照,他們迥異的反應和行動值得人們思考。這種例子在《奇石》中比比皆是。一個個大大的“拆”字給眾多北京胡同帶來厄運,在急切的現代化進程中,人們擯棄傳統,追求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承載了幾千年老北京人情味的胡同壽終正寢,人們“毫無反抗地搬走了”,[4](25)他們順從地忘記過去,麻木地接受著未來,似乎一切都是程式;他們恪守規則,按部就班地生活。極為相似的是三峽庫區的移民們,只是多了幾分對未來的盲目渴望。大部分人無奈但順從地接受背井離鄉的命運,搬至政府新建的移民住宅區,甚至遷往外省,他們認為新的總比舊的好,因為如果不修大壩,這些貧窮的人們“還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夠達到現在的水平”。[4](141)對于環境保護、山體滑坡等問題,他們視而不見,只想抓住眼前的機會,“政策經常在變……人們覺得改革是一次機遇。大家都要抓住這個機遇,因為那可能又不會長久。[4](142)突然看到外面世界的中國人,上到政府有關部門,下至百姓都是盲目的,就如同第三世界飛散者一樣,只想瞬間丟掉過去的一切,換上全新的面孔。
類似艾米莉這樣的由內地城鄉來深圳打拼的年輕人是故土飛散者中的代表。深圳突然間由小漁村變身為經濟特區,人們的精神趕不上經濟與物質的爆炸式發展。迅速發展的深圳吸引了大量的年輕人來追尋夢想,他們拿到比內地多得多的工資,他們急切、好奇地望向國門之外,被外來文化卷席,甚至連根拔起,致使他們迷茫無措。深圳有著當時相對閉塞的內地所沒有的自由與開放,“一幫幫小伙子肆無忌憚地高聲交談,一群群女孩子開懷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見老人。這就是深圳的自由——這里沒有陳規,也沒有過去,大家都遠離家人”。[4](112)這個城市似乎一瞬間洗刷掉了所有傳統的束縛,但在突如其來的自由面前,人們又手足無措了,正如艾米莉所說:“人們太忙于賺錢,都不知道該怎么生活”,[4](108)“深圳是一座沒有靈魂的城市……每個人都很焦慮——無法找到平靜”。[4](122)然而在金錢、感情、毒品、賭博以及性方面,年輕人們又無法擺脫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即便認為深圳比中國其他地方性開放是件好事,艾米莉仍會說:“但不應該越過一定的界線……跟傳統道德有關。”[4](119)在深圳的這群人是某種程度上的故土移民,他們雖然離開故鄉來到外來思想大量涌入的沿海城市,但他們沒有踏出國門、沒有直接處在西方文化之中,他們所認為的“來自西方社會”的思想觀念并不完全是西方文化,而是一種在本國長久的壓抑中生活太久、突然得到自由時產生的無節制釋放和混亂。他們在這種混亂中掙扎,既要自由,又對背棄傳統的做法誠惶誠恐。與第三世界飛散者相比,他們背負著更沉重的歷史傳統,他們身在故土,處在自身文化傳統之中,在接受外來文化時會受到更大的傳統道德束縛。
另有一些故土飛散者,他們踏出國門去學習先進技術并受某些品質的感染,為的是回故土,以一種中國式的創造性的形式發展。他們已經找到平衡,摸索到出路。地處內陸的蕪湖市,本沒有特色產業、沒有自己的品牌,卻“通過向外國人學習,但保持控制權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礦企業”,[4](302)充分利用中西方各自的優勢,取他人之長,拿來為己所用。“就像學畫畫。你不可能一開始就畫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臨摹他人的畫作”。[4](311)在競爭、學習中,甚至不惜采用一些違規之舉,得到國外廠商的設計機密。精明、敢于冒險、擁有進取心的蕪湖人(奇瑞汽車公司)最終成為中國最大的汽車出口商。海斯勒寫道:“我在中國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發讓我想起美國。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擁有無止境的樂觀和精力……他們一向擁有自命不凡的品質,相信自己能夠戰勝時間——中國人的這一品質比美國人還要美國化。”[4](314)這種“走出去—引進來—發展自我”的人們是本文故土飛散者的又一特征。他們機智地選取外界文化中可以為我所用的部分,果斷拿來,與本土融合,最終塑造出強大的自我。占據地理優勢的溫州人,眼光一直瞄準國外,他們不僅務實而勤勞,且更具有國際化眼光,甚至“帶著諸多美國文化的影子”。[4](385)溫州人清楚自身優勢,了解國外市場需求,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任何人無需離開大陸,便能在溫州發現其與傳統計劃經濟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諸多東西”。[4](385)當美國人對經濟危機產生恐慌的時候,溫州人依然表現出中國人特有的順勢而為的心態:“如果全世界都在走下坡路,我們不過是跟著走下坡路而已,那么事情實際上并沒有太大的變化。”[4](391)他們不慌不忙,在中外文化的交融中從容淡定、游刃有余。麗水畫匠陳美子是另一個充分利用外界資源發展自我的例子。在全球互聯網浪潮的影響下,“麗水很難看到外國面孔……城內的國際化面貌卻比比皆是”。[4](321)陳美子接收來自海外的要將照片轉化成油畫的訂單,她手中描繪著異國風情,卻“從不認為有必要與外部世界發生深層次的關聯”。[4](327)作為全球互聯網絡一端的勞動者,她沒有受到傷害,更沒有迷失方向。她通過市場窺探著零星的、碎片式的遙遠的國度,同時將自己的文化信仰與外來文化區分得一清二楚,日子過得舒心靜謐。身處故土,通過現代化手段了解外界、獲取信息,又巧妙地將外界的資源拿來為我所用,這類人是故土飛散者中最為成功的典范。
三、結 語
“‘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狀類似其他物品的石頭”。[4](172)飛散者們就似這奇石,在文化交融中被塑造成各式各樣的形狀。帝國飛散者們無意識地保留優越感的同時,也會主動接受同化,為自身構建起混合身份,在恰當的時刻選擇恰當的身份,周旋于故土、他國。
無需跨越國界,在當今通訊科技幫助下,在故土上迎來外國文化沖擊的故土飛散者們掙扎于傳統與外來文化之中,有的盲目求新,有的迷失了自我,更多的已尋得獨特的出路。海斯勒在開羅為此書作序時寫到:“我又搬到了一個全新的國家,開始學習一種全新的語言。有時,這感覺令我喘不過氣來,有時,它又讓我如歸故里。”他本人就是一粒飛散的種子,游歷各國,吸收、融合著各種文化,日益豐盈,以其特有的方式繁榮燦爛。
[1]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113.
[2]張德明.流浪的繆斯——20世紀流亡文學初探[J].外國文學評論,2002(2):57.
[3]童明.飛散的文化和文學[J].外國文學,2007(1):89-99.
[4][美]彼得·海斯勒.奇石[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5.
[5][美]彼得·海斯勒.尋路中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1.
[責任編輯:高辛凡]
錢建偉,男,講師,博士生。(浙江傳媒學院 大學外語教學部,浙江 杭州,310018)
I712.075
A
1008-6552(2017)02-01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