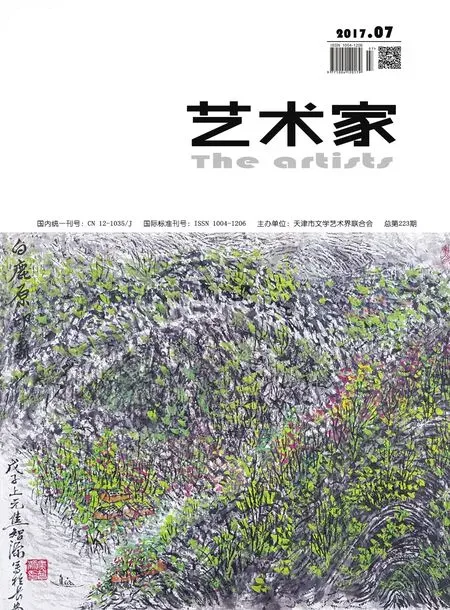淺析傳統白字戲《樓臺會》的音樂唱腔
□鐘靜潔 廣東省海豐縣白字戲藝術傳承中心
白字戲是我國南方地區比較古老的一個地方劇種,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按調式,白字戲音樂可分為輕六調、重六調、活五調、反線調和小調等,表現功能相對固定,如輕六調式擅長表現輕快的情懷,但也會表現悲憤的;重六調式擅長表現莊重的正劇;活五調式擅長表達哀怨、悲切;而反線調式擅長表現喜悅、歡快的情調。當然,這是相對的,在具體運用上則是千變萬化。
白字戲傳統保留劇目《樓臺會》,是八大連戲中《英臺連》的一個折子戲,屬大鑼鼓戲。這出戲在音樂唱腔設計上運用了許多特殊的處理,形成獨特的音樂風格,久演不衰。
第一,它的音樂唱腔雖然采用活五曲調式【下山虎】的曲牌,但不以大鑼鼓伴奏,卻用小鑼鼓戲進行音樂唱腔設計,把輕快的小鑼鼓節奏和哀怨的活五曲調式曲牌糅合在一起,從而形成特殊的藝術風格。
第二,這出戲從頭到尾有一百多句唱詞,只用了一個活五曲調式【下上虎】的曲牌,把全出戲巧妙地貫穿起來,以同一曲牌表達不同的人物內心情感。音樂素材雖少,但曲調變化豐富而不單調,音樂形象也較為鮮明。
第三,它雖屬于悲劇,但作者在創作時安排了多處喜劇情節,主要來自早期白字戲《事久弄》,語言生動風趣,富有鄉土氣息。戲劇情節悲喜交替,以喜襯悲,使后來的“悲”產生強烈的戲劇效果。
一、唱詞方面
白字戲傳統劇目的唱詞多以七字句為主,句式結構對音樂創作帶來很大的限制,多數傳統劇目由于唱詞結構呆板,唱腔設計出來的往往是那種節奏單一的子母句結構。而這出《樓臺會》的唱詞,七字句的較少,多以長短句的自由體為主,一句唱詞少則三字,多則達十三個字,句式靈活而富于變化,相比整齊的七字句唱詞,更是靈活自由。因此,若配合得當,白字戲劇目的唱詞也能運用長短句的結構形式,更易于抒發人物的思想感情。
此外,這出《樓臺會》的唱詞多處運用并列和反襯的寫作手法,如“牛童歌唱”“鳥只聲啼”;“離別三旬近”“如隔三秋景”;“細襪宮鞋”“杏臉桃腮”……這些并列短句與自由體的長短句,在節奏上形成鮮明的對比,豐富多變的句型結構體現了詞句的韻律美。
二、唱腔方面
唱腔的設計是為了臻美塑造人物的音樂形象。白字戲《樓臺會》雖然從頭至尾僅僅套用了一個活五調【下山虎】曲牌,但它在劇中經過不同樣式的處理,較成功地塑造了劇中不同人物、不同情懷的音樂形象。可見,白字戲的曲牌可塑性較大。
例一,戲一開場,山伯懷著喜悅的心情演唱了第一段曲“不憚迢遞,有約前來訪故人……”這段曲牌結構比較完整、嚴謹,由曲牌頭—滾唱—曲牌尾組合而成,全曲分為四個樂段,起承轉合的安排都很合理。若按一般規律,一到滾唱便是平板的子母句結構,而在這里,旋律設計上對兩個并列短句的音樂節奏做了壓縮,為“弦笛鼓樂動人心”旋律的展開做了鋪墊,在旋律節奏上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對“動人心”三個字的處理,使用了切分節奏,音調翻高六度,猶如奇峰突起,與曲牌頭旋律的一高一低形成倒映式的音樂效果。并運用一張一弛和壓縮重復的手法,使音樂有起有伏,層層深入,把音樂情緒推向高潮,音樂形象可謂生動鮮明。
往后,山伯在全出戲的其他唱段都根據這一曲牌自由發展,但不再用曲牌頭了,有的以滾唱起句,有的以三板起句,有的則以散板起句,使全劇聽來不覺重復,劇中人物音樂形象的變化自然統一,生動鮮明。
英臺和銀心的唱腔也是根據這一曲牌演變而來的,多是在曲牌頭第二句旋律做了合理的處理而引起全曲質的變化。
例二,英臺與山伯會廳見面,一番寒暄之后,英臺接唱“自別書林,朝夕思兄暗沉吟……”曲牌頭第二句曲的第一小節,山伯唱的“有約前來訪故人”音型是“1 5”起,而英臺唱的“朝夕思兄暗沉吟”音型是“1 4”起,兩者只是相差了一個大二度,一音之差,女性矜持的音樂形象便顯現出來,這一變化實是微妙。
為了使英臺與銀心的音樂有所區別而樹立不同的身份,唱腔設計也做了不同的處理。
例三,就在銀心聞得“門外聲響”,出門看個究竟時唱的一段曲子,曲牌頭與英臺唱的相同,但加上了英臺唱時的串子。“(牌頭略)舉步近前去,一旁細端詳……”這便是滾唱的開始。若按以往規律,音樂就顯得呆板平敘,很難塑造活潑伶俐的小丫頭形象。所以,旋律在“細端詳”的“詳”字上做了夸張,從“7 ”音躍至“4”音,是一個減五度的不協和音程,隨著又來了一個富有形象動作的拖腔,把銀心伶俐的人物形象描繪得十分細致傳神。
白字戲歷來男女同腔同調,沒有明確的行當唱腔分別。但在這出《樓臺會》中,似乎又有了行當唱腔分類的雛形,如山伯的小生腔、英臺的青衣腔、銀心的花旦腔。同時,襯詞拉腔“啊咿噯”在生行中運用得較少,在旦角中的應用則較多。
三、間奏音樂方面
白字戲《樓臺會》整出戲只用了二首弦詩過門音樂,是為了刻畫英臺愁悶的心情,其他則運用小串子(即小過門)。音樂素材簡單,手法干練,運用得當,可以說是這出戲在間奏音樂運用上的一個典型例子。如上半場,山伯和銀心的唱腔用同樣的串子,以輕快的小鑼鼓節奏伴以跳躍的音樂旋律,渲染了喜悅的氣氛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而對英臺的內心描繪,音樂則是緩慢沉重的。
四、板式結構
1.散板
一種是散而無板,另一種是散而有板。如英臺唱的“誰知你”這句是散而無板,至“不曉文君意”則是散中有板。再如,英臺與山伯合唱的“噯——欲別又難忍,難舍恩愛情……”這不但散中有板,而且是內含某一具體因素的板式。另外,還有一種哭板,也是叫散板,如“噯,山伯我的梁兄……”它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2.二板(2/4)
這一板式中,唱詞往往有并列短句,旋律做壓縮重復,對抒發感情、渲染氣氛起了積極作用。當然,這個戲的音樂唱腔設計也存在不足。如由于僅僅運用一個曲牌,移調手法相對較少,音樂色彩略感單調了些。此外,就是有些唱腔特別是拖腔運用不恰當,如銀心唱的“卻原來,事久阿哥來相訪”之后的拉腔,這句旋律的情緒偏向哀愁傷感,不符合當時銀心的內心情緒。
白字戲是我國古老而珍稀的地方劇種之一,豐富的音樂唱腔值得我們去發掘研究、總結整理。本文是筆者在長期的戲劇工作中,對白字戲傳統劇目《樓臺會》音樂唱腔的一點粗淺探研,希望能為劇種的傳承工作做點微薄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