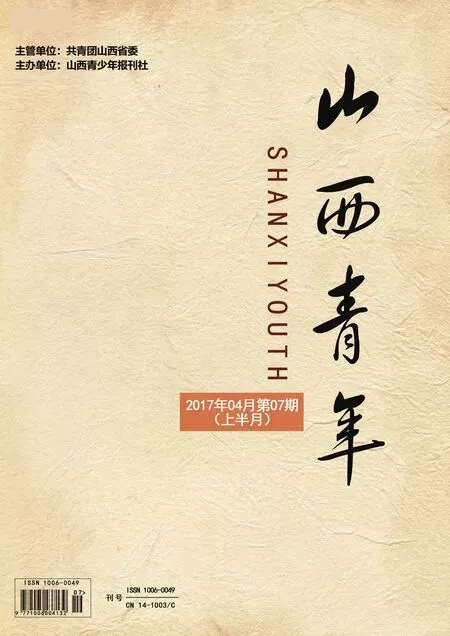淺談?lì)欘R剛與《古史辨》的編寫
李彥釗
云南民族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云南 昆明 650500
?
淺談?lì)欘R剛與《古史辨》的編寫
李彥釗*
云南民族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顧頡剛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是古史辨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他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涌現(xiàn)出的大師,在古史研究、古文獻(xiàn)研究、歷史地理學(xué)和民俗學(xué)等多領(lǐng)域都作出了杰出貢獻(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上,顧頡剛以大膽疑古和編著《古史辨》而聞名。
顧頡剛;古史辨;編寫;態(tài)度
筆者最早聽聞?lì)欘R剛先生是在大學(xué)課堂上,老師講到他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diǎn),對此感到很欽佩。長期以來,學(xué)界對他的疑古思想褒貶不一。顧頡剛認(rèn)為研究古史應(yīng)先破后立。雖以辨?zhèn)问窞榧喝危渥罱K目的是辨?zhèn)吻笳妗?923年顧頡剛寫給友人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這篇文章發(fā)表以后,引起史學(xué)界眾多學(xué)者就相關(guān)問題持久的考辨論議,以此為標(biāo)志,引發(fā)了中國近代史學(xué)上著名的古史辨運(yùn)動(dòng)。學(xué)者們關(guān)于中國上古史的爭論考辨文章,從1926年到1941年的15年間,被陸續(xù)編輯成書,編成了《古史辨》七冊。其中一、二、三、五冊為顧頡剛編著,四、六冊由羅根澤編著,七冊上中下三編由呂思勉、童書業(yè)編著,但也是受到前者的感召和鼓勵(l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這套論叢,并在顧頡剛建議下增加了歷史地理內(nèi)容的第八冊。
在這套書的開始,是顧頡剛先生的《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對于自己從小如何開始讀書,對讀書的認(rèn)真態(tài)度,一直講述到如何漸漸從前人的思考中受到啟發(fā),不斷探索印證自己的觀點(diǎn)。之后有顧頡剛先生所作自序,亦是他的一篇自傳,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顧頡剛的“疑古”思想的發(fā)端和他嚴(yán)謹(jǐn)認(rèn)真的治史治學(xué)態(tài)度。讀過之后,筆者有幾點(diǎn)感慨如下。
第一,歷史是需要多讀書,多思考的。每一部著作都離不開長久的思考與積累,有其深厚的淵源可尋。顧頡剛先生在文中提到自己“從小就喜歡亂翻書”,且家中各類書籍不少,“我祖父研究《說文》和金石,室中放著許多古文字學(xué)書。我的父親為了應(yīng)書院的月試,多作詩和律賦,室內(nèi)多文學(xué)書。”他的叔父喜歡治近代史,也有不少史書,顧頡剛在上私塾時(shí)每天放學(xué)回來就偷偷看這些書,漸漸受到了各方面的啟發(fā)。由此感到讀書應(yīng)該是多方面的,正因?yàn)槭菍W(xué)習(xí)歷史,更應(yīng)全面。顧頡剛先生在隨后的自序中提到他對于歷史的最早認(rèn)識(shí),令人頗有親切的認(rèn)同感,是幼時(shí)祖父母所講的故事傳說等。“祖父所講大都屬于滑稽一方面,如‘諸福寶(蘇州的徐文長)’之類;祖母所講則大都屬于神話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類。”他提到“祖父帶我上街,或和我掃墓,看見了一塊匾額,一個(gè)牌樓,一座橋梁,必把它的歷史講給我聽,回家后再按著看見的次序?qū)懗梢粋€(gè)單子。因此,我的意識(shí)中發(fā)生了歷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歷史的認(rèn)識(shí):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都是慢慢兒地積起來的,不是在古代已經(jīng)有,也不是到了現(xiàn)在剛有。這是使我畢生受用的。”
文中提到當(dāng)他感到家中藏書無法滿足知識(shí)欲后,便去買書。在挑選書籍的過程中,又學(xué)會(huì)了看書籍目錄,并對此產(chǎn)生了興趣,知曉了如何尋找自己所需要的書籍。甚至通過書目開始了對資料的歸納整理。通過編《清代著述考》,半年寫成了二十冊,將清代學(xué)者的學(xué)問方向及其作出的貢獻(xiàn)大致摸了一個(gè)底,看清楚了近三百年來學(xué)術(shù)思想的演進(jìn)。讀過之后,感到顧頡剛先生對待學(xué)問是極認(rèn)真細(xì)致的,這樣的由興趣發(fā)端進(jìn)而認(rèn)真的去做一些整理工作,對于我們?nèi)绾稳グl(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是很有啟發(fā)的。之后顧頡剛結(jié)識(shí)了胡適先生,兩人通信交流,顧頡剛先生逐漸接觸到了前人古人的批判思想,開始有了自己的一系列想法。現(xiàn)在看來,每個(gè)價(jià)值重大的發(fā)現(xiàn)或?qū)W說的提出,都是一步步得來,而且知識(shí)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
第二,對歷史的態(tài)度必須是嚴(yán)肅認(rèn)真又負(fù)責(zé)的。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一開始就提到“兩年前,我在《努力周報(bào)》附刊的《讀書雜志》里發(fā)表辨論古史的文字時(shí),樸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dāng)時(shí)答應(yīng)了,但老沒有動(dòng)手。”這樣的原因只是“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論文字沒有做完,不能得到一個(gè)結(jié)束;我總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可是我的生活實(shí)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幾個(gè)較大的題目,做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絕不易找到時(shí)間,這是使我永遠(yuǎn)悵恨著的。”另外他講讀別人做的書籍時(shí),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yàn)榭戳丝梢粤私膺@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占有的地位。可見看書先看序是十分有必要的一件事。
他對自己的工作有著強(qiáng)烈的責(zé)任感,“老實(shí)說,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時(shí)勢,我的個(gè)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bào)紙上的發(fā)表固然是近數(shù)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象與假設(shè)的構(gòu)造是一點(diǎn)一滴地積起來的。我若能把這個(gè)問題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沒有辜負(fù)了我的個(gè)性和環(huán)境,沒有什么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說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會(huì)給與我的損害了。”
用顧頡剛先生自己的話來說,他對于自己的地位有了這種的了解,所以對于自己的見解(給一般人詫為新奇的)常以為是極平常的,勢所必然的,他只順著自然的引導(dǎo),而自己無力于其間,“譽(yù)我和毀我的話都是廢話而已。”但對于贊揚(yáng)或詆毀的人,他也不嫌怪,因?yàn)樗麄冎灰姷剿闹鲝埖臄嗝妫荒苌钪浪膫€(gè)性和環(huán)境。
在《世紀(jì)學(xué)人自述》中,也載有顧頡剛的一部分,是除《古史辨》自序后他的又一自傳,從先生的自述中,可看出他是個(gè)性格有些矛盾的人,而矛盾的性格或許恰恰促成了他的學(xué)術(shù)生涯。他對于自己性格的分析是強(qiáng)烈的責(zé)任心、同情心以及知識(shí)欲,他在自述中寫道他對于自己的認(rèn)識(shí)是,要過的生活只有兩種,“監(jiān)禁式”即關(guān)在圖書館和研究室里,沒有一點(diǎn)人事的紛擾,或者“充軍式”即到各處地方去搜集資料,開辟學(xué)問的疆土。
第三,是對于學(xué)習(xí)、學(xué)問的態(tài)度。并不是渾渾噩噩無所謂的,而是認(rèn)真思索,找定一個(gè)明確的方向。感觸較深的一段是“我以前對于讀書固極愛好,但這種興味只是被動(dòng)的,我只懂得陶醉在里邊,想不到書籍里的東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驅(qū)遣著,把我的意志做它們的主宰。現(xiàn)在忽然有了這樣一個(gè)覺悟,知道只要我認(rèn)清了路頭,自有我自己的建設(shè),書籍是可備參考而不必作準(zhǔn)繩的,我頓覺得舊時(shí)陶醉的東西都變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最初也有普通的想法“當(dāng)我初下‘學(xué)’的界說的時(shí)候,以為它是指導(dǎo)人生的。”而且“學(xué)了沒有用,那么費(fèi)了氣力去學(xué)為的是什么!”,但是“但經(jīng)過了長期的考慮,始感到學(xué)的范圍原比人生的范圍大得多,如果我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jìn)。所以在應(yīng)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qū)別,但在學(xué)問上則只當(dāng)問真不真,不當(dāng)問用不用。
學(xué)問固然可以應(yīng)用,但應(yīng)用只是學(xué)問的自然的結(jié)果,而不是著手做學(xué)問時(shí)的目的。從此以后,我敢于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這一個(gè)覺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jì)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xué)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gè)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這一段現(xiàn)在看來是講出了顧頡剛能取得后來學(xué)術(shù)上成就的根源吧。怎樣去作學(xué)問,看來也是一個(gè)需要認(rèn)真思考的問題。
另外,在自序的后面,他提出了三點(diǎn)。主要是講:第一,書的性質(zhì)是討論性質(zhì)而不是定論的性質(zhì),而且里面也有錯(cuò)誤,但是為了保存當(dāng)時(shí)討論的真相,所以不加改正保存下來了,希望后來看到的人能夠切實(shí)批判,不輕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現(xiàn)在剛才開頭,要得到一個(gè)總結(jié)論不知要到什么時(shí)候,他的工作,在于辨證偽古史方面,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盤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討論出結(jié)果來。并且“希望大家對于我,能夠知道我的學(xué)問的實(shí)際,不要作過度的責(zé)望。”第三,認(rèn)為這本書序文與內(nèi)容中都還尚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歡迎對這些問題同樣懷有興趣的人去探索解決。最后提到“總結(jié)一句話,我不愿意在一種學(xué)問主張草創(chuàng)的時(shí)候收得許多盲從的信徒,我只愿意因了這書的出版而得到許多忠實(shí)于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進(jìn)展的諍友。”一代大師對于治史治學(xué)的勤懇樸素、實(shí)事求是的優(yōu)良作風(fēng),謙虛慎重的態(tài)度躍然紙上。雖然學(xué)術(shù)界對于“疑古”與否展開了討論,意見不一,但是新學(xué)說的提出畢竟活躍了人們的思想,開辟了新的史學(xué)道路,對于以后歷史的發(fā)展起了促進(jìn)作用。
[1]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世紀(jì)學(xué)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李彥釗(1990-),女,漢族,河南安陽人,云南民族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xiàn)代史。
K
A
1006-0049-(2017)07-00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