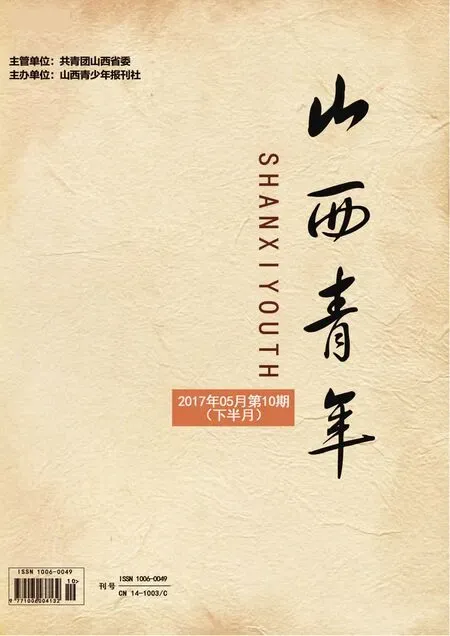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探討
葉 欣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
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探討
葉 欣*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新形勢下對寬嚴相濟及坦白從寬政策的進一步發展,有利于建立和緩寬容、繁簡分流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試點初期,須明確該制度的內涵及適用條件,厘清該制度與英美法系辯訴交易制度的關系,堅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明確偵查階段為該制度適用的起點,訴訟各階段的主要任務,尤其重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
認罪認罰從寬;辯訴交易;程序構造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要求,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中第13項對此項制度提出了具體要求,在試點改革初期該制度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雖學界與實務界對其作出了不少研究,但當前依然沒有明確且細化的實施標準。本文擬從宏觀角度探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中國式構建。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涵
(一)何為“認罪”
刑法規定的自首與坦白是現行較為典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根據刑法第67條的規定,對于自首與坦白情形,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而條文中明確規定成立自首與坦白的前提條件是“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認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所犯罪行,對于被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認罪不要求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性質或罪名有準確的認識,可能出現行為人雖然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但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構成其他罪名。這種對于法律認識上的錯誤并不影響對“認罪”的判定,屬于法律適用的范疇,應當由處于專業領域的司法機關作出判斷并向其闡明。“認罪”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具體的事實情節進行辯解,但所作辯解不能影響犯罪構成。
(二)何為“認罰”
“認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認罪的基礎上自愿接受所犯之罪帶來的刑罰后果。理解“認罰”應當從三個方面來把握:第一,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在犯罪嫌疑人認罪的基礎上自愿接受處罰,檢察機關提出較之不認罪情形下更輕的量刑建議,若嫌疑人同意并簽署具結文書,則可以認定為“認罰”。[1]第二,“認罰”包括程序上同意適用簡化后的訴訟程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目的在于實現繁簡分流,提高訴訟效率,因此適用這一制度必然要求程序從簡,犯罪嫌疑人須正確理解并同意在庭審中放棄部分訴訟權利。第三,對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認罪認罰要求犯罪嫌疑人積極主動退贓退賠,取得被害人的諒解,這是悔罪的重要表現。因此,對于“認罰”的認定,應當同時滿足上述三個條件。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定位
(一)與“寬嚴相濟”和“坦白從寬”的關系
寬嚴相濟與坦白從寬是我國長久以來堅持的刑事司法政策,認罪認罰從寬是貫徹該原則性政策的具體制度。從這個角度看,“認罪認罰從寬”是“寬嚴相濟”中的“寬”和“坦白從寬”中的“寬”的政策延伸。但同時,認罪認罰不僅包括坦白,還包括實體法上的自首與程序法意義上的刑事和解、簡易、速裁程序等,可以說它是“坦白從寬”的進一步發展。“寬嚴相濟”中的“嚴”是該政策的另一個層面,在此意義上“認罪認罰從寬”是否表示不認罪認罰即從嚴呢?
寬容司法的理念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充分的加深,刑事訴訟謙抑化是當今司法發展的必然趨勢。“失去寬容的世界,必然是一個野蠻的世界;失去寬容的世界,必然是一個愚蠢的世界;失去寬容的世界,必然是一個僵化的世界。”[2]雖然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我國刑訴法規定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原則并沒有確立沉默權制度,但立法者修改刑訴法時增加這一條,就標志著接受了當今世界具有普世價值的“反對強迫性自證其罪”的刑事訴訟規則[3],我國正在朝著確立被追訴人沉默權的文明司法前進,即使步伐還不夠大。事實上,坦白從寬政策與沉默權在訴訟價值屬性和目標上具有一致性,都旨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實現司法公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不坦白、不認罪,或者只自愿承認犯罪事實但不同意量刑建議,也不能以此為從重處罰的情節。認罪認罰從寬必須遵循罪刑法定原則,不得超越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而任意協商,對于不認罪認罰者來說,事實上其所須承擔的刑罰則嚴格依照法定情節確定,勢必比認罪認罰的刑罰更重。從這個角度看,認罪認罰從寬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寬嚴相濟政策中的“嚴”。
(二)認罪認罰與辯訴交易
辯訴交易是英美法系國家一項重要的司法制度,指檢察官以撤銷部分指控或向法院提出更輕的量刑建議為條件,與被告方協商換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長期以來,我國刑事法學界對于引入辯訴交易制度持否定態度,2002年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審理的孟廣虎案是我國第一起采用辯訴交易的案件,此案件發生后引起各界爭議,目前來看,我國的文化背景和刑事訴訟的基本理念決定了不宜引入辯訴交易,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控辯雙方的協商雖有借鑒英美法系的辯訴交易制度的內容,但二者存在本質區別。
1.證明標準不同
此為二者最明顯的區別,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證明標準必須堅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如果將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納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來,就違背了疑罪從無的基本原則,而變成疑罪從輕。刑訴法第53條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無論被告人是否作有罪供述,都不能依據口供定罪,依然要根據檢察機關提供的證據判斷案件是否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而辯訴交易適用的大多數情況是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檢察機關以輕緩的量刑建議來換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辯,交易結果往往與案件事實無關,而是取決于辯訴雙方各自擁有的資源,包括證據的質和量、雙方的談判技巧和手段高下、被告人的心理狀態等。[4]
2.交易(協商)的內容不同
在辯訴交易模式下,將被告人選擇作有罪答辯或者無罪答辯作為被告人的一種權利,該權利的行使不以公訴方的同意為前提,辯護人只有選擇有罪答辯的建議權,最終決定權屬于被告人,其可自愿和理智地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答辯,檢察機關則被賦予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對已經成立的罪名降格起訴甚至不起訴。因此,辯訴交易中,雙方可就指控的罪名和罪數達成協議,處于消極中立地位的法官則在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辯的基礎上直接作出判決,也不經開庭聽證和辯論來作實質審查。而我國認罪認罰從寬機制是建立在罪刑法定與罪刑相適應基礎上的,不允許控辯雙方就罪名和罪數進行協商。雖然在實體上被告人可以得到較輕的處罰,程序上可簡化某些環節,但對判決的影響是法定的從寬結果而非控辯雙方協商的結果。即使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法官仍然須開庭審理,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內對被告人依法予以從輕處罰,不得因被告人認罪認罰而隨意減輕刑罰甚至改變為較輕的罪名。
三、訴訟各階段程序構造
(一)偵查階段
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否適用于偵查階段,目前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只能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適用,因偵查階段的任務為取證,若賦予偵查機關促成犯罪嫌疑人認罪協商的權力,可能導致重口供輕證據的情形,甚至出現刑訊逼供,導致冤假錯案。[5]這一觀點值得商榷,現有的立法及司法解釋多處鼓勵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如實供述罪行,如刑法第67條第3款規定:“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此處“犯罪嫌疑人”的表述應視為肯定了在偵查階段如實供述也應認定為坦白。《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對于庭前坦白與當庭認罪作出了不同階次的量刑規定:應當看到,在偵查階段促進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對于偵查機關搜集證據提供了更多路徑,對于一些犯罪手段、實施場所極為隱蔽的案件,可根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提取線索,獲取盡可能多的證據。
(二)審查起訴階段
作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控方,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承擔著與犯罪嫌疑人進行控辯協商的任務。首先,我國檢察機關擁有控訴職能與法律監督職能,因此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中,依然要堅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對于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材料進行客觀審查,對于依法不構成犯罪或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也不可默認與其協商量刑建議。其次,若案件達到法定證明標準,檢察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以及從寬處罰的建議,并聽取辯護人與被害人的意見,對于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并同意量刑建議的,雙方簽署具結書,檢察機關據此在起訴書中寫明情況并提出盡可能具體的量刑建議。再次,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可能對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產生影響,除法定不起訴外,刑事訴訟法規定了酌定不起訴以及附條件不起訴:“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對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另外,根據《試點辦法》規定,認罪認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提起公訴。
(三)審判階段
此前正在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條件是: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自愿認罪,當事人對適用法律沒有爭議的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盜竊、詐騙、搶奪、傷害、尋釁滋事等情節較輕,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單處罰金的案件,進一步簡化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相關訴訟程序。[6]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沒有案件類型的限制,亦沒有審判程序的限制,即不管是普通程序還是簡易程序、速裁程序都可適用。在法庭審理程序上,認罪認罰從寬只是對普通程序的某些環節作了簡化,審判機關仍然必須開庭審理后才能進行裁判。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中,法院不必再對案件的定罪問題進行實質審理,應集中審理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以及量刑是否合理兩方面的問題。法院可專門舉行聽證會,就被告人認罪認罰自愿性以及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為保障弱勢方被告人的權利,應由公訴方證明被告人是自愿認罪認罰的,被告方若提出異議,公訴方應舉出相應證據加以說明;雙方若對量刑建議有異議,法院還應結合雙方意見進一步調查。[7]若法院經審查認為被告人自愿簽署的具結書是真實合法的,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在合理的法定刑幅度內,就應當予以采納;若經審理認為被告人事實上不構成犯罪或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認罪認罰的,可不采納檢察院的建議,轉由其他程序審理。對于被告人是否可以上訴的問題,筆者認為,考慮到該制度的程序分流目的與效率價值,應當對被告人上訴的情形予以限制,只有在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量刑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以及一審程序的正當性等問題上出現異議才允許被告人上訴。
四、結語
在當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工作中,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通過實踐進一步探索明確,如偵查階段該制度的適用與防止刑訊逼供造成冤假錯案的矛盾如何避免,如何在實現繁簡分流的前提下兼顧實體公正與訴訟效率,如何保障辯護律師的有效參與等等,如何構建適應我國“水土”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仍須在摸索中不斷完善。
[1]陳衛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J].中國法學,2016(2).
[2]賀來.寬容意識[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22.
[3]何家弘.中國式沉默權制度之我見——以“美國式”為參照[J].政法論壇,2013(1).
[4]廖明.辯訴交易:美國經驗與中國借鑒[J].法治論壇,2009(4).
[5]陳衛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J].中國法學,2016(2).
[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06/28/content_1869454.htm,2016-12-3.
[7]陳瑞華.“認罪認罰從寬”改革的理論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運行經驗的考察[J].當代法學,2016(4).
葉欣(1994-),女,華東政法大學,2015級訴訟法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
D
A
1006-0049-(2017)10-0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