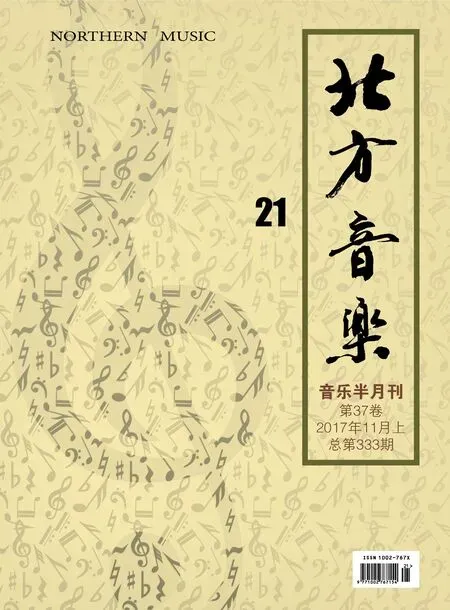試論西方中世紀(jì)音樂(lè)與同時(shí)期中國(guó)音樂(lè)之差異
王 婧
(徐州幼兒師范高等專(zhuān)科學(xué)校,江蘇 徐州 221000)
中世紀(jì)在西方歷史上一直被作為“黑暗時(shí)代”來(lái)看待,其實(shí)不然,今天的史學(xué)家更傾向于用客觀的態(tài)度來(lái)對(duì)待。正如蔡良玉在《西方音樂(lè)文化》中所說(shuō):“假如中世紀(jì)沒(méi)有孕育進(jìn)步的思想,文藝復(fù)興就不會(huì)有所承襲。”[1]當(dāng)西方音樂(lè)步入中世紀(jì)時(shí),正值我國(guó)的隋唐五代及宋元時(shí)期,春蘭秋菊,各有千秋,本文就中國(guó)音樂(lè)和西方音樂(lè)在同一時(shí)期的兩個(gè)較為突出的不同點(diǎn)進(jìn)行論述,對(duì)西方音樂(lè)有一個(gè)更清晰的認(rèn)識(shí),對(duì)同一時(shí)期的中國(guó)音樂(lè)也做了回顧和了解,從而讓我們的視野從自己的專(zhuān)業(yè)擴(kuò)展到更廣闊的空間,豐富和提高自己。
一、音樂(lè)中心機(jī)構(gòu)方面
在西方,中世紀(jì)文化受基督教影響最大,甚至被基督教所壟斷,整個(gè)中世紀(jì)就是一個(gè)基督教的世界。那些不滿(mǎn)于羅馬統(tǒng)治者政治壓迫,并渴望從宗教中獲求一點(diǎn)精神安慰的猶太有產(chǎn)者在這時(shí)參加了基督教社團(tuán)。隨著這股力量的不斷壯大,這些有產(chǎn)者給所屬教會(huì)提供經(jīng)費(fèi)、活動(dòng)場(chǎng)所,并為教會(huì)制定教義,宣傳教會(huì)主張等,無(wú)形之中逐漸形成了以基督教教會(huì)為中心的統(tǒng)治機(jī)構(gòu)。統(tǒng)治階級(jí)可以通過(guò)基督教來(lái)擴(kuò)大統(tǒng)治基礎(chǔ)。基督教徒既已被引入向往天國(guó)和超凡脫俗的幸福中,必然會(huì)把塵世認(rèn)作是個(gè)墮落鄙俗的世界,意念之中有著天國(guó)與俗國(guó)的對(duì)比,促使教會(huì)和國(guó)家這兩種社會(huì)合二為一了,這也成為了中世紀(jì)被稱(chēng)為“黑暗時(shí)代”的有利鑒證。從上述的分析來(lái)看,在音樂(lè)方面,基督教的教會(huì)音樂(lè)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音樂(lè)中心機(jī)構(gòu)是教會(huì),教會(huì)壟斷了官方的音樂(lè)機(jī)構(gòu)和社會(huì)的音樂(lè)活動(dòng)。
在中國(guó),從歷史淵源上講,“王權(quán)主義”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核心,宣揚(yáng)君主至上,認(rèn)為君主是全社會(huì)的最高主宰者,君主是人間的天地。這種王權(quán)主義是君主政治的需要,強(qiáng)化了君主專(zhuān)制統(tǒng)治,并通過(guò)多種社會(huì)化渠道,直接控制和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shí),君主則是全社會(huì)最高的主宰者。因此在音樂(lè)上,以神圣般的君主為中心的宮廷音樂(lè)占有主要地位,音樂(lè)中心機(jī)構(gòu)則是宮廷,宮廷和王室壟斷了官方的音樂(lè)機(jī)構(gòu)和社會(huì)的音樂(lè)活動(dòng)。
西方的教會(huì)思想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教會(huì)音樂(lè)崇拜上帝,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為教會(huì)服務(wù),為宗教禮儀服務(wù),帶有功利性;相對(duì)于西方占統(tǒng)治思想地位的教會(huì)思想,中國(guó)的君主思想則是在社會(huì)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宮廷音樂(lè)歌頌皇帝的豐功偉績(jī),是為宮廷娛樂(lè)和宮廷祭祀服務(wù)、為國(guó)家的政治所服務(wù)的音樂(lè)。
西方教會(huì)通過(guò)必要的活動(dòng)場(chǎng)所和完備的教育體系,如教堂,修道院,學(xué)校及其圖書(shū)館等來(lái)培養(yǎng)音樂(lè)家,以男孩為主,并在教堂里雇傭知識(shí)淵博、技藝精湛的音樂(lè)家,使教會(huì)音樂(lè)家的聰明才智得到了發(fā)揮的機(jī)會(huì),推動(dòng)了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促使“個(gè)人作曲家”開(kāi)始出現(xiàn),無(wú)形中使教會(huì)成為音樂(lè)創(chuàng)作,音樂(lè)理論,音樂(lè)教育的中心;相對(duì)于西方一些音樂(lè)活動(dòng)場(chǎng)所,中國(guó)唐朝在宮廷設(shè)立了分別擔(dān)任不同職能的大樂(lè)署、鼓吹署、教坊、梨園等,來(lái)管理教習(xí)音樂(lè),訓(xùn)練培養(yǎng)樂(lè)工,這里不僅僅是以男孩為主,唐玄宗非常重視選拔和培養(yǎng)人才,尤其是在內(nèi)廷設(shè)立的梨園,宮廷梨園藝人不只是男子,也有女子。殊途同歸,宮廷也成為音樂(lè)教育的中心。
西方教會(huì)音樂(lè)以聲樂(lè)形式為主,最突出的是格利高里圣詠,一般禁止使用樂(lè)器,認(rèn)為樂(lè)器是魔鬼,而管風(fēng)琴是唯一被允許使用于教堂的樂(lè)器。 相對(duì)于西方以聲樂(lè)為主的教會(huì)音樂(lè),中國(guó)宮廷音樂(lè)是容聲樂(lè)、器樂(lè)、舞蹈、表演于一體的,如唐代大曲,又稱(chēng)燕樂(lè)歌舞大曲,是綜合器樂(lè)、 歌唱和舞蹈的大型樂(lè)舞。
二、音樂(lè)成果方面
第一,記譜法。西方13世紀(jì)就有了記錄節(jié)奏的記譜方法,體現(xiàn)在弗朗科的有量記譜法中,到14世紀(jì)的“新藝術(shù)”出現(xiàn)時(shí),記譜原則突出二分的“不完全拍”,體現(xiàn)在穆里斯和維特里提出的記譜原則;相對(duì)于西方,中國(guó)的記譜方面可分樂(lè)譜、舞譜及琴譜,它們是以記錄演奏技法為基本特征的手法譜,而真正能記錄節(jié)奏的準(zhǔn)確方法還未能發(fā)明。
第二,音樂(lè)律學(xué)。南宋蔡元定在《律呂新書(shū)》中提出了以古代“三分損益法”十二律為基礎(chǔ)的十八律理論,這在時(shí)間上是先于西方巴洛克時(shí)期的十二平均律的,不足的是十八律未能付諸實(shí)踐 ,而十二平均律卻付諸了實(shí)踐。
第三,世俗音樂(lè)。西方中世紀(jì)時(shí)期的世俗音樂(lè)包括游吟詩(shī)人、英雄業(yè)績(jī)尚松以及流浪藝人等,這些世俗音樂(lè)只是作為宮廷的娛樂(lè)音樂(lè),帶有功利性;相對(duì)于西方的世俗音樂(lè),中國(guó)在宋元時(shí)期出現(xiàn)的瓦子、勾欄、等演出場(chǎng)所以及陶真、貨郎兒等雜耍表演,這些才是真正的世俗民間藝術(shù),對(duì)于民間藝術(shù)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第四,藝術(shù)歌曲。中國(guó)宋代新出現(xiàn)了藝術(shù)性較高的民間歌曲,即藝術(shù)歌曲, 主要有“叫聲”、“嘌唱”、“小唱”、“唱賺”;而此時(shí)在西方,藝術(shù)歌曲還沒(méi)有顯露尖角,直到浪漫時(shí)期的舒伯特出現(xiàn),才將藝術(shù)歌曲提升到一個(gè)新的藝術(shù)境界。
第五,作曲家。西方中世紀(jì)時(shí)期,作曲家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逐漸產(chǎn)生。在當(dāng)時(shí),“個(gè)人”這一個(gè)小的單位已被社會(huì)所重視。阿奎那神權(quán)論中提升了個(gè)人的作用,個(gè)人個(gè)性的價(jià)值也有所保障,人只有在社會(huì)和國(guó)家之內(nèi)并通過(guò)社會(huì)和國(guó)家才能達(dá)到完善的地步。因此,“作曲家的產(chǎn)生是西方‘個(gè)人’創(chuàng)造觀念的產(chǎn)物,伴隨記譜的發(fā)展,‘無(wú)名氏’創(chuàng)作被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所代替。”[2]在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整個(gè)社會(huì)受封建專(zhuān)制主義的支配,當(dāng)時(shí)的音樂(lè)家則是受?chē)?guó)家政治擺布的,他們無(wú)地位,只是以“奴仆”的身份去接受現(xiàn)實(shí)。這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的“君尊臣卑”的映射。正如韓愈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論中論及到:“君當(dāng)然是上品,臣是中品,民是下品。上品與中品都有統(tǒng)治權(quán),下品只有被統(tǒng)治的義務(wù),被剝削的義務(wù)。”[4]因此在中國(guó),沒(méi)有西方所謂的“作曲家”,但音樂(lè)家的數(shù)量非常多,包括作曲家、詞作家、琴家、歌者,他們具有演奏古琴的高超技巧,傳授過(guò)技藝,并整理過(guò)琴曲,琴譜,也創(chuàng)作過(guò)新曲,但能查到姓名的很少。
再次,縱觀整個(gè)歷史發(fā)展趨勢(shì),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曾處于“貞觀之治”、開(kāi)元盛世”,到處洋溢著歡聲笑語(yǔ),經(jīng)濟(jì),文化,音樂(lè)都有著無(wú)可比擬的高度成就,但盛唐之后,許多方面開(kāi)始呈下坡趨勢(shì);而在西方,中世紀(jì)的黑暗漸漸退去,迎來(lái)的是“新藝術(shù) ”和文藝復(fù)興的曙光。這也是中西方音樂(lè)在同一時(shí)期的顯著差異。
綜上所述,同一時(shí)期內(nèi),西方音樂(lè)和中國(guó)音樂(lè)大相徑庭,但無(wú)論是“黑暗”中世紀(jì)的西方,還是政權(quán)更迭的中國(guó),它們只是歷史的一個(gè)小分支,它們相互影響,在歷史發(fā)展中,都有一定的進(jìn)步意義。如:基督教傳入中土、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根據(jù)他自己在東方的親歷目睹,撰成《馬可·波羅行紀(jì)》,無(wú)疑對(duì)于東西方之間音樂(lè)和文化的交流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在當(dāng)今世界上,不同國(guó)家之間存在著異樣的音樂(lè)文化,表現(xiàn)出各個(gè)不同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就像西方音樂(lè)和中國(guó)音樂(lè),地域不同,信仰不同,因而彰顯藝術(shù)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異中又有同,雖然出自不同地域,但它們共同組成了世界音樂(lè),它們是世界音樂(lè)的支流,殊途同歸,最終匯流成河,注入到世界音樂(lè)的長(zhǎng)河中,給世界音樂(lè)帶來(lái)更多的繽紛,注入更多的新鮮血液。從分析西方音樂(lè)與中國(guó)音樂(lè)之不同,我們可以得出,無(wú)論是怎樣一種音樂(lè),都有它存在的價(jià)值,我們應(yīng)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抱著客觀、實(shí)事求是的態(tài)度去看待、學(xué)習(xí)、研究它們, 這樣才能將知識(shí)融會(huì)貫通,達(dá)到學(xué)以致用的效果。
[1]蔡良玉.西方音樂(lè)文化[M].北京: 人民音樂(lè)出版社,1999.
[2]蔡良玉,梁茂春.世界音樂(lè)史音樂(lè)卷[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
[3]袁華音.西方社會(huì)思想史[M].天津:南開(kāi)大學(xué)出版社,1988.
[4]陳定閎.中國(guó)社會(huì)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0.
[5]轉(zhuǎn)引自?shī)W古斯丁.懺悔錄[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2.
[6]金文達(dá).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M].北京:人民音樂(lè)出版社,1994.
[7]馮文慈.中外音樂(lè)交流史[M].長(zhǎng)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