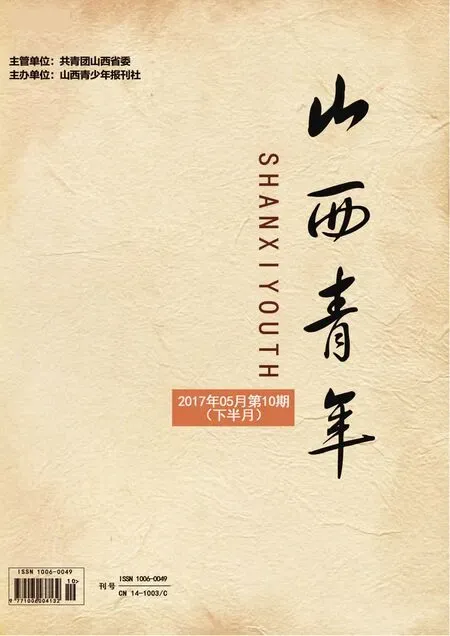這樣一種通達發舒的人生態度
——探尋《四書章句集注》中的孔子
朱萌然
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
這樣一種通達發舒的人生態度
——探尋《四書章句集注》中的孔子
朱萌然*
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至圣先師孔子時時刻刻親力親為,將儒家的翩翩君子之風和溫潤如玉之德,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謹慎虔誠地闡釋與發揚出來。不論面對禮崩樂壞的諸侯爭霸,還是身處百家爭鳴的軸心時代,孔子始終能夠恪守儒家君子的通達發舒之道,不卑不亢地向我們展示著生命之柔美、天地之和諧,使我們心生敬仰,感慨“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通達發舒;孔子;儒家思想;四書
司馬遷在其孔子傳的結尾寫道:“《詩》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慧心睿智的孔子,是悠悠千年里萬人景仰的“至圣先師”,同時也是踽踽獨行路上自娛自樂的“孤獨君子”。他拒絕隱逸避世,始終直面“禮崩樂壞”的人世,既不愿“逍遙游”,也不愿蠅營狗茍。他選擇了牢牢堅守住對道的信仰與保護,一句看似簡短單薄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出了孔夫子捍衛儒家精神與君子氣質的大氣概。于是,在人心不古、天翻地覆的亂世里,孔子努力使生命的精氣神與生活的真善美虔誠和諧地交織在一起,努力用天道的廣博無垠去滋潤和震撼山川樹木與花鳥雨露,努力使自己和他人在戰火紛繁中平和舒泰。
一、通達發舒——“君子之德”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德行乃為成仁之本,文藝則為行事之末。唯有守著根本,扎得根深,窮其本末,知所先后,方可入德矣。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余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在德行恰當的時候以文飾之,則在內仁德寬厚,在外文質彬彬,如此才是明德、修身和致于君子之道。
若德之不修,只是單單以“文”來裝飾自己,那么雖然看起來是一位文質彬彬的翩翩君子,卻因為內在根基的缺乏或軟弱,常常會面臨“亂了陣腳”和“失了原則”的尷尬境地,而這也正是千百年來我們從未停止探討“德”與“才”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更有甚者,不僅德之不修,而且“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只是一味地以華麗虛浮的外在來粉飾空虛貧乏的內心,那便真正“是吾憂也”了。
二、通達發舒——“成人之道”
“子不語怪、力、亂、神”。答于鬼神之問則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大概唯能坦蕩磊落,以誠待人,守著義理天道,方可以此延伸,慎終追遠以事鬼;唯能明德修身,克己復禮,盡著人倫之責,方可循著人性,樂安天命以知死。事人,事鬼,知生,知死,然后則可見害不避,見利不趨,常舒泰,少憂戚。
孔子說過:“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他還說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所以,孔子向往、追求的乃是融合政治人生與審美人生為一體的高質量的生命歷程與精神高度,是憂樂圓融的坦蕩蕩的君子人生。所以,要成就這樣通達發舒的“人”和如此自由舒展的“人生”,不求敬畏神秘且難以捉摸的鬼或神,也不靠縹緲無言且難以解答的生或死。循著義理天性自由暢快地培育生命和心靈,便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安和充實,不知老之將至。
三、通達發舒——“圣賢之樂”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門之樂,動靜之間,從容如此。因與自然造化融為一體,因此得以于形骸之外,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隨心舒發。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之貧如此,然賢人自有其所樂,因此得以處之泰然而不為功名富貴擾亂本心。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可見,去仁而享有富貴功名,君子不齒,唯小人樂之;守仁而粗茶淡飯,則其心無所違,其樂亦無窮。
短短幾句,灑脫卻不失厚重的圣賢氣象便躍然紙上,與此同時,一個熱愛生活、悠游自在、優哉游哉的孔夫子也使我們與其更加親近。天真,釋然,風輕云淡;爽朗,愜意,自娛自樂。與山水自然親近,與天地萬物親近,與自己的內心親近。在貧困潦倒時自得其樂,不為富貴功名所擾亂本心;在享受自然時自在暢想,不因世道衰敗而苦大仇深。縱使大道不行,縱使七零八落,縱使人生坎坷,縱使顛沛流離。只要心中自得其樂,萬物便皆備于我。
四、通達發舒——“暮年之哀”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為大道不行;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此為賢徒命短。子哭之怮。從者曰:“子怮矣。”曰:“有怮乎?非夫人之為怮而為誰!”夫子之痛惜,可謂至深,然其為隨性而發,由心而生,故又不失其正。之后,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數句之間,對弟子短命之無可奈何,與大道不傳之無能為力,溢于言表。
這就是孔子。樂便樂地“不知老之將至”,“哀”便哀地直呼“天喪予!天喪予!”然而,無論喜悲,均能得體合理,不失其正。樂是由心而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哀也是隨心而動,泣不成聲,淚如雨下。正是因為孔子始終捍衛著生命的圣潔與精神的高度,始終堅守著生活的本真與靈魂的質樸,所以才有了喜怒哀樂上的“致中和”與“不偏不倚”。
五、結語
至始至終,孔子都保持著對道與天命的堅守。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朱子如是評說:“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茍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夫子終其一生,向內求諸己,向外傳乎人,矢志不渝,甘顛沛落魄。其思想道路的選擇、政治理想的追求、精神信念的堅守,皆為此一道而已矣。最終,對道與天命的堅守成就了其通達發舒的人生。
于是,當垂垂老矣的夫子回首自己的人生歷程時,雖感慨無限、辛酸萬千,也依舊能夠問心無愧、淡然平和地這樣說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朱義祿.儒家理想人格與中國文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3]趙明.在塵世安頓人生——走進孔子的思想世界[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朱萌然(1996-),女,漢族,河南焦作人,河南師范大學,2014級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本科在讀。
B
A
1006-0049-(2017)10-02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