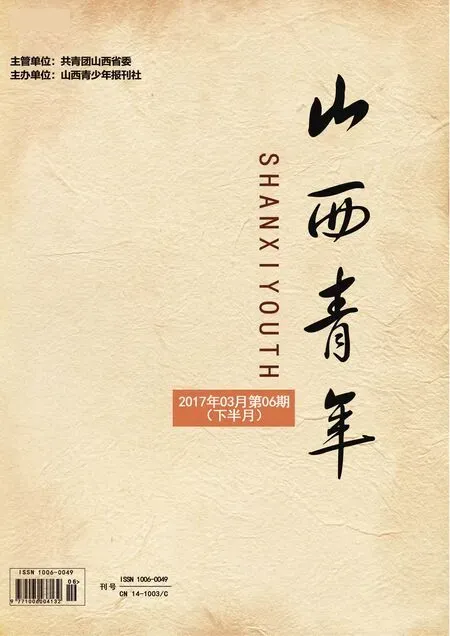儒家文化體系中的性別規訓及其演變
續華杰
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儒家文化體系中的性別規訓及其演變
續華杰*
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儒家思想由春秋時期的孔子創立,他認為春秋諸侯戰亂使得周禮名存實亡,以克己復禮為其目標,其后經秦朝到漢朝漢武帝時期,儒學逐步被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統治階層所認可,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儒家所闡釋的性別制度作為儒家思想體系的一個子系統,其性別規訓對當今社會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儒學所代表的性別制度是蘊含于封建禮教之中的,是以“男女有別”“男尊女卑”“以順為正”為基礎建立起其特有的性別規訓,其扎根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之中,以至于后來演變為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分,至今對中國社會仍有深刻的影響。
儒家文化;性別;演變
一、男女有別
儒家思想首先基于男女有別,這是其倫理道德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禮記》中記載:“男女有別,然后父子親。父子親,然后義生。義生,然后禮作。禮作,然后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可見,在儒家的倫理體系中,男女有別使其倫理綱常的基礎,而人之所以不同于禽獸,也是正因如此。儒家的思想大部分承于周禮,從人類發展歷程來看,當時是原始社會末期,正處于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分工,農業和手工業開始逐漸分離,這一分工更加使得男女基于其生理的性別差異而進行生產方式和生活空間方面的分工,男女有別也正是始于周代。作為儒家倫理體系中的子系統之一,男女有別主要涵蓋了三點內容:性別隔離、性別分工、性別塑造。
性別隔離主要是儒家禮教中強調的“男女大防”,比如“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等。而封建社會基于性別的空間劃分正式根據儒家的這一性別隔離來不斷進行塑造的,并且這種劃分已經根植于中國文化之中,即使在現代社會仍有很大的殘留形跡可循。中國古代的宮室布局、民宅的功能布局,這些空間布局中的每個方位對應著家族身份即是此種觀念的一種反映。進一步延伸到現代,就是傳統觀念中的“男主外,女主內”。隨著現代化的不斷進步,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后出現的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機器代替手工生產模式,使得男女不再局限于固有的生產生活空間,固化的性別隔離模式開始松動并逐漸解放,女權主義和一系列后現代化理論也應運而生。相對于傳統的儒家倫理,女權主義者更多的主張的是女性權利,尤其是尋求兩性權利的平等、促進婦女個性的解放,破除性別隔離的壁壘,一些帶有明顯性別性質的行業、領域的性別特性逐漸模糊化。
馬克思認為,最初的性別分工是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分工,這種分工是基于男女的生理差異的。而在儒家的性別規訓中,其分工原則也是秉承了男外女內的思想。在農耕社會男耕女織式的生產分工方式與男外女內的性別隔離相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男耕女織式的性別分工在周之前就已基本定型,性別分工要早于男女有別這一規訓的提出,性別隔離的男外女內原則也應該是根據性別分工而來的。而在現代社會,隨著女性權利的不斷解放,固化的性別分工模式開始松動并逐漸解放,男女基于生理差異的生產分工差異正在逐漸模糊。
基于性別的生理差異進行的性別分工決定了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而儒家禮教為了讓男女從出生到死亡這一生命歷程中能擔當既定的角色,就決定了男女要基于性別差異來進行不同的教化過程。正如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后天塑造的。”在儒家思想中,基于性別隔離和性別分工所形成的性別塑造,從人一出生就開始賦予了其性別角色期望,以此角色期望來對男女進行分別培養和塑造,從而有促進了性別的分工與男女之間的差別。儒家倫理中,關于性別的規訓主要體現在對于男性的“三綱五常”和對于女性的“三從四德”的論述,而這些東西對象在的中國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尤其是對于女性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影響。
男女有別的初衷是為了確立父子間的血緣關系,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確立父權。生理上的“男女有別”,即女子特有而男子不具備的孕育能力,使得母權是先天的,而父權只能是后天的。人類社會從“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會向“知父”的父系氏族社會轉變是一個很漫長的歷史過程。儒家認為男女無別是禽獸之道,男女有別、性別隔離的真實意圖就是為了推行“一夫制”,確立父權。因此,儒家在確立男女有別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是男子在爭取父權的過程中以一種社會化的“男女有別”的男權來反對生理上的“男女有別”女權。
二、男尊女卑
與男女有別相聯系,男尊女卑是儒家性別倫理的另一根本準則,也是封建社會男性居于統治地位的象征。從觀念上看,男尊女卑源自儒家學說對于周禮的繼承與發展,是依據周朝天人觀年對于男女本性的界定。《周易》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用乾坤來界定男女的本性,乾為上坤為下,這樣,男女就有了高下尊卑之分。這樣對男女的二元性的論述成為了儒家性別倫理的基礎。董仲舒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將男人和女人分別定為陽和陰,陽尊陰卑,從而基本將封建倫理綱常定型。宋明理學在性別關系方面更加趨于固化,逐漸將女性物化,主張男女應有尊卑,夫唱婦隨。這樣使得性別倫理天理化,強調“天理”不可違。
將男尊女卑的準則置于家庭中就形成了儒家的家庭倫理體系。夫妻作為家庭最基本的細胞,家庭中夫妻地位從屬關系的確定,成為了家庭其他成員之間的階序關系的基礎,從而形成了家庭中的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家庭階序,家庭成員之間的階序關系未然夫妻關系而定,不外乎夫尊妻卑、父尊母卑、父尊子卑等等。“男尊女卑”、長幼嫡庶等原則賦予家庭以秩序和等級,賦予每個人的地位就是所謂的名分,基于名分,形成了以父親為中心的輻射型關系,父權制的社會模式從而有了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基礎。
三、以順為正
男尊女卑的家庭階序關系明確了家庭中關于性別的主從關系,物化女性,妻子作為丈夫的附屬要從于夫,而對于“從”,則有相應的規范。儒家關于夫婦的論述中,“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丈夫作為家主,妻子作為附屬,要聽憑丈夫,所以說“事”的本質是“順”,“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如果說關于男女的尊卑是一種本質的規范,那么,這一本質表現在生活領域就是以順為正。儒家主張妻子應當順從,但順要通過教化才能實現。用“三從四德”框定了教化的內容,規訓了女性的角色、行為。
基于這樣以順從為正的儒家思想的教化,封建女性的社會角色以及與其相對應的社會行為規范逐漸定型,而男性對于女性的壓迫成為理所當然,這一觀念深深根植于人們的思想、根植于社會,從而形成了一整套服務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倫理體系。
四、儒學的現代性演變
儒家思想中的性別體系究其根源是按性別進行的勞動分工,而性別分工本身存在等級,男性區于主導地位,女性處于從屬地位。反過來說,如果婦女獲得同男人一樣的社會地位,如果男女的潛能都得到充分的發展,男女的分工等級制應當會消亡,而且,男女分工本身也會消除。封建社會中圍繞儒家思想形成的各個社會系統有很強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性別體系只是存于其中的一個子系統,這一系統下形成男耕女織的男權主導社會中,女性是受壓迫的一方,但是由于教化的根深蒂固,使得女性屈從與這一系統,認為其理所應當。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工業化的發展,封建體系的瓦解直接導致了為其服務的儒家思想也幾近瓦解。生產力的發展,機器以及工廠的出現,使得原有的性別分工體系受到沖擊,農業生產中處于弱勢的女性利用機器進入市場,對于家長制的男權社會發起挑戰。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其相對于代表現代性的機器大生產的工業社會形成一種妥協,這就形成了當前的一種新的性別格局。女性在社會市場中仍然處于弱勢地位,由于男女基于生理的性別差異,女性的生育功能使得女性相對于男性仍需更多的停留于家庭,相反男性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本,因此,造成了女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依靠男性的必要,而男性則從中獲得更多的家庭支持與社會成就。
現代社會雖然瓦解了儒家思想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但是其兩千多年來形成的體系已經融入到了人們的思想,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當今社會,儒家思想中的性別規訓對于女性的壓迫已經不再凸顯,而且女權運動不斷的從被動的狀態轉換為主動,但是,儒家思想中對于性別的區分、性別的塑造仍對社會有著深刻的影響。
[1]王琴.《論語》的時間與規訓[J].中國文化研究,2014.
[2]董金平.女性符碼與女性規訓[J].學術探索,2007.
[3]胡穎峰.規訓權力與規訓社會——福柯權力理論新探[J].浙江社會科學,2013.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M].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5]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續華杰(1991-),男,漢族,山西呂梁人,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性別社會學。
I
A
1006-0049-(2017)06-01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