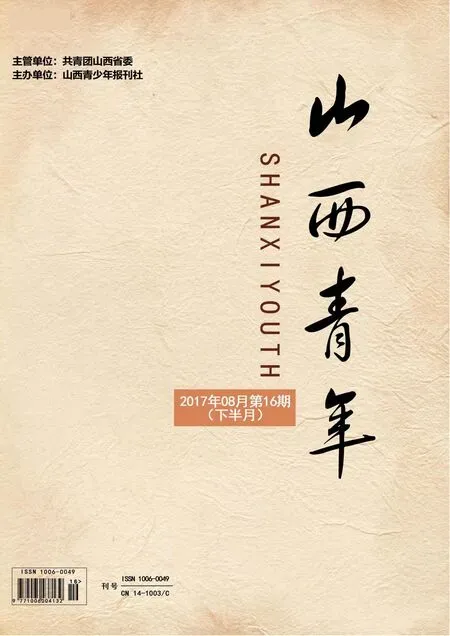簡論父母探視權
張 健
簡論父母探視權
張 健*
揚州大學法學院,江蘇 揚州 225127
2001年我國婚姻法納入探視權制度,填補了立法上的空白,為父母探視權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依據,也保障了未成年子女因父母離婚受到的傷害。但由于立法技術的不完善,實踐中在行使探視權的問題上產生了許多矛盾和爭議,阻礙了探視權案件的順利執行。本文將簡要介紹探視權的概念,闡述我國現行立法中有關探視權規定存在的問題,并且針對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旨在完善我國探視權制度,最大程度上保護子女的權益。
探視權;法律問題;中止;完善
一、父母探視權概述
所謂探視權,是指父母離婚后,子女由其中一方負責監護和照顧,而未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便獲得了對子女進行短期探視(探望性探視)或較長期探視(逗留性探視)的機會。[1]在我國,探視權是在父母離婚后才出現的,是源自于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緣關系與父母子女之間的親權關系也是離異后的各方所享有的一種基本的人身權利。
首先,探視權本質上是親權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種人身權利。[2]這一權利基于親權關系產生,不能轉讓,也無法回避和放棄。探視權與撫養權不同,不屬于財產權利,而是一種人身權利,是為了滿足權利主體精神上的慰藉與需要;其次,探視權在法律上往往比較復雜,其實現阻礙因素也較多,例如與子女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可能不想讓另一方見到子女,也可能會受到被探視未成年人的排斥;三是探視權作為一種特殊的權利,其對應的義務是父母的撫養義務,其履行的目的也是為了保障父母在年老時子女能夠積極主動地履行贍養義務。
二、父母探視權制度存在問題
(一)探視權主體狹窄、探視權內容不夠明確
從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能夠行使探視權的只有父母,且僅為離婚以后未能和子女生活的那一方,這一規定顯然使探視權的主體范圍較小,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首先,“離婚后”的限制使實踐中一部分有探視需求的群體權益得不到保障。比如分居期間的探視權問題、無效婚姻、被撤銷婚姻中的探視權問題以及對非婚生子女的探視權。[3]其次,探視權的主體為父母一方,排除祖父母、外祖父母行使探視權的可能。縱觀他國法律,祖父母、外祖父母同樣應該成為探視權的主體,享有探視權。[4]最后,法律未明確子女的探視權主體地位。子女是探視權行使的核心,子女的身心健康及合法權益維護也是探視權行使的基礎。要保障子女的權益得以真正保障,必須考慮到子女的主體地位,對子女意愿予以充分的尊重。[5]
(二)分居期間探視權規定不充分
在婚姻內的男女雙方感情出現危機,決定離婚之前,夫妻通常會經歷一段分居時間,在經過這一階段后,男女雙方大多會走向離婚。在夫妻分開生活期間,子女基于現實只能跟某一方生活,因而就產生了另一方探視權問題。但是通過筆者對我國目前婚姻法的研究,發現在夫妻分開生活期間,婚姻法對此并沒有具體規定,只規定了離婚后夫妻一方享有探視權,導致實踐中一部分有探視需求的群體權利難以得到滿足和實現,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長。[6]
(三)探視權中止立法規定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婚姻法規定: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應中止探視,除此以外沒有具體的規定。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理解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而實踐中父母雙方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理解和認識也不相同,比如過于頻繁地行使探視權是否屬于探視權中止的事由,雙方認識各異,導致了越來越多的糾紛和矛盾。而“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這一籠統的規定也成為一部分不愿意子女與另一方接觸過多的父或母阻斷探視權行使的借口,不利于探視權的正常行使。
三、完善父母探視權制度的具體立法建議
(一)擴大探視權主體范圍
我國現行婚姻法將探視權的主體限制為父母,這一規定顯然不合理。其一,從老人角度來說,在我國,很多孩子從小就由其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來撫養,僅將父母作為探視權主體就等于剝奪了祖父母、外祖父母探視孫子女的權利,這一做法是不人道的,不符合法制精神;其二,從孩子角度來說,僅僅規定離婚后的父母一方享有探視權,阻斷了孫子女和外孫子女的聯系,情感上找不到寄托,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其三,從社會第三方來說,離婚后,有時夫妻雙方都不愿意去管孩子,而且除了父母孩子沒有其他監護人,此時孩子可以說是得不到任何關愛和保護,這時候父母所在單位、村委會、居委會就可以作為孩子的監護人,將探視權主體擴大至父母所在單位、村委會、居委會將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保護孩子的健康成長,這樣才能使孩子的利益最大化。
(二)規定分居期間探視權
法律給探視權設置了“離婚后”這一前提,即離婚后,未與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才享有探視權,但這一規定卻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分居期間的探視權該如何分配和行使?很多夫妻在離婚之前都會選擇分居,這時候,未與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理應有探視子女的權利。筆者建議將“離婚后”這三個字從現行法律刪除,這樣就可以擴大探視的主體,使其不局限于父母,以填補法律規定之漏洞。
(三)明確探視權中止及恢復的條件
探視權作為父母離異后對子女的法定權利,但權利不應該無限制,應在法律規定的合理范疇,從而避免權利的濫用。為此探視權中止這一規定便應運而生。《婚姻法》38條將探視權中止的法定事由規定為“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這一規定雖然能夠涵蓋實踐中的多種情形,但不夠明確具體的規范可能引發更多的沖突和糾紛。在探視權中止問題的完善路徑中要盡可能實現其條件的明確性、事由的詳盡度,因此應當考慮的問題包括影響子女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因素。筆者認為,筆者認為司法解釋在詳盡規定問題的實現方法上的作用不可忽視,應該注重司法解釋的功能作用,使立法生動并具有較強的操作性。
[1][美]凱特·斯丹德利,著.美國家庭法[M].屈廣清,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280.
[2]孫禮海.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改立法資料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12-414.
[3]馬憶南.婚姻家庭法新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76.
[4]馬憶南.婚姻家庭法新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76.
[5]劉世杰,劉亞林.離婚審判研究[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8:216-217.
[6]車發強.論探視權案件的執行[J].山東社會科學,2012,5:209.
張健(1991-),男,漢族,江蘇淮安人,揚州大學法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學。
D
A
1006-0049-(2017)16-015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