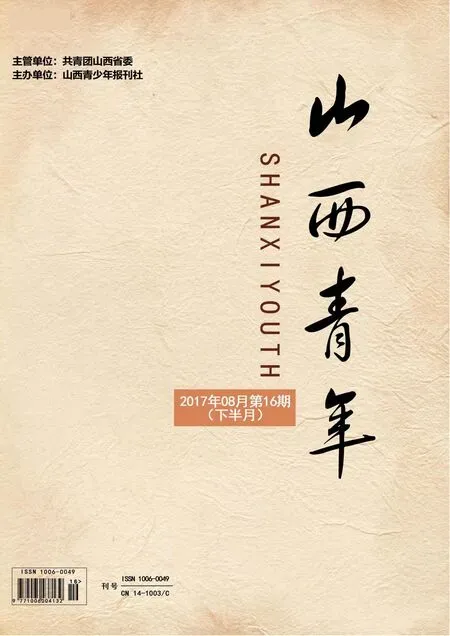淺析蘇聯社會中的勞動異化現象
趙益晨
淺析蘇聯社會中的勞動異化現象
趙益晨*
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蘇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然而歷史的光輝并不能掩蓋事實的真相,作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的蘇維埃政權,在長達70多年的執政中所產生的問題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指出的異化的情況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本文首先對勞動異化理論進行簡要論述,并試圖通過例證來說明蘇聯在7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的異化現象,然后對此做出簡要評價。
勞動異化;蘇聯;馬克思主義
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關異化的概念理解
首先,異化的概念可以根據《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論述來獲得答案。異化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主體創造出的對象反過來成為與主體對立,凌駕于主體之上,支配和奴役主體的對立物,即人所創造的對象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反過來作用于人。
而根據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異化的四個層次分別是: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活動相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即人同自由自覺的活動及其創造的對象世界相異化;人同人相異化。
(一)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
馬克思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一方面,從價值的序列性來看,人的目的性價值被迫下降為物的功能性價值,在序列上目的論為了手段。從歷史的角度審視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人事生產的目的轉變為生產是人的目的,而生產的目的在于財富。而另一方面,即使從功能性價值角度考察,創造物的價值的勞動者本身也是廉價的,即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化。
(二)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活動相異化
對于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于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別人。正因為如此,工人才會感到不自在、空虛,才會把勞動看作是自我的肉體犧牲,飽受折磨摧殘,渴望逃避勞動,僅僅將勞動當作滿足自己外在需要的手段。
(三)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
馬克思強調,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異化勞動就是將作為類本質的人的特性變成支配和奴役人的對立物,使人喪失了它的類本質的屬性,使原本的人成為了一種非人的存在物。
(四)人同人相異化
最后,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產品供其享受的那個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
馬克思借助異化勞動的概念,初步探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揭示私有財產的本質和起源。同時,勞動異化理論為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社會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認識和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社會主義的發展問題上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價值。
二、蘇聯時期經濟社會中的異化現象
1919年12月17日《真理報》發表了托洛茨基《論勞動軍事化》一文。托洛茨基強調:強迫勞動、嚴密組織和軍事化并不僅僅是一種緊急措施,工人國家有權根據自己的選擇強迫公民在任何地方從事任何工作……工人應該向士兵一樣,服從命令……強制勞動的緊張程度將會達到最高峰,逃避勞動的人應被編入懲罰營送到集中營。而布哈林認為,社會的機械化——人們協作勞動、“活機器”的一致性將是推行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2]。而根據可見的歷史資料,布爾什維克黨最初希望以這樣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來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由此便不難發現這一歷史事實的殘酷性,即從馬克思主義那里所提到的異化勞動的概念不僅沒有在即將要實現的蘇維埃俄國中消失,反而變本加厲。工人生產出的產品成為了剝削和壓榨工人一切資源的合理手段,而工人之所以做的目的甚至不是為了獲得低廉的工資,而是為了自己的生命不會在懲罰營或是集中營中以極為悲慘的方式結束而已。勞動活動本身成為了工人唯一存在的理由,工人作為的類本質早已不復存在,他們是蘇維埃俄國軍事化的龐大機器上的一顆微不足道的零件。當然,最后這些工人為之奉獻一切的這個蘇維埃政權的背后,當然是組成布爾什維克黨的每一位領導人。如此殘酷的剝削換來的是這個政權取得了與敵人戰爭的勝利,而問題卻是人民為了保衛蘇維埃政權幾乎犧牲了一切,而最終是否獲得了他們想要的結果呢?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一五計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為打敗德國法西斯創造了物質條件。然而,取得這一系列輝煌矚目的成就的背后卻是以犧牲廣大農民的沉痛代價換來的。為了積極響應工業化的號召,斯大林強行推進農村集體化,并以剪刀差的形式向農民已購買的名義征收糧食。由于忽視經濟規律而強行推行的農村集體化運動使得農村的生產效率不升反降,加之義務交售制的推行,農村怠工現象也逐漸顯現。但是馬上便受到了蘇聯黨和政府的嚴厲打擊。這種政策推行的結果就是,盡管農業總產量不斷減少,但是國家的收購量卻不斷增加。隨之而來的便是當一五計劃結束,蘇聯出現了嚴重的大饑荒。1932年至1933年大饑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付出了近千萬人的代價。這樣殘酷的現實反映出的問題就是,農業成為了工業化的原料產地、傾銷市場和糧食來源,農民成了異化勞動的主體,他們的生命的價值就在于積極響應工業化,而為了工業化,他們可以隨意地從世界消失。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衛蘇聯,可是他們為之獻出的生命的結果卻使得這種異化行為更加肆無忌憚。
如果說斯大林時期的特權階層由于大清洗的出現而難以穩定的話,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擴大化、穩定化得到了正式的確立。這一目的明顯在于收買黨和蘇維埃機關上層,同樣也由于社會資源的嚴重匱乏促使特權行為的出現,特權的內容也是琳瑯滿目。這些特權通過任命制和終身制得以在該階層中保持穩定,進而是這一政權牢固地緊握在一部分人手中。而廣大的蘇聯人民就成了這一小部分人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生產者,而這些生產者也飽受嚴重的剝削:一個普通的蘇聯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僅能買一瓶果醬;同時由于食物供應的效率低下,排隊也成了家常便飯。而千千萬萬的蘇聯工人創造出的甚至一度超越美國的重工業、軍事工業的強大生產能力成為了保衛這一階層的堅固堡壘和其推行大國沙文主義的有力工具。其中,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不言自明,如果說在斯大林時期人們每天以保護生命為目的而小心翼翼地效忠供奉著斯大林的話,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人們不再為了自己的生命而提心吊膽,但是代價就是要通過自己的勞動供養一個更加廣泛且穩定的階層,以換取微薄的收入兌換生存的必需品。
三、對蘇聯經濟發展中異化現象的簡要評價
正如雅科夫列夫所指出的那樣:“幾十年來,生鐵、煤炭、鋼、石油總是優先于飲食、住房、醫院、學校和服務業。類似‘這是必要’的說教,實際是謊言。工業化加上類似封建管理所付出的代價之昂貴是災難性的。人力物力損失及其慘重,對人的漠不關心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3]。”蘇聯的異化從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某一個人的創造,而是當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人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后,現實的殘酷讓他們意識到了穩固這個新生政權的路徑便是通過異化勞動的形式保全自己現有的身份地位,以實現自己的理念和抱負。而當斯大林體制確立之后,異化勞動成為了這個國家不斷發展的動力。其中大量的勞動力甚至是在毫無報酬的情況下為這個國家服務的,他們就是那些被國家(很多情況是隨意地)指控為反革命、右派、富農的這批人,他們被剝奪了一切財富和地位,除了被槍斃的部分人之外,大量的人死于環境極端嚴寒惡劣的勞改營之中,而正是他們為國家“無私”地奉獻著。或許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穩定讓人們感到了一次生機,然而這一問題的實質從未改變,反而更加沉重。如果說蘇聯的解體是很多原因造成的,那么大量的異化勞動極端化的事件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公開化所產生的影響絕對不可忽視。
正如馬克思所講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蘇聯的嚴重問題從這句話里面能夠尋找到合理的答案。蘇聯的解體無疑是20世紀所發生的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而以蘇為鑒,防患于未然,是今天我們應從中汲取的深刻教訓。
[1][德]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2-54.
[2]金雁.“喀瑯施塔得事件”的歷史真相[J].社會科學論壇,2015(02).
[3][俄]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132.
趙益晨(1995-),男,河南鄭州人,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A
A
1006-0049-(2017)16-024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