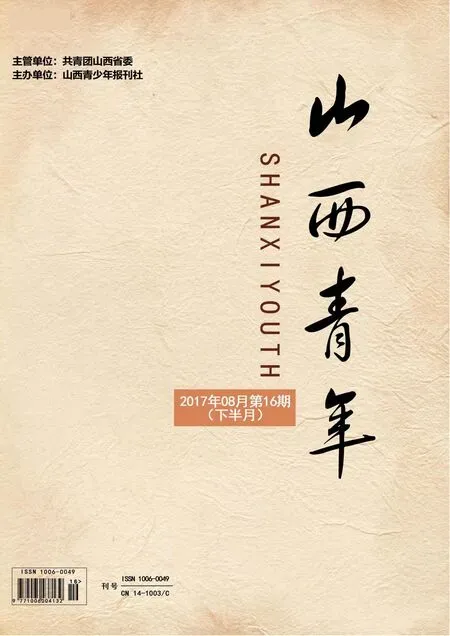民族文化藝術的新思考
劉天妍
民族文化藝術的新思考
劉天妍
新疆藝術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9
血脈之源,割舍不斷的56個民族情,情系相連,共尋民族文化藝術傳承路——我國民族文化藝術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只受自身因素影響,還要經受全球經濟化的沖擊,文化藝術和經濟之間也正處在“尷尬發展”的階段,是繼續堅持“經濟為王”的快速發展?還是尊重民族文化藝術發展的自然規律?在大審美經濟時代下的它又將何去何從?讓我們破除思想上的“誤解”,增強自我文化自信,力創民族文化藝術新品牌!
文化資本;文化自信;審美經濟;品牌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源”,是其長期發展動力的源泉;民族藝術,是民族文化審美的演變,是人們享受生活、創造生活的符號表達,民族文化+藝術的融合,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優秀文化傳承的客觀載體,是文化強國的風向標——轉變民族文化藝術發展的傳統模式,拋開對“藝術經濟化”反感的枷鎖,努力發展民族文化藝術產業化的創新驅動,打造屬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藝術的強國之路!
一、民族文化藝術的文創之路
“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現今社會不單“快”是一種能力,“慢”更是文化藝術方面的“素”與“質”的表達,有“高原”無“高峰”,已經將文藝創作陷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窘境,不是說中國“沒有”文化藝術,而是在這個快節奏的社會中很少有人能夠懂得沉下心去創作,在中華五千年光輝歷史進程中所創造出來的民族文化藝術瑰寶還少嗎?——從1998年的《花木蘭》到2008年的《功夫熊貓》,再到2009年的《阿凡達》,美國“夢工廠”讓我們看到了文化像種子一樣開出了奪目的花,也讓我們為之警醒文化文藝的創作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夢”這一詞的表達,揠苗助長固然結不出成熟的果實,堵住源泉也不能細水長流,所以說,民族文化藝術的發展根本在“人”,更在于人的思想!
優秀的民族文化藝術是一個強國擁有優秀的文化資本最直接的體現;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伊萬·撒列尼運用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概念,研究了波羅的海德語人群的興衰史,以個案例研究的方式說明文化資本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1],雖然海德語人群受政治和國家的制約而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不可否認的是其文化資本帶來的輝煌時期,正如民族文化藝術的發展一樣,它也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就包括國家給予生存環境的影響以及人民群眾接受度的影響,而相較于其他國家政治體制的復雜性,我國的藝術創作環境在正確價值觀的引導下仍是寬容可取的,但在內容創作下卻顯單薄,立法方面仍不完善,文化強國,文化立法,成為接下來的重要任務和挑戰——隨著“兵荒馬亂”的2016年剛過去,2017年迎來了新的改革之年,在此之前所遺留下的問題成為2017年文化發展的突破口與新拐點,民族文化藝術產業也成為各界所關注的重點項目之一,傳承和發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再次被兩會提上議程。據知網統計顯示,2006年有關于民族文化藝術的發文量為340篇,環比增長118%,在2007年熱度持續保持,而后在2014年媒體的發文量僅有130篇,到2015年、2016年也只是小幅度的增長,相對于2006用戶的下載量來看,用戶的關注度與媒體的關注度還是有所關聯的,僅在2006年用戶下載量達到1757篇,環比增長206%,2007年、2008年兩年間也“余熱未消”,但在接下的幾年,民族文化藝術發展與推動卻歷盡坎坷,從2009年的“新疆7.5事件”到2010年“神話人物認親記”再到2011年的“故宮多重門事件”,我國的民族文化藝術在之后的幾年似乎“沉寂”下來,可實際上民族文化藝術的項目開發卻是一直在進行,只是沒有集中化的展示或者說是沒有一個能讓人耳目一新的記憶點,所以說民族文化藝術的“產業化與大眾化”是整個文化鏈中的連接點,只有依靠民族文化藝術的襯托,才能從深層次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精神“消費需求”,也能讓民族文化藝術發揮出它應有的活力!
二、民族文化藝術的自信傳承
娛樂至死,我們不是讓文化變成禁錮我們的監獄,也不是讓文化成為娛樂至死的舞臺[2],我們需要的是“自主、自信、自強、自尊”的民族文化藝術,文化不是誰的附庸,藝術更不是任意載體具體化后的就叫“藝術”,因為民族文化藝術它包含了許多藝術表達形式,如民族戲曲、工藝美術、音樂、舞蹈等都是民族文化在藝術中的體現,可現在社會大眾對民族文化藝術的“模糊”界限顯然變成它發展的阻隔,令原本優質的“體現”也隨著經濟價值的考量,使得文化藝術欣賞的目光變得不再純粹,即便是現在擁有如此強大的民族文化藝術的背景,研究文化的各個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為什么還是不能有足夠的自信去傳承它、去發揚它呢?
法乎其上,則得其中,法乎其中,則得其下。在民族文化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只能處于“講道理給別人說”的狀態,而是要腳踏實地從實際出發,尊重他人的自我創作成果,對成果高標準、高素質,對藝術創作者嚴標準、嚴要求,面對民族、面對文化、面對藝術,都應該不盲目、不狂妄地樹立一個“人無我有,人有我優”自信標桿,因為我們知道,文化發展在于進步,藝術創新在于嘗試,就阿克蘇去年9月舉行的以西域文化、本土文化為主題的民族文化藝術的大型燈會來說,大膽利用當地民族文化藝術結合現代科技去創作,它不是純粹的“拿來”,而是集合眾多人思想的結晶,這對于民族文化藝術的長期發展來說,思想的“行動力”才是源源不斷的發展源泉!
無文化,無自信;無自信,無精品。文化自信源于自身的強大與外界的支持贊美,如果沒有自我的肯定和他人的理解,文化的再創也不能達到“浚其泉”的真諦,而只有抓住根植于民族血肉上的藝術之花,才能與人民產生共鳴,才能多方助推、乘風破浪,所以在踏上文化強國的征途上,我們不能過于強調中庸的論調,而是要將文化的關建在于“發揚”落到實處,畢竟現在的中國在國際的地位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一舉一動都受到世界的矚目,國家的強盛讓人民自信,人民自信促進文化的發揚,那民族文化藝術的發揚是否能讓我國走上文化大國之路呢?我認為這答案是肯定的:即便是我們不能確切的預測未來的走向,但是卻能肯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種藝術理念永遠不會被時代淘汰,就像新中國66周年華誕之時,66個中國本土品牌齊齊亮相紐約時代廣場為祖國慶生,就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向全世界人民展現我們的“中國紅”、訴說著我們的“中國夢”、傳遞著我們民族文化藝術前進的火與熱,讓我國民族文化藝術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拋開民族文化藝術只是各個民族的民間文化、民俗文化這“狹義的觀念”,接納各民族文化產品的衍生文化藝術,再凝聚我們淵源長河中優秀的中國因子,好好做出更多的民族文化藝術精品,造就吾國與吾民強大的文化自信,才能樹立光輝的國家形象,打造屬于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藝術品牌!
三、民族文化藝術的“美利”綻放
眾所周知,藝術源于生活,生活的藝術和藝術的生活分別成為人們在精神和物質上的追求,可以說前者是從思想上的創新,是用思想的“行動力”去創造生活的美學,而后者更偏向于物質美化后繼而間接帶來的精神享受,“美”成為當代社會藝術價值的標準,它不僅體現在視覺上的沖擊美,更體現在百說不厭的文化的內涵美,而民族文化藝術就是國家淵遠流傳的至美!
2001年,德國學者格爾諾特·伯梅在《審美經濟批判》中提出了“審美經濟”的概念[3]。《印象·劉三姐》、《云南映象》、《千手觀音》等大型優秀演出項目也成為中國審美經濟下時代需求的文化產物,民族文化和藝術完美的融合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好前景,這些與“平常”的演出作品相比,“更上一層樓”的作品贏得的贊譽更加印證了民族文化藝術的開發離不開經濟的改造和支持。一方面,有些學者認為“藝術經濟化”是對藝術的玷污,讓審美在享受的過程中變得有些功利化,而這樣的轉變是會給文化和藝術的發揚形成阻礙;另一方面,事物的發展都有兩面性,我們應該承認過快的經濟發展勢必會帶來一些弊病,可是我們卻不能只以悲觀的態度去看待藝術,因為存在權威性的“悲觀”更會讓人惶恐而不知“發展”在何處,而民族文化藝術的發展中缺少的就是這樣權威性的自信與支持——每當有創作者將傳統的劇作音樂與流行元素結合,就會讓不少網友大呼“不倫不類”,不管最后的結果是否成功,最先開始仍是“質疑”,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它是傳統而“被傳統化”,就算民族文化藝術作品的質量是最應該先考慮一方面,但更值得一提的還是它思想上傳遞給觀者以文化自信的問題,因為所有的傳統文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本身在傳承過程中就是剝離糟粕吸收精華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并不是盲目地去附和經濟的發展,而是要擺正“創新給予鼓勵,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只要不低俗、不媚俗、不盲目的“篡改”民族文化藝術,這些大膽的創新仍是有可取之處的。總之,無論“藝術經濟化”還是“經濟藝術化”都要持以開放包容的眼光去看待,畢竟一只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才是春!
四、民族文化藝術發展的挑戰與機遇
人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自然主體,在創造文化改造文化的過程中都是以“需求”為中心。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最高級”的自我實現需要在如今看來更像是變相“低級”的生理需要,因為人們剛從經濟物質需求的鐵軌上下來,迎接的是文化藝術在精神上的需求,而如何尋找文化藝術在精神上的需求成為經濟開發者創造價值的關鍵——旅游開發成為帶動民族文化藝術發展的動力之一,如何讓游客選擇這個“首選之地”,品牌的創立就顯得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各個地區民族文化藝術的“包裝”,除了豐富的內涵以外還要樹立一個“標志性”的思維:“我沒去看它或購買它就是白來”,而這樣標志性的文化藝術及其衍生品,在為當地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是不是也間接地將當地的民族文化藝術傳播出去了呢?雖然從表象看來民族文化藝術的傳承和發揚只是依靠旅游的“引進來”,但是成功的“走出去”卻是“引進來”的奠基石,兩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它真正的魅力,畢竟體制式、標準化的傳承和保護已經不足以滿足“民族文化藝術”的需求,它現在需要的是活性的“人人傳承”、流動性的“處處發揚”,而“人人”、“處處”雖不能概之以全貌,但是也能在民族文化藝術走上品牌化的發展道路上注上一劑強心劑。
目前,民族文化藝術發揚的重任仍放在各類的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肩上,可據CFC基金會中心網數據統計,雖到2015年自愿加入基金會中心網的基金會數量達到5620所,但其中以模糊搜索“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11所,平均透明指數FIT約為66.62,精確搜索“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2所,精確搜索“民族藝術”基金會1所,精確搜索“民族文化”基金會8所,并包含了精確搜索“民族文化藝術”中的兩所基金會,并且8所“民族文化”基金會平均透明指數約為48.65,兩所“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平均透明指數約為55.6,這些數據都反映了幾個重要的問題:一,我國明確發展民族文化藝術的基金會基數過少;二,這類基金會劃分的界限在哪兒;三,各個基金會的透明指數還不夠高。這幾個大問題是推動民族文化藝術發展的關鍵之處,只有抓住它傳承發展根源處的弊病,才能立足腳跟,切實地落實到根本,畢竟各大基金會的存在除了推動民族文化藝術的發揚之外也要考慮它的保護與傳承問題,而保護也應該偏向于“保存”這一塊兒,在努力發展基金會項目管理與運作的同時還要注重優秀民族文化藝術“留影”工作,保證在今后的傳承在創新之余也能不改變其本質。“留影”工作既是對過去的優秀“致敬”,也是向未來的創新“警醒”,并且文化藝術的發展都是離不開人民的生活,一切脫離群眾的文化藝術都不能被稱為真正的文化藝術,由于高科技時代的來臨,為我們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合理利用高科技手段去傳承民族文化藝術也稱得上可取之選,數字化博物館、數字化智庫、藝術網絡等項目都可以逐步實施計劃,而我們也意識到只有建立一個完整的信息共享中心,才能有的放矢,為民族文化藝術指明明晰化的創新道路!
[1]薛曉源,曹榮湘.全球化與文化資本[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
[2]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廣西大學出版社,2008.5.
[3]李思屈.審美經濟與文化創意的本質特征[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8.
G
A
1006-0049-(2017)16-00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