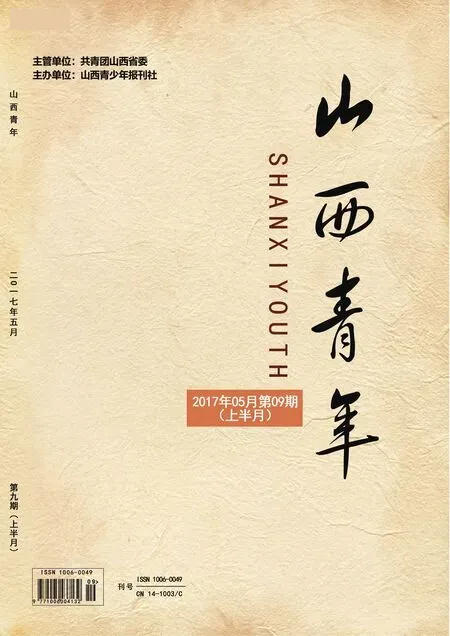芻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
杞月詩
南昌大學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88
?
芻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
杞月詩*
南昌大學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88
作為國際條約出現前知識產權的顯著特點之一,地域性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然而正是由于這一特性,國際條約關于知識產權規定的大量增長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議,不少論者據此現象推斷知識產權已經突破了其嚴格的地域性特點,甚至提出了“超地域性”的觀點。本文將對于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所謂的“超地域性”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知識產權;地域性;超地域性;國際保護
一、知識產權地域性的概述
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征指在某國領域內依法產生的知識產權獨立受該國的法律承認及保護,而在其他國家范圍處于無效狀態。如若沒有國際條約或協定的特殊規定,則知識產權僅具域內效力。
(一)知識產權地域性產生的原因
知識產權的客體即知識產品,它是各國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與其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息息相關。各國立法保護知識產權旨在維護其所有者財產利益的同時,發展本國的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
首先,知識產品的非物質特征使得它能在多個國家被多個主體同時創造并利用。因而依國家主權原則,對位于本國范圍內的知識產品的創造、使用和處分,各國可以獨立行使屬地立法管轄權。換言之,同一知識產品上能夠依法存在多個平行時間空間的知識產權。
其次,獲得知識產權的基本條件有二:憑借主體智力創造性活動的事實行為①并通過國家相應主管機關依法確認或授予。作為無形財產,知識產權所有人無法僅依據其創造性活動當然地、充分有效地享有權益,其前提是依據國家法律的直接規定或由相關行政主管機關依法確認或授予知識產權。因此,法律往往需要做事前引導,通過界定知識產權的創造、收益、處分的相關法律關系來明確權利人在特定范圍內行使權利并承擔義務。故而各國為規范同一知識產品相關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會獨立行使其屬地立法管轄權。
(二)知識產權地域性的嬗變
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催化了該領域內國際條約的誕生,而這,形成了區別于傳統物權的一大特色——國際保護。
19世紀隨著西方各國工業革命的相繼完成,生產力與科技空前發展,西方普遍建立了工業產權制度。然而由于各國對其工業產權行使屬地立法管轄權,使得工業產權僅具有域內效力,這極大地阻礙了國際間的信息交流與技術合作。一時間各國紛紛呼吁對知識產權實行國際保護,于是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條約和國家間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便應運而生了。自首個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公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到彰顯著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進入新階段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出臺的這一百多年里,關于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群迅速成長成型,其為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帶來的意義非凡:各成員國對他國國民知識產權的申請不再單獨設立門檻,而是給予彼此以國民待遇。確立國際條約統一協定的最低限度保護原則,使得各國知識產權法與國際保護的標準相統一②,這不僅打開了知識產權所有者國際范圍內權利保護的大門,亦促進了國際間的知識產權的交流與發展。
二、對于知識產權“超地域性”的認識
作為國際條約出現前知識產權的顯著特點之一,地域性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然而正是由于這一特性,使知識產權具有了迥異于有形財產的國際保護制度,不少論者據此現象推斷知識產權已經突破了其嚴格的地域性特點,甚至提出了“超地域性”的觀點。
在筆者看來,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并不意味著已經產生了某種超越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如跨國專利或者世界專利,要求相關國家予以一體保護。這是因為,知識產權是由主權國家的法律予以規定和保護的條件下,世界專利、世界商標或者世界版權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世界各國同意讓出一些主權,才有可能產生所謂的世界專利、世界商標或者世界版權。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能否產生世界統一的確定侵權與否、權利有效與否的法院體系,仍然是一件值得懷疑的事情。
在這方面,歐洲聯盟的情況比較特殊。近年來,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出現了“共同體商標”和“共同體外觀設計”。從表面上,這似乎是跨越國家的注冊商標和外觀設計。但在事實上,這是歐盟成員國讓出了一些主權給予歐洲共同體,使之通過共同體商標條例和共同體外觀設計條例,注冊了在歐共體范圍內一體有效的商標和外觀設計。而且,即使在這樣的注冊商標或者外觀設計,在發生侵權時,仍然是由各個成員國的法院按照各自的訴訟制度,進行一審或者二審。歐盟的一審法院和上訴法院,主要是澄清相關的法律問題,而非進行侵權與否或者權利有效與否的審判。所以,理解這類注冊商標和外觀設計,仍然不能離開主權國家的概念。況且,假如真的有一天,歐洲聯盟成立一個主權國家,有關的共同體商標或者共同體外觀設計,仍然是依據這個主權國家的法律而產生,并在這個主權國家之內獲得保護的知識產權。③
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也不同于知識產權的涉外保護。后者是指某一個國家,依據自己的知識產權法律,對他國國民或者法人的智力活動成果予以保護。顯然,對于外國國民或法人的知識產權或者智力活動成果予以保護,是依據本國的法律而非國際條約。即使是在那些規定國際條約自然產生法律效力的國家,也需通過國內法的確認,從而自動成為國內法的一個部分。如果法院在個別判決中不得已而引證了國際條約的相關部分,也是從國內法的意義上引證的。當然,從國際條約的角度上來說,一個國家對外國人提供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必然是已經達到了相關國際條約的基本原則和最低要求。而這些又正是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宗旨和目的所在。
綜上所述,所謂的“超地域性”是一種誤解與偏頗,是并不存在的,地域性這一特點使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別具一格。對這一特點的嬗變研究,將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大有裨益,從而更為廣泛且有效地開展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
[ 注 釋 ]
①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449.
②鄭成思.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人民出版社,1995:244.
③李明德.知識產權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第15頁.
[1]潘皞宇.論知識產權國際化的保護模式及我國的應對策略[J].法學評論,2015(01).
[2]李明德.知識產權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3]鄭勇.知識產權地域性之現代嬗變[J].商業時代,2013(15).
杞月詩(1996-),女,漢族,湖北十堰人,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在讀。
D
A
1006-0049-(2017)09-02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