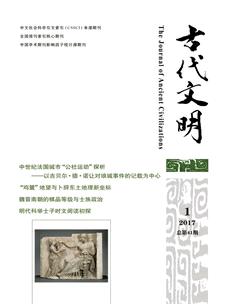“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范金民
提 要: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重視商品流通,從自然資源、社會生產與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闡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業的重要性,提出農虞工商并重論;從人心人情的本性出發,從商業與財富的功用出發,高度評價商人的正當經營和經商致富行為;從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業倫理與商業思想。司馬遷的商業商人觀殊少被官方采行,但《貨殖列傳》中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為經商鼻祖,其闡發的很多商業、致富、民生思想,多為后世所肯定。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商業思想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08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是正史第一次為商人立傳的名篇,充滿中國早期的商業智慧和商業倫理,全面地闡發和反映出了作者對于商業、商人及財富的觀念,并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描摹,也被后人反復引述。這些商業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深入總結,珍視理解。
一
司馬遷眼光獨到,為王侯將相立傳的同時,為先秦以至漢代中期的歷代大商巨賈立傳,樹立了傳頌千古的商業鼻祖,賦予商人應有的歷史地位,也為后世留下了較為集中的商人經營活動資料。
司馬遷先為先秦時期的列國大商人8人立傳,繼而為漢興以來的富商立傳。兩部分都是先概述各地區的經濟特產狀況和風土人情,然后列敘人物。
計然。相傳是葵丑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有說是范蠡之師,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也有說范蠡所著之書名《計然》,恐非。所謂計然之策,其宗旨是“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意為知時所用之物。若此,則萬貨之情而得而觀之。第一要懂得天時變化,其規律是可以掌握的,農業產量呈現出短期波動、長期循環的特點,如能預測豐歉水旱,就能預測商品供求變化的長期趨勢;第二要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判斷價格的漲落,“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及時買進和拋出,經營就能獲利成功;第三,國家要用調節供求的經濟辦法來控制物價,使之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之內,以對產銷雙方有利,防止谷賤傷農和影響商人的經營利潤;第四,經營者要十分注意商品的質量,貯藏貨物“務完物”;第五,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1司馬遷認為吳國能成為春秋五霸之一,觀兵中國,正是用了計然之策。
范蠡。居陶,擇人而逐時,治產居積,從而“三致千金”,經營屢屢成功。
子貢。端木賜,廢著鬻財,經商致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并以雄厚的財力使孔子之名布揚天下。司馬遷認為能使孔子之名布揚于天下者,正是子貢之力,此所謂得藝而益彰者乎!子貢恐怕是歷史上第一個將從商與為官成功結合的典型。
白圭。魏文侯時人。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用計然之術經營得法。其人“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其經營策略謂:“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1于此,司馬遷大力崇揚商人應該具備的智勇魄力和機變能力。
倚頓。用鹽起家。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數世,秦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其筑女懷清臺。2司馬遷以烏氏倮和巴寡婦清為例,能“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司馬遷為之立傳的前四位大商人,均以獨特的經營方法長袖善舞,活躍在商業流通領域;后四位商人,則均以特殊行業獨擅其利。孔子批評子貢的貨殖活動,說他“不受命”,司馬遷則說,子貢“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3不但肯定贊揚子貢的經營活動,而且看到了子貢經營成功后對孔子游說列國所起的作用。司馬遷表彰先秦時期計然、白圭、范蠡、子貢等大商人,很值得深深體味。梁啟超認為西方有富國之學,中國自古言學派者,未有及此,太史公立傳贊頌其言行,知先秦以前實有此學,“若以治今日之中國,拯目前之涂炭,則白圭計然,真救時之良哉”。4太史公記這些大商人,如越國用計然之術而躋身五霸,將白圭之術比作伊尹呂尚之謀、孫吳兵法、商鞅行法,子貢聘享諸侯與列國君主分庭抗禮,其主張,其實效,其地位影響,實毫不遜色于同時期任何學派。
司馬遷為當世賢人且至富厚以經營之術起家的商人立傳,作為“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典型,共有12人。
蜀卓氏。被秦國遷徙,抵達臨邛之地,鐵山鼓鑄,運售各地,富厚擬于人君。
程鄭。山東被徙之人,也在臨邛從事鼓鑄,販售各地,富埒卓氏。
宛孔氏。梁人,被秦遷到南陽,發揚舊業,大力鼓鑄,治陂池,終至連車騎,游諸侯,因商賈之利而有名于游閑公子間。又因此而獲得厚利,遠超一般經營之人,故南陽行賈紛紛效法孔氏。
魯人曹邴氏。也以鐵冶起家,富至巨萬。而且父兄子孫數代人,俯仰取予,“貰貸行賈遍郡國”。至此,司馬遷論商業的影響:“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5
齊地刀間。收容奴虜,使之追逐漁鹽商賈之利,大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6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師史。利用洛陽居在齊秦楚國之中的有利地理,從事經營,“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7故師史至富至七千萬。
關內宣曲任氏。當秦敗時,豪杰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藏倉粟。當地缺糧,豪杰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尚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大力田畜。田畜人爭取甲價,而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任公仍家約,非串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表率,故富而主人器重之。
邊塞負責斥候之卒橋姚,馬牛羊粟無數。吳楚七國兵起時,用錢孔急,子錢家以為侯之邑國在關東,勝負成敗未決,不肯出貸,只有無鹽氏出了千金貸,其息十倍。吳楚平,無鹽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諸田,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等,也巨萬(此3人只有姓而無事跡)。
司馬遷用這些事例說明成功的經營之術。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1
司馬遷最后列舉“誠壹之所致”的9種行業9人:從事田業的秦,掘(拙)業的田叔,博戲的桓發,行賈的雍人樂成,販脂的雍人伯,賣漿的張氏,灑削業的郅氏,胃脯的濁氏,馬醫的張里。2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傳的商人,誠如李埏先生所說,是有選擇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其標準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3在《貨殖列傳》敘述漢代當世的大商人后,司馬遷又說,“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述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4“很顯然,司馬遷為之立傳的商人必須是一不害于政,二不妨百姓,三能取予以時從而獲息增加財富之人。這些人,是布衣匹夫之人,而不是貴族、官僚以及武斷鄉曲之人;是通過經營獲致富厚的人,而不是憑藉身份作奸犯科以超經濟手段獲得權勢的人;是與時俯仰大獲成功中之少數卓犖異常之人,而非經營成功的普通富豪。5司馬遷的這種思想,被人評為“前所未見的新思想、新觀點”。6史馬遷為這樣的商人立傳,充分反映出了他的商人觀和商業倫理觀。
二
司馬遷重視商品流通,從自然資源、社會生產與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闡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業的重要性,提出農虞工商并重論。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首先比較《老子》的社會理想與三代以來的社會實際情形,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社會治理和發展思想。7即是對于人心均有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藝能之榮的心理,高明的統治者是順應利用之,其次是引導之,再次是教誨之,更次是調節之,最下則是與民爭利,或者限制抑制之。
緊接著,司馬遷敘述全國的自然資源和地利情形,指出各地的自然之利,“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8這種自然之利的開發利用,并不需要統治者政教發征聚斂,而只要人們各盡其能,各竭其力,即能實現。所以物賤時求貴,貴時求賤物,各勸其業,各樂其事,猶如水之趨下,一刻不停,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樂趨,這正符合自然之道,正是自然之驗。司馬遷將人們依據自然資源和地利情形各竭其力的行為,由市場通過價格自發調節達到一個較為均衡狀態的情形歸結為“自然之驗”。
接下來,司馬遷開宗明義,先引用《周書》所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稱此四者是“民所衣食之原”,9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此貧富之道,不能予取予奪。此四者,巧者,利用得好,則富饒有余;拙者,不善利用,則貧乏不足。司馬遷而后援引齊國致強稱霸的例子,先述太公望所封的營丘,鹽鹵之地,人民鮮少,太公勤其女紅,盡其技巧,販賣魚鹽,以致人們輻湊而至,成為冠帶衣履天下、吸引人前往趨利的重地。后來齊國中衰,管子采用調節錢幣之法,富國強兵,終至桓公稱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由齊國的事例,司馬遷引用《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名言,強調“禮生于有而廢于無”,君子富則好行其德,小人富則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山深而獸往,人富而仁義附。總之,富者得藝益彰,失藝則客無所之,因而不樂,更加窮困。于此,司馬遷總結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1即使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且患貧,何況匹夫編戶之民呢!
如此,層層遞進和展開,縝密地闡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業的重要性,農虞工商各其有重要地位,缺一不可。司馬遷以前的思想家論述“富”和“利”,多是從一般原則或國家的觀點提出問題,“沒有從個人以及農虞工商各業如何經營致富的問題進行考察”,“在這個問題,司馬遷可以說是第一人”。2
三
司馬遷重農重商,通過介紹歷代大商巨賈的經營過程與特點,高度評價商人的正當經營和經商致富行為。
司馬遷以是否富厚來看待平民百姓之治生。各地利用自然之利,業農藝業致富之人,“皆與千戶侯等”。這樣的人,不窺市井,不行異色,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相反,如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而應感到慚恥。從事治生,不待危身取給,應該是賢人所勉勵之事。所以司馬遷總結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馬遷本富、末富、奸富之論,并不是否定末富和奸富,而是認為能求本富最好,其次是末富,奸富也不排除。其中心意思是:“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3司馬遷發展《尚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的觀念,認為因貧不能養贍父母不但不孝,而且足堪羞恥。
司馬遷總結“誠壹之所致”的功用,《史記·貨殖列傳》載: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4
在這里,司馬遷對各種行業,并不作道德評判,而惟以是否達到求富目的為評判標準。
四
司馬遷思想敏銳,從人心人情的本性出發,從商業與財富的功用出發,充分肯定富商巨賈的正當社會功用與積極影響。
司馬遷敘述各地自然地利與風土人情之關系。關中;巴蜀;三河;西北;邯鄲;燕地;洛陽;齊地;鄒魯;江淮;楚;越;南楚;嶺南。于此,司馬遷闡明,統治者應該了解民情風俗,善用地利,選擇或聽任百姓是業農還是經商,選擇謀生之方。清楚地闡明了自然地利與民情風俗、生產生活方式及經營行業的關系。
司馬遷從荀子的人性論出發,5但側重點有所不同,認為農虞工商各個社會階層的普遍“求富益貨”活動,是來源于人類的基本欲求和較高欲求,是人之情性所致,“不學而俱欲者也”。6司馬遷展示了社會各業求利求富的一幅寬廣的圖畫,舉凡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于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均是為了求得富厚,廉吏、廉賈之行,也是為了取利獲致富貴。社會各界如壯士攻城,斬將搴旗,不避湯火之難,是為了重賞;里巷少年,任狹兼并,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為了財用;趙女鄭姬,梳妝打扮,目挑心招,不擇老少,為了奔富厚;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為了富貴;犯晨夜,冒霜雪,不避艱險,為了得味;斗雞走狗,必爭勝,為了不失重負。他如醫方技術之人,為了收入,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鋸之刑,是貪賄賂;農工商賈畜長,本來就是求富益貨者也。社會各界為求富求貴,必不遺余力。整個社會就如諺語所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1
司馬遷贊揚商業與農工等他業一起,“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2并肯定孔子周游列國得以成行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弟子子貢將經營所得予以資助的結果。
所以班固在《漢書》中批評他“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3班固的說法,其實只說出了司馬遷描述商人行為的表面現象,司馬遷實際上是要闡明:士農工商以至社會百業,并無高下尊卑之分,均不可或缺;各業應該充分利用自然地利客觀條件,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使社會經濟的各個環節流通運作起來,謀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商業居于經濟流通的末端,收效最為明顯最為迅速;無論何業,只要堅持,持之以恒,必能收“誠壹”之功效,若是因循消極,懶惰無所作為,不思進取,而終歲貧乏窮困,仍侈談仁義,那就極為可恥。因此,司馬遷其實是在總結求富之路謀生之方,而并不輕視賤業,羞恥貧困,并不“崇勢利而羞賤貧”。
五
司馬遷高屋建瓴,從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業倫理與商業思想。在士農工商“四民”的社會功用上,司馬遷引用《周書》所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稱此四者是“民之衣食之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此貧富之道,不能予取予奪。《管子》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業,也是四等,而且等序不能變動,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4但司馬遷所主張的四業,既無本末之分,也無尊卑高下之別,均有其相應地位,均應充分發揮其作用,而且可以變動,任時擇業。較之《管子》,無疑更進一步。
在財富與道德行為的關系方面,司馬遷強調《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提出: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藝而益彰,失藝則無節操而言。
在人的求富動機方面,司馬遷認為,整個社會如諺語所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求富是人之情性,不學而俱欲者也。社會各界雖然從業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表現形式不同,但為了求富求貴,必定不遺余力,宗旨則一。司馬遷認為,即使在等級社會中,人們謀求富裕的機會卻是均等的。
在對待財富的人生態度方面,應該盡其所能,去追求富厚,如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而應感到慚恥;“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因此,無論何業,均應虔誠一心,孜孜追求,以實現“誠壹之所致”。5
在追求財富的成效方面,提出各業致富的回報率。司馬遷認為,農虞工商四業,皆是本業,“衣食之原”,缺一不可,但“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要擺脫貧困謀取財富的成效和速度,營商是為突出的。司馬遷強調,即如諺語所稱,“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一般人視為末業的商業,恰恰是貧者之所資,更是謀生求富最有效率的行業。這是因為,從事商業貿易,貨款回籠快,資本能迅速賺回本利,周期越短,次數越多,國內貿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賺回一次,甚至三四次”,1而農業就不可能。斯密甚至說,“我們常常看見一種白手成家的人,他們以小小的資本,甚至沒有資本,只要經營數十年制造業或商業,便成為一個富翁。然而一世紀來,用少量資本經營農業而發財的事例,在歐洲簡直沒有一個。”2斯密關于商業致富的奧秘,早在近兩千年前,就由司馬遷揭示了出來。
在對待商業和商人的態度方面,司馬遷主張“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對農虞工商各行各業最上之策是任其自然發展,其次之法是因勢利導,因民之利而利之,再次之策是教誨限制,最下之策是與民爭利、壟斷專利。司馬遷反對漢武帝時采用鹽鐵官營等專賣壟斷政策和征收重稅的商業政策,更反對實行抑制削弱以至打擊懲罰商人的算緡弊政。司馬遷甚至說因勢利導之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驗”,3言下之意,若有違拗,恐會付出代價。
在經營方法和經營理念方面,推崇人棄我取人取我予之法,推崇“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說“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4也即強調發揮貨幣的流通作用,加速資金周轉。巫寶三先生認為,“如果以司馬遷的貨殖學說與亞里士多德的貨殖學說相比較,他們在無限度的增殖貨幣財富的論點上,可以說是一致的,但司馬遷論述財富的增殖,不像亞里士多德限于貨幣,還包括生活用品等實物,也不像亞里士德那樣仍然沒有擺脫倫理規范的束縛”。5
因此,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述贊》中論《史記》:“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筑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6
近代思想大家梁啟超先生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深有感觸地說:“《史記·貨殖傳》私謂與西士所論(指“富國學”——引者)有若合符。茍昌明其義而申理其業,中國商務可以起衰。前哲精義,千年湮沒,致可悼也。”7當代經濟史家學巫寶三認為,司馬遷提出的求富是人之情性,農畜工虞等均屬財富范疇,農虞工商同樣重要,發揮人的積極性就能積累財富等原則和學說,“應該說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最具有創新性的”,“關于重工商的思想,不獨先秦諸子沒有一個可以與之相比,即使西漢思想家也是如此”。8因此,司馬遷的商業商人思想,不僅較之前人和時人迥出其上,9而且較之后人,也顯示出卓異之處。
司馬遷以后,只有東漢的著名史家班固,在其撰作的《漢書》中,同司馬遷一樣,也為商人立有專傳《貨殖列傳》,10但班固對商人的評價卻十分低下,對商業的認識則大大落后于司馬遷。《史記》為歷代商人立傳,是要頌揚商人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肯定其正面的地位。班固《漢書》的《貨殖列傳》,入傳商人絕類《史記》,甚至襲用《史記》原文,但立意完全不同,而是要“列其行事,以傳世變”,11從中悟出商人對社會秩序的破壞與消極作用。《漢書》在司馬遷傳中,批評太史公“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12因此,班固在《貨殖列傳》中,總論以《管子》士農工商四民序列為切入點,先說周室衰弱之時代,“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余”;既說到了齊桓、晉文公之后,《漢書·貨殖列傳》載: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1
全社會重商、商人活躍的結果,是禮樂大壞,上下失序,國家異政,家庭殊俗,以下犯上,僭越無等;是難得奢僭之貨得以流通,奇技無用之物得以生產,官吏治政者反道而行,全社會貧富不均,的飾變機詐者衣錦食肉,守道循良者啼饑號寒。司馬遷在總結各種致富的正道與奇勝之術后,認為“皆誠壹之所致”,而班固擷取《史記》中的同樣事例,敘述歷代大商人的致富過程,最后卻得出“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的結論。2
司馬遷在史書中為商人立傳,是要高度評價商人,使人充分認識到商人的價值。班固為商人立傳,班固《漢書》的《貨殖列傳》,入傳商人絕類《史記》,甚至襲用《史記》原文,但立意完全不同,而是要“列其行事,以傳世變”,從中悟出商人對社會秩序的破壞與消極作用,使人意識到商人顛覆社會的破壞作用,兩者異若參商。班固對西漢中后期豪商巨賈乘堅策肥、交通王侯的強大勢力有著深切體會,只看到了商人勢力的強大對社會等級秩序帶來的沖擊,導致的貧富兼并兩極分化,但他無視商業和商人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從而完全否定商人的社會價值,較之司馬遷,在社會人文觀上,倒退了一大步。以后歷代官修史書,更不為商人立傳,較之司馬遷,觀念似倒退了不少。
巫寶三先生說:“在這種社會政治條件下,司馬遷能突破傳統教條,重視工商業的作用,認識增殖財富的必要,提出‘法自然的社會經濟發展原則,不能不說他不但在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上享有卓越的地位,并且在世界經濟思想發展史上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3
六、余論
商人和商業,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必不可缺的一環,有著極大的進步作用和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但往往和其他階層的利益發生矛盾沖突,確有影響其他經濟、腐蝕社會機體的消極、頹廢作用。斯密說:“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制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于欺騙公眾,甚至在于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4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引用托·約·登寧(Thomas Joseph Dunning)在《工聯和罷工》中所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5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又引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27年出版的《論商業與高利貸》中說:“但既然商人對全世界,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干下了這樣多的不義行為和非基督教的盜竊搶劫行為,那末,上帝讓這樣多的不義之財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搶走,甚至使他們自己遭到殺害,或者被綁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國君應當對這種不義的交易給予應有的嚴懲,并保護他們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無恥的掠奪。”馬克思在引用這段話后指出:“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后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這樣。”1
十分不幸的是,后世主政者大多承接班固的商業觀,只看到商人商業消極的一面,二千年中以農為本業,而以商為末業,重農抑末,賤商限商,輕視商業的作用,甚至盡量限制商人的社會身份與地位,直接剝奪肆意摧殘商人的利益,或者從社會道德價值判斷出發,而忽視甚至無視商業價值,忽視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如號稱“決斷精敏”的開封府推官蘇軾,當熙寧初王安石創行新法時,上奏稱:“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2這種看法,時至清初,還被大思想家顧炎武視為“根本之言”。3
司馬遷的商業商人觀殊少見到被官方采行,但其在《貨殖列傳》中立傳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為經商鼻祖,頂禮膜拜;其闡發的很多商業、致富、民生思想,多為后世所肯定。如“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推崇水旱豐歉掌握貴賤待時而動的計然之策,長袖善舞的子貢,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白圭之術等,為歷代商人所崇奉,所運用。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誦之人口。“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思想觀念,為人所熟知。“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真諦,成為歷代商人的強大動力。“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末業為貧者所資,似成為人們的共識,在歷代知識人士的論述中隨處可見。司馬遷提出的財富觀,也影響著歷代士人。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就認為,“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4清初思想家唐甄,就面對“自污于賈市”的譏誚,氣憤地說:“今者賈客滿堂,酒脯在廚,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匱。此救死之術也,子不我賀,而乃以謂誚我乎?”唐甄又因從事牙人之業而遭“恥業”、“近于利”的質問,理直氣壯地說:“呂尚賣飯于孟津,唐甄為牙于吳市,其義一也。”5
司馬遷用詞典雅,描摹人事,精準確切,形象生動,《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很多精彩描述,成為經典名言,也為后世所不斷引用。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等名言,不時出現在歷代人士激勵經商的論述中。如“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貰貸行賈遍郡國”,往往成為描寫徽商、晉商等行商能力的專用語。如“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往往用來描寫陜西商人、山東商人的特別能吃苦耐勞的品格。如“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的觀念,往往成為各地地域商人經商的立身依靠和衡量擇業是否得當是否成功的尺度。至于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抗禮的行為,成為描寫后世豪商巨賈的成功典范。如“冠帶衣履天下”的描述,后世常用。明萬歷時杭州人張瀚的《松窗夢語》,描述南京,即稱“三服之官,內給尚方,衣履天下”。6史記《貨殖列傳》對商人行為的諸多描述,往往成為后世商人墓志銘的畫龍點睛之筆。
(責任編輯: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