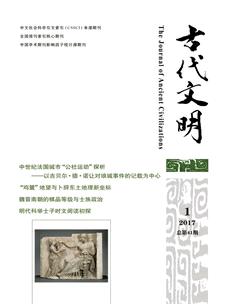明抗倭援朝戰爭初期中朝宗藩間之“信任危機”及其根源
孫衛國 解祥偉
提 要:抗倭援朝戰爭初期,明與朝鮮間本來穩固的宗藩互信關系出現危機。戰前,先是朝鮮私自通信日本種下禍根,繼由東亞貿易網傳來朝鮮誘引日本入犯大明的報告。朝鮮感到壓力后迅速派使辯誣,暫時修復了信任關系。戰初,朝鮮節節潰敗,但遲遲未向明廷請援,再度引起明朝懷疑。面對危局,明朝主動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撥使節進入朝鮮;朝鮮則連遣使節入遼、入京請援,同時與東來明使臣溝通,釋疑辯誣。經過努力,雙方終于再建信任關系,并迅速投入到聯合對日作戰中。上述信任危機的產生及其應對處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關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為中隱含著別有意味的內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鮮宗藩關系框架下,辯誣、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處理不良事件而成為宗藩體制之重要內容。
關鍵詞:明代中朝關系;抗倭援朝戰爭;朝鮮宣祖國王;“信任危機”;朝日關系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3
朝鮮王朝與明朝經歷了建國初期的摩擦后,雙方建立起穩固互信的宗藩關系。其后二百多年間,這種關系曾遭受過各種挑戰。1592年4月,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則是對明、鮮間互信的宗藩關系最為嚴重的挑戰。先是,戰前明朝懷疑朝鮮誘引日本入犯;戰爭爆發后,進而懷疑朝鮮國王與日本勾結,假倭入侵。面對信任危機,雙方都采取措施積極應對,盡力消除隔閡,尋求關系正常化。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已有所關注,但仍有很大拓展空間。1從中朝宗藩關系視角看,學術界一般強調中朝宗藩關系的“典型性”,2而對其“非典型性”一面討論甚少。筆者探究此問題,試圖揭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關系”中“非典型性”的一面,以期豐富學術界對宗藩體制和明代中朝關系的認識。
一、日鮮通信與明鮮信任危機
萬歷朝鮮之役期間,明、鮮信任危機,當從朝鮮庚寅通信日本說起。萬歷十八年(1590年),即朝鮮宣祖二十三年,歲在庚寅,朝鮮派遣黃允吉、金誠一為正、副使回聘日本。1看似尋常的這次通信使活動,實際卻蘊含著非同尋常的意味。
首先,這是一次與當時東亞華夷秩序相違背的外交活動。15世紀,由于日本與東亞朝貢貿易圈的變化,朝鮮與日本之間的通使性質發生重大變化。明朝立國之后,朝鮮和日本分別于1392年和1402年加入明朝主導的宗藩體制,在這一制度圈內,雙方通使本屬藩國交鄰之常規,故而本次通使前,朝鮮遣使日本多達59次,2明廷并無異言。3然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陷入內亂的日本中斷了勘合貿易,事實上脫離出“冊封—朝貢”體制,4在這種情況下,朝貢貿易圈內的朝鮮,作為明朝的藩屬國,如再與“圈外”的日本通使,違背了“人臣無外交”的原則。
其次,朝鮮王廷刻意隱瞞通使日本之事,破壞了對明朝的“事大”準則。在1587至1591年間,朝鮮兩次高規格接待日本使節,繼而遣使回聘,如此頻繁的外交活動從頭至尾竟不露聲色,對明廷諱莫如深。按照東亞華夷秩序下宗藩關系的交往準則,宗主國要“字小以仁”,藩屬國須“事大以誠”。所謂誠者,誠信也,亦即藩屬國必須忠誠于宗主國,保持一種值得宗主國信任的狀態。5朝鮮的做法顯然違背了這個基本準則。
再次,通使日本時,朝鮮所獲得的倭情,對明“從輕奏聞”,繼而留下了嚴重后患。16世紀80年代,日本政局發生巨大變化。豐臣秀吉統一全國,開始策劃對外擴張,并把主要侵略矛頭對準明朝,試圖建立一個控制東亞地區的日本帝國。61587年和1589年兩次遣使朝鮮,目的就在于探明朝鮮形勢,謀劃先侵略朝鮮,繼而入犯中國大陸。這個侵略野心,在當時給明朝造成莫大威脅,問題可謂嚴重之至。7在1590年朝鮮回聘過程中,日本蔑視通信使,稱朝鮮通信使之行為“入朝”,所帶禮物為“方物”,接待禮儀上屢屢違禮慢待,同時在回復國書中明目張膽地要求朝鮮配合其侵略活動。8通過這次通使,朝鮮對日本侵略明朝之野心,已完全明瞭,然竟對明朝故意隱瞞真相,最終埋下明、鮮信任危機的禍根。
1591年5月初,通信使歸國后將日本國書呈遞國王,由于國書中日本宣稱將“一超直入大明國”,9事關明朝上國,朝臣對于是否向明朝通報出現分歧。判書尹斗壽認為應該陳奏明朝,聽明廷決斷;兵曹判書黃廷彧表示贊同,曰:“我國家事天朝二百年,極其忠勤,今聞此不忍聞之語,安可恬然而不為之奏乎?”10認為應該防患于未然,否則萬一日本入犯,明朝沒有準備,朝鮮必定后悔莫及。副提學金睟則強烈反對,認為豐臣秀吉的話只是一派狂言,如果倉促陳奏,一來使明朝廷徒為擔憂,二來日本必定知道,一定怨恨尋釁,“若既奏之后,果無犯順聲息,則非但天朝必以為不實而笑之,至于日本則亦必以此而致怨,他日之憂有不可言。”11左相柳成龍贊同暫緩陳奏,“聞諸使日本者之言,則必無發動之形,雖發亦不足畏。若以此無實之言,一則驚動天朝,一則致怨鄰國,秀吉之怒,未有不由此而始萌也,至于通信一事,直為奏聞之后,萬一自天朝盤問其曲折,則恐必有難處之患也。”12宣祖國王認為明朝可能通過福建等地商貿網絡得知朝鮮通信日本之事,擔心如果隱瞞不報,將來明朝追問,朝鮮則不好交待,因此主張以陳奏為佳,但并沒有做出最后的決斷。1
為此,朝鮮采取了兩全的措施:一方面在回復日本國書中,以與明朝系君臣大義,明白拒絕日本的要求,道:“惟我東國,即殷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故中朝之待我,亦視同內服,赴告必先,患難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親者……人臣之有黨者,天必殛之,況舍君父而黨鄰國乎!”2另一方面采納左承旨柳根意見,對明“從輕奏聞”,即遣賀節使金應南五月份入京時“略具倭情”,“稱以傳聞為咨文于禮部”。至于隱瞞與日通使之事,則以朝鮮被擄人從日本所帶回傳聞予以搪塞,“若以聞于被虜逃還人金大機等三十余日本刷還者為辭,極為穩當。”3朝鮮王廷雖拒絕了日本的要求,但最終對明廷采用了繼續瞞報和盡量遮掩的處理辦法。
與此同時,明朝陸續得到倭情報告。1591年7月,福建海商陳申攜帶琉球中山府長史鄭迥倭情報告送達福建巡撫趙參魯處。41592年2月,在日華人郭國安、許儀后的報告亦送達。陳申,福建人,遭遇海難漂至琉球,身患重病而滯留。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遣使要求琉球朝貢和提供壬辰戰事所需錢糧。由是,陳申探知倭寇“(將)入北京者,令朝鮮為之向導”。鄭迥,字利山,祖籍福建,為明初移居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5
中鄭姓后人。他曾以琉球官派留學生身份來華學習,對明感情頗深。陳申獲得倭情后,與時任琉球王廷事務長史的鄭迥商議,并通過其幫助,搭乘琉球朝貢船歸國報告:“朝鮮國已造船向導助戰”。6在日華人郭國安、許儀后均為明朝人,二人因海難被倭寇擄到日本后,以醫術見用、見信于薩摩藩主。在郭、許二人幫助下,同樣是被倭寇擄掠至日本的福建海商朱均旺將倭情傳回國內,“高麗國遣官入貢為質,催關白速行。”716世紀末的東亞海域,中國與朝鮮、琉球等國之間除了官方的朝貢貿易外,還存在著民間貿易。借由這些商業網絡,人員往來、文化交流、情報傳遞等活動至為頻繁,東亞各國彼此分享著同一個“世界”。8在這種大環境之下,朝鮮私自通使日本之行跡,經由各方情報虛虛實實地傳入中國,并傳聞成朝鮮勾結并引導日本入犯大明。朝鮮瞞報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由此顯現。
最后,戰爭初期,朝鮮在節節敗退之際,并未積極向明朝請兵,更加重了明廷對其疑忌之心。1592年四月十三日,日本軍隊從朝鮮釜山浦登陸,分三路入侵朝鮮,壬辰戰爭爆發。由于朝鮮“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9日軍很快攻克東萊、金海、密陽、尚州,過天險鳥嶺后,直逼漢城。四月二十八日,朝君臣即有“去邠”之議;三十日,國王“西狩”;五月初三日,京城陷落;六月十五日,平壤亦陷,君臣奔義州。10僅兩月時間,朝鮮“殘我八路、夷我五廟、陷我三京、燒我二陵”,11情況極其慘烈,兵將潰敗之巨,引起明朝的懷疑,“你國乃天下強兵處,何以旬日之內,王京遽陷乎!”12另一方面,在如此潰敗的情況下,朝鮮并未立即向明請援。朝鮮對遼東兵將持有戒心,遲遲下不了請援決心,“大臣以為遼廣之人,性甚頑暴,若天兵渡江,蹂躪我國,則浿江以西未陷諸郡,盡為赤地。兩議相爭,日久不決。”13更有甚者,朝鮮邊將直接拒絕明朝援兵,“寬奠堡總兵召義州牧使黃琎謂曰:‘爾國受兵,自上國不可不救,俺當不日領兵過江,爾其以此意,急急啟知。琎曰:‘我國雖猝被兵禍,舉國奔播,然敝境兵足以當賊。豈勞大人之救乎?總兵笑而去。”1以此疑慮耽擱,朝鮮請援使節遲遲沒有遣出。這一反常舉措,使明廷更加懷疑朝鮮遭受日本侵略的真實程度。在彼此疑懼的氛圍下,隨著日軍步步緊逼,朝鮮君臣紛紛北逃,國王為假王的傳聞便開始播揚,“朝鮮與日本連結,詭言被兵,國王與本國猛士避入北道,以他人為假王,托言被兵,實為日本向導”,2此后當國王真向明朝請求內附之時,明廷則更加顧慮朝鮮立場,懷疑朝鮮國王請求內附是假,所言被犯失國亦詐,實欲作為向導引誘倭寇入犯中國。
壬辰大戰爆發之際,朝鮮王朝原本應該仰仗明朝,聯合抗擊日軍,但由于朝鮮在一系列問題上處置不當,加劇了明朝對朝鮮的猜疑。煙火彌漫,疑云密布,兩國宗藩間互信關系遭受到劇烈的沖擊。如此下去將使戰爭情勢,對朝鮮更加不利。如何重拾明朝的信任,并化解危機,使明朝迅速投入到對日作戰中,成為朝鮮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明、鮮對“信任危機”的處置
日軍侵略朝鮮,是對傳統東亞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明朝也逐漸認識到“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3朝鮮無法承受各種傳聞所引起的宗主國明朝之猜疑,隨著局勢緊張,取得明朝信任,得明軍大舉入援,是唯一應對危局的辦法。故此,對于信任危機,明、鮮均高度重視,朝鮮只得接連遣使入明辯誣,明朝不斷派人入朝勘疑,雙方均積極應對,盡心化解。
萬歷十九年(1591年)五月,朝鮮賀節使金應南入遼,朝鮮王廷命他視情況而定,靈活奏報倭情,但他發現遼地“一路嘩言朝鮮謀導倭人入犯”,態度上亦“待之頓異”,到山海關則被大罵,“汝國與倭同叛,何故來耶?”4意識到倭情已泄,便隨機應變,“即答以為委奏倭情來”,遂使“華人喜聞,延款如舊”。5到達北京后,明廷恰剛接到趙參魯奏報,當時已是“國言喧藉”,皆言朝鮮與日本勾結入犯,只有閣臣許國尚替朝鮮說話,“吾曾使朝鮮,知其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姑待之”。6見此情形,金應男當即遞交所備倭情咨文,辯明朝鮮拒倭立場,得此解釋,明廷方“群疑稍釋”。7
該咨文雖然傳遞了倭寇即將入犯的情報,但卻以被擄漂流人傳聞作為情報的來源,“圣節使金應南之去也,以倭賊欲犯上國之意移咨于禮部,據漂流人來傳之言為證, 而通信使往來之言,初不及之也”,8在掩蓋與日通使真相的同時,降低了情報的可信程度,影響了明廷對形勢的判斷,并未解決問題,遺患仍在。
次年二月,在日華人郭國安、許儀后的情報送達后,明廷再度掀起輿論風暴。由于許儀后在日生活多年,與薩摩島主關系密切,情報非常可靠。此則情報披露了鮮、日交通和日本外犯的諸多細節,如“五月高麗國(朝鮮)貢驢入京,亦以囑琉球之言(吾欲遠征大唐,以汝琉球為引導)囑之,賜金四百,高麗之貢倭,自去年五月始也”,“今秋七月一日,高麗國遣官入貢為質,催關白速行,九月初七日文書行到,薩摩整兵兩萬,大將六員到高麗會齊取唐,六十六國共五十余萬,關白親率五十萬,共計百萬,大將一百五十員,戰馬五萬匹。”9這使得明廷剛剛消除的疑云,再度泛起。兵部隨即“使遼東(都司)移咨于朝鮮,問其然否”。10明朝官方正式詰問,并直接追責朝鮮與日本交往之事。面對這一外交危局,朝鮮于同年十月派出陳奏使韓應寅一行,專門攜帶辯誣奏文,入京陳辯。
朝鮮首先解釋倭情已匯報于明,“已將所聞未委虛的及伊賊哄脅難測事情,節次備咨禮部,順付赴京陪臣去后,今該前因,已經略具詞節回咨都司,計已轉聞朝廷。”進而指出日本故意傳言朝鮮誘其入犯,意在離間明、鮮關系,“及說入北京,令小邦向導,入福、廣、浙,令唐人向導,小邦有無為伊向導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人,果何指認,而一體準擬如此!雖蠻荒代有逆種,未有似伊狂妄者……乃敢張說虛喝,但得展轉疑惑”;繼而辯稱朝鮮與日本原不往來,然偶為國防及刷還人口計會有羈縻之策,遣人前往實地打探倭情,“要以偵探彼中,以為伊國道里物力,只憑傳聞,動靜機詐,徒付遙度,委于應敵之道不便故也”;最后傾訴委屈,表白朝鮮事大忠心,“自臣祖先有國,世篤忠順敬畏”,而現在輿論懷疑朝鮮為日向導,十分冤屈,“乃以向導之名歸之,言亦丑辱,臣何不幸!”1奏文層次分明,雖然仍然沒有透露通信日本之實,但提到刷還人口遣人使日之事為遮掩,并飽含冤屈之情,對明事大之誠溢于言表。
朝鮮自立國后,一直對明恭順事大,明神宗寧信其真,接受了朝鮮的解釋,“(朝鮮)偵報具見,忠順加賞,以示激勵”,2接著“出御皇極殿,引使臣慰諭勤懇,賞賚有加,降勅獎論。皇帝久不御朝,外國使臣親承臨問,前所未有也”。3禮部亦擬獎敕云:“朝鮮國王李昖,克修職貢,恥言向導,顧效防御,宜示旌嘉。”4受此褒獎,朝鮮再遣申點等入貢謝恩,國王“令奏倭情,比前加詳”。5這樣,戰前猜疑風波暫時平息下來。
然而來年大戰爆發,朝鮮節節潰敗而不請援,再次引起明廷的猜疑。這次明朝率先采取行動。五月末,兵部尚書石星派遣崔世臣、林世祿一行到朝鮮調查實情。此時朝鮮仍沒有決定向明朝請援,以為使臣是來商討入援事宜,故打算將使臣擋在邊城,且以朝鮮殘破,明朝大兵無法久駐為由,委婉拒絕明朝入援的可能,“托以迎慰,實欲以我國(指朝鮮)殘破之狀,面陳天兵難久住之意,令差官不到平壤,自義州回去”,6然而隨著國王向北一路敗退,“時變起倉促,訛言傳播”,7假王假倭謠傳正盛,朝鮮王廷覺察崔、林入境“以探審賊情為名,實欲馳至平壤,請與國王相會,審其真偽而歸”,8朝鮮無法承受明朝對其國王真假的質疑,于是改派禮曹判書尹根壽兼宣慰使將崔、林迎入平壤。六月初,朝鮮國王親自接見,坦誠交代時情:“敝邦不幸,為賊侵突,邊臣失御,且因升平日久……寡人失守宗祧,奔避至此,貽朝廷憂恤,重勞諸大人,慚懼益深。”9同時,派領相柳成龍帶林世祿到前線探察倭兵。至此,明使查明真相,深覺形勢危急,于是“世祿唯唯,亟求回咨而去”。10對此,明朝政府當即做出決定,六月二日即“令遼東撫鎮發精兵二枝,應援朝鮮”;11十五日,遼東所派參將戴朝弁、先鋒游擊史儒帶兵一千零二九名、馬一千零九十三匹渡江入鮮。12雖然兵馬不多,但可看出明廷對朝鮮已經釋疑,并開始入援。
至六月中旬,朝鮮局勢更加不堪,國王不斷與大臣商討內附明朝之議,并于六月十三日定議內附之策。內附的前提首先是得到明朝的信任,請明援助,關鍵是必須消除明朝的疑慮。在崔、林二人勘疑釋嫌之后,朝鮮又接連派兩撥使臣正式請援,一由李德馨到遼東都司,13一派鄭昆壽入京面請。14《明史》記載這時期朝鮮“請援之使絡繹于道”。15此時,國王請求內附之舉,恰與先前“假王誘引日本入犯”謠言相合,明廷又難辨其虛實,于是再派使臣入朝勘疑。朝鮮再次被動應對辯誣。
六月十四日,朝鮮國王命大臣“修內附咨文,送遼東都司”。1遼東都司收到咨文后,將其轉送兵部,并提出疑慮:“朝鮮號稱大國,世作東藩,一遇倭賊,至望風而逃……倭奴譎詐異常,華人多為向導,若攜詐闌入,貽害非常,則作何處置?”2為此,遼東巡按御史李時孽先自派遣曾經見過朝鮮國王的指揮宋國臣,以送咨文為名再入鮮境,刺探真偽,“巡按以我曾從黃天使出來,親見國王面貌,故使之來見真偽”,在看到國王為真王后,國臣復命報稱“的是真王,非假王也”,“遼鎮信之”。3
內附咨文遞入北京,正值明廷百官對是否大規模出兵援朝激烈爭論之時。多人激烈反對出兵,如兵科給事中許弘綱認為四夷應該為中國守,而不是相反,“中國御倭當于門庭。夫邊鄙中國門庭,四夷則籬輔耳。聞守在四夷,不聞為四夷守……(朝鮮)望風逃竄,棄國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葦障乎?”4直隸巡按御史劉士忠認為援助朝鮮會加劇國內局勢嚴峻,會導致民心不穩、財政吃緊、兵力部署被擾亂,“天津兵士占民屋奪民食,民思逃竄,而盛暑大雨,軍多暴露于烈日霖霪中,又沿海柴草不生,水苦咸,飲食不便,往往嬴瘠。南北兵爭窩,互斗洶洶,恐有他虞,是軍與民俱困也。天下事定于鎮靜,擾于張皇,今倭限天塹,飛渡為難,入秋海颶大作,且久戰高麗,物力亦罷,豈遽航海與我爭衡,未見倭形,先受其敝”。5朝鮮和遼東呈文上達后,進一步加重了明廷出兵的疑慮,為此,兵部尚書石星再派指揮黃應陽、夏時、徐一貫等人攜帶畫師進入朝鮮境內,以偵報倭情為名,核查朝鮮國王真偽。
七月一日,黃應陽一行入境,經過宋國臣一事,朝鮮意識到“此人往還,機關慎重”,國王隆重接待,力圖“不使之落寞,以失其心”。同時,大臣尹根壽出示兩份日將行長、義智所寫的“倭書”,剖白心跡:第一份是六月一日寫給李恒福的。希望朝鮮質子于日本,與日本和親,日本駐兵朝鮮八道,“幸甚以賢計慮,和親如何?貴國若要和親,王族及當權之輩,為質子,遣日本可也……若枉黨日本,只遣質子而已。吾諸將分遣八道者,粗錄其姓名,以備臺覽”。6第二份是六月十一日寫給李德馨的。要求李德馨將日本愿與朝鮮結黨、和親,合力入犯大明之事上達國王,“庶幾枉黨于日本,相議犯大明乎?又運和親之籌,然則回龍駕于城中耶?抑亦留龍駕于平安道耶?只在龍襟而已。”7兩份“倭書”,反映了日本對朝鮮之威逼利誘,朝鮮由于堅守對明朝的君臣大義而遭日寇侵犯的原委。見到“倭書”,黃應陽等人煥然釋疑,曰:“探哨人,不會見真倭,恐是假倭子,今見倭子書契的是真倭,爾國為天子失家失國,許多生靈盡被屠戮,竄一隅而猶不變,真可憐憫。”8
次日,朝鮮國王約見黃應陽三人,滿懷委屈哭訴冤情:“上年倭奴欲犯上國,令小邦向導,而小邦斥絕假途之謀。故肆毒蹂躪,古今安有知此事!”黃等大為感動,以至憤呼:“(朝鮮)為賊所迫,不變臣節,而中國不知,反疑之。”當時,彼此“相向哭,良久而止”。9經此了解,黃應陽等人表示不再去平壤觀察真倭,而直接回京復命,請朝廷盡快發兵,“爾國堅持臣節,嚴拒逆謀,搆怨速禍,破國亡家,爾既以盡忠而遭釁,我焉忍坐視而忘情?是以遠勤圣慮,特遣偵詢,務俾得其虛實,必欲救其生靈,矧流離播棄,仁君之所深憫,而毒痛暴戾,天討之所必誅,亟遣陪臣,即時東向。”10回國之后,黃應陽立即報告兵部,“星大喜,東援之役乃決”,11“自此中朝知無其它,遂大發兵來救云矣”。12十月十六日,明廷命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御倭總兵官,率兵援朝。1至于朝鮮國王內附之事,本身就面臨國內群臣的激烈反對,此后更隨戰局逆轉而不了了之。
綜上所述,萬歷朝鮮之役戰前東亞疑云密布,明朝對朝鮮的疑慮與日俱增,朝鮮為重拾宗主國信任,先以賀節使金應南兼奏,繼以陳奏使韓應寅專門奏報倭犯情節,使宗藩間疑懼初步得以稍釋。戰爭爆發后,局勢日漸緊張,朝鮮遲遲未向明請援,加之國王一路北退,各種傳聞再起,而此后國王內附請求,又與傳聞相和。為慎重起見,明朝主動勘疑,兵部及遼東都司接連派出三批使臣,入朝探查國王、軍情真偽。朝鮮亦積極應對,通過國王親自接待使臣、將日本勸降信件交于使臣查看、帶使臣于前線探見真倭等措施,辯誣釋疑,最終消除雙方信任危機,共同聯合對日作戰。
三、從明鮮宗藩信任危機看明代中朝宗藩關系
明、鮮信任危機問題的產生及雙方的處置辦法,反映了明代中朝宗藩關系中較少被關注的兩個層面。
第一,信任危機的產生,表明明代中朝宗藩關系雖號稱“典型”,但其中存在“非典型”的一面,朝鮮王朝在事大主義的旗號之下,考量其國家利益,不惜違背宗藩關系準則。
縱觀古代中朝宗藩關系史,文獻史料中比較引人注目的往往是雙方“典型性”的一面,與其它藩國相比,中朝往來更加頻繁,關系更為密切,交往制度最為完善,堪稱中外宗藩體制中的典范。2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并非如此,在14世紀末,高麗王朝曾在北元和朱明之間幾次反復,甚至殺掉過明使;315世紀前期,申叔舟等曾出使日本,并留下尊日正朔的案底;416世紀初,在得明“再造之恩”背景下繼位的光海君,也對明多懷“兩端”之心。5壬辰戰爭時期在位的宣祖國王,雖然朝鮮史料稱其“事大之誠,無所不用其極”,6但朝鮮在戰前及戰初,卻明顯存在著對明違禮和瞞報等行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因為朝鮮王朝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意為之。
本次明、鮮信任危機,始萌于朝鮮私自與宗藩體制圈外的日本通使,并對明朝刻意隱瞞,違背了宗藩間“人臣無外交”的原則;進而朝鮮瞞報倭情并且一味遷延,破壞了宗藩關系中“事大以誠”的準繩,進而在戰前及戰初引發種種猜疑傳聞,幾乎影響到了中朝邦交。基于整個中朝關系的視域,該如何看待這一系列并不符合宗藩交往準則的行為及其性質?
考察這一決策形成過程,可見朝鮮君臣反復考量的因素只有兩個:一是事大“大義”,二是“國家利害”。朝鮮君臣之所以激烈爭論,內心糾結,問題在于二者形成一對矛盾,即坦誠上報堅守了事大大義,有礙國家利益;瞞住不報則正好相反,如金睟、柳成龍所言如果明奏倭情,一是懼怕被日本獲悉,遭受其疑忌和侵犯;二是也擔心明廷發現朝鮮通使日本行跡,以致受到責備。柳成龍還料想,即使豐臣秀吉張狂出兵,也必然無法打到中國大陸,而朝鮮近在咫尺,必然橫受其禍,因而日本不能得罪,奏報萬萬不可。可見在其權衡中,朝鮮國家利益成為最重砝碼。商討最終折衷而行的“從輕奏聞”,看似顧全了兩個方面,但是由于其隱瞞與日通使之事,影響了情報的可靠性,結果干擾了明朝對形勢嚴重程度的判斷。
第二,考察兩國對信任危機的處置,可見在宗藩體制下,除了進貢、冊封等常規儀式外,還存在著處理特殊事件的如辯誣、勘疑等慣常做法,它們都在維護宗藩關系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因受宗藩制度的規范約束,而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在本次宗藩信任危機中,辯誣無疑是朝鮮王朝主要的應對手段。本來朝鮮對倭情特別是擅自交倭之事,極力遮掩,但當其發現瞞報,惡果已現,關于朝鮮引誘日本入犯中國的謠言大起,明朝上下在震動之余,對朝鮮已起疑心的時候,朝鮮迅即采取辯誣的辦法。承擔朝貢任務的賀節使金應南,率先主動兼起辯誣的任務。而當日本和琉球傳來的情報再度引起明廷震動,并詰問朝鮮之時,朝鮮迅即任命韓應寅為陳奏使,專門攜帶奏文到北京辯誣。大戰爆發,朝鮮迅速潰敗和假王假倭傳聞又使明廷生疑之際,朝鮮重臣乃至國王也加入了辯誣的隊伍。由于其想方設法、不遺余力,加上兩國關系一貫良好,明廷對朝鮮一直信任寬容,百官乃至皇帝都輕易接受了他們的各種解釋,一度消除了對其的疑慮和誤會,褒獎有加。盡管朝鮮在匯報倭情問題上一味遮掩,不但其辯誣奏文“甚(陳)委曲,而不能悉陳通使答問之事”,1而且國王、大臣幾次面臨明使勘疑仍對通倭諱莫如深,因而并未盡到“事大之誠”,但雙方信任危機很快得以消釋,迅速投入到對日聯合作戰中去,因此,辯誣在處理兩國關系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另一方面,明朝作為宗主國則常用勘查實情的手段,消除疑慮。在壬辰戰初處置信任危機過程中,明朝勘疑的積極作用尤其明顯。當各種謠傳泛濫之時,明政府主動遣使,從朝廷到地方連續派使臣入朝鮮,從辨別國王真偽,到眼見真倭來犯,勘疑使節迅速查明朝鮮實情,消除各種不實的傳聞,打消了明朝上下對朝鮮的猜疑和減小了大規模出兵支援的阻力,進而為雙方信任重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于這兩個層面的考察有利于更好把握中朝宗藩關系的復雜面相,從而更全面看待傳統中國與朝鮮的交往。
綜上所述,通過以上對壬辰戰爭時期明朝與朝鮮之間信任危機的產生和處置之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信任危機背景下,明鮮處理雙邊關系的某些心理態度和所作所為,這是明代中朝關系中為人較少關注的層面,但并不意味著特殊例外和無代表性。任何事物包括明、鮮信任關系,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在“事大字小”問題上,朝鮮對中國的忠誠和欺瞞、中國對朝鮮的信任和懷疑,皆作為一對矛盾,在中朝關系的動態延續中,此消彼長或相互交替。盡管朝鮮對明朝的恭順忠誠和明朝對朝鮮的仁義寬容,都非常突出,稱頌于史,但不可否認這并非絕對無二與一成不變,因為大義背后還存在著決定雙方態度和政策變化的國家利益因素的影響。2另一方面,對于中朝宗藩體制,學者大多關注進貢、冊封等重要形式,而對于辯誣、勘疑等卻容易忽視。雖然它們不屬成文規定,但已廣泛且有效運用,甚或約定俗成,無疑同樣屬于宗藩體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明代中朝關系遇到問題、互信體制受到損害之時,辯誣和勘疑活動可以及時有效地進行彌補,從而在維護宗藩體制上起到獨特作用,因而應當重視此類交往方式之意義。認識到這些,將有資于更全面地關照整個對明代宗藩關系體系復雜性的認識。
(責任編輯: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