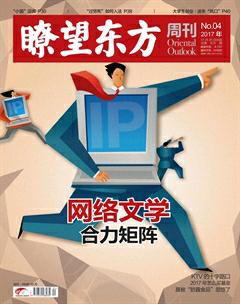“野百合”的春天來了?
劉佳璇
“一切跟5年前已經大不相同。”網絡作家唐家三少感慨。
2016年12月,唐家三少出席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作代會”),并當選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成為首位進入中國作協主席團的網絡作家。
5年前唐家三少第一次出席作代會時,整個會場的網絡作家還屈指可數,而在中國作協5年來2553名新發展的會員當中,網絡作家等新興文學群體已占13%。
從默默碼字到被粉絲追逐,再到被資本熱捧、被主流社會認可,唐家三少的經歷是整個網絡文學行業發展的縮影。
在媒介轉型的大背景下,網絡文學迅速成長,伴隨資本對IP價值的重視,它從網上走到網下,深深嵌入大眾娛樂,引發了一個龐大的泛娛樂文化產業的勃興。
“資本注入,政策法規和評論界都參與進來,成就了一個全新的網絡文學場域。”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影響中國網絡文學的力量,已不再只是“受眾和資本”,而是變為“受眾、資本、文學知識精英、國家政策”四種基本力量的合力矩陣。一度被視作“野百合”的網絡文學,正生長蔓延出邊緣的“幽谷”,迎來新的春天。
從“隱形的大象”到“會跳舞的大象”
“它是一只隱形的大象,跋涉了最初的荒原,如今這只大象不僅不再隱形,并且開始放眼文學之外更廣闊的天地,它已成長為一只‘會跳舞的大象。”閱文集團CEO吳文輝對《瞭望東方周刊》這樣形容網絡文學的發展。
“大象”成長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媒介與技術變革對大眾生活的滲透。
2010年,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擴大了網絡文學的用戶基礎。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6年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1億,手機網民規模達6.56億。在此基礎上,網絡文學已擁有3億多受眾,規模增長率保持在3.5%以上,而2016年網絡文學市場規模則可達90億元。
15年前,吳文輝每天早中晚各“掃”一次論壇,就能把當天全網更新的小說看完,“而且沒有挑選的余地,那是個比較蠻荒的時代”。
互聯網普及之初,一些網民將線下出版物的內容分享到網絡論壇,積累起第一批互聯網閱讀愛好者。受此激發,一批愛好者在網上發布自己創作的原創小說,但這個行為仍帶有明顯的小眾特征。
文學網站漸漸出現后,網絡文學內容愛好者有了聚集地。2002年,吳文輝和朋友們建立起點中文網,并建設了一套收費制度。
“這是網絡文學建立自身商業邏輯的起點。”吳文輝說。
在線上付費習慣根本沒形成時,起點中文網這個看似“自尋死路”的決定,改變了網絡文學的未來——收費使得作者的留存率提高,進而激發了創新力,網絡文學由此迎來內容暴發期。
猶如玄幻小說主角潛伏多年后嶄露頭角、笑傲江湖,網絡文學這只“大象”改變的不只是中國人的閱讀,并且正用它自己的“舞蹈”,顛覆著文娛內容的生態體系與產業模式。
自《甄嬛傳》開始,網絡文學的IP價值凸顯,中國人的電視熒屏和電影銀幕上,出現大批由網絡文學作品改編的作品。
2016年,大眾所熟知的網絡文學IP改編作品,就有電視劇《歡樂頌》《老九門》《微微一笑很傾城》,電影《七月與安生》等。2017年1月8日,由網絡作家天下霸唱的小說《鬼吹燈之精絕古城》改編的同名網劇播出過半,獲得超過16億次的播放量。
“這類被影視改編后的網絡文學作品,社會影響力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大神作品能夠比的。”杭州師范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院長夏烈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這種輻射效應使得網絡文學的經濟體量在近5年內大幅增加,顯得空前龐大和活躍。2016年12月,網絡文學經由翻譯網站在海外得到譯介的消息引起行業關注,人們訝異地發現,原來網絡文學已悄然承擔起文化輸出的職能。
“整體來看,網絡文學越來越主流化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承擔起主流文學的職責。”邵燕君這樣認為。
正在告別“泥沙俱下”時代
越來越多的網絡作家和唐家三少一樣加入了作協組織,而浙江、上海、江蘇、湖北等地還成立了網絡作家協會。
這讓網絡作家找到了“組織”和認同感,也使得文學知識精英與網絡相互靠近。
一個重要的政策背景是,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對網絡文藝工作提出了“加強正面引導”與“吸引和團結互聯網和新媒體領域的文藝創作主體”兩點要求。
“過去‘泥沙俱下的局面必然要發生改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新媒體文學委員會秘書長吳長青對本刊記者說。
另一方面,盜版嚴重仍是行業痼疾。在全新的市場環境中,這損害的不只是作者收益和讀者閱讀品質,還直接影響著正版數字內容商的營收,甚至影響優質IP開發。
長江中文網編輯董江波曾作過抽樣調查,發現一些網絡文學讀者看到喜歡的作品后會先搜索免費盜版,“如果一時找不到,他們就會等盜版小說網更新”。
據艾瑞咨詢數據,擁有付費習慣的網絡文學用戶量雖在增長,但也只占四成,而搜索引擎、手機瀏覽器、云盤、貼吧、第三方應用等或監管不力,或在利益驅使下做“幫兇”,更使得“秒盜”橫行。
“對于這種現象,有時甚至麻木到不想評論。”網絡作家貓膩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不少盜版網站的服務器都設在海外,因此,維權成本高、取證困難,加上中國著作權法中對侵權行為的賠償數額定得偏低,使作者們對盜版常常感到無能為力。
可喜的是,伴隨行業規則的建立和政策法規的健全,這一現象在2016年已有所改觀。
2016年6月,百度貼吧為清理盜版網絡文學關停了一批文學類貼吧。不久后,閱文集團、掌閱科技等網絡文學行業龍頭企業聯合發起“中國網絡文學版權聯盟”,以網絡監督、舉報查處、提起訴訟等手段共同打擊盜版。
以閱文集團為例,2016年針對盜版侵權發起維權的成果是:發起民事訴訟數百起,成功下架侵權鏈接數十萬條,維權作品數萬部。
貓膩認為,平臺方的打擊雖有成效,但要“治本”,“終究還是要看國家的態度和整個社會的輿論環境”。
近年來,國家版權局等四部門開展的“劍網”專項行動,大量網絡文學盜版平臺被處罰。2016年11月,國家版權局又發布《關于加強網絡文學作品版權管理的通知》,細化了著作權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
過去,資本和受眾是影響網絡文學的主要力量,缺乏知識精英、國家政策的共同介入,力量不均造成裂隙,即盜版與“有數量缺質量”等問題。而今,隨著合力矩陣的形成,裂隙正在“修復”。
囤積IP已不再可能
2016年,IP市場迎來變局。或因IP本身的質量問題,或因開發過程中的急功近利,不少IP改編作品在口碑和市場效果上都“撲街了”,如《華胥引》和《云中歌》。
這一變化,將驅使網絡文學行業在IP開發環節進行“自我修復”。
“最終能夠創造出怎樣的文化產品與多少利益,還是要看作品的本身質量以及改編的態度及水準,這是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貓膩說。
“把IP做好”不僅僅是網絡文學行業要面對的,吳文輝表示:“包括影視游戲動漫開發方、資本方等都需要相互串聯,全產業鏈協同方能形成新生態。”
而在IP開發中因資本短視造成的泡沫現象,則以盲目哄搶與過度炒作為甚。
“看到有改編劇火了,就爭先恐后買IP,甚至一些根本不懂如何轉化的人也去投資性地囤IP,好像害怕現在不買就會被別人搶走了,這對原作者和購買者都不是好事。”有制片人說。
多位業內人士都對本刊記者表示,2016年的IP交易市場較之前兩年已大幅降溫。
一方面,優質IP大多“名花有主”,另一方面,IP改編作品的失敗也讓資本更加審慎。
“現在做項目的幾乎已不看IP,要看完整的劇本,過去粗鄙化的作業方式是達不成交易的。普通IP也做不動,沒人敢買,怕砸在手里。”吳長青說,總之,囤積IP已不再可能,接下來要解決的是IP全產業鏈的升級。
未來,會有相當一批跟不上升級步伐的IP運營公司遭遇大浪淘沙,而擁有完整娛樂產業鏈的互聯網巨頭們,則是IP運營的理想玩家。
一個例子是,由盛大文學和騰訊文學聯合成立的閱文集團僅成立兩年,便依托盛大文學的專業性、騰訊的資本與資源,成為網絡文學行業的“最大咖”,幾乎包攬行業頂尖內容——《鬼吹燈之精絕古城》便是企鵝影視聯合正午陽光開發的作品。
邵燕君則對這種“秦王掃六合”的局面表示擔憂:“對行業發展來說,過于壟斷性的力量并不好,長線來講仍需多元發展。”
騰訊系網絡文學企業的“一家獨大”,使中小網絡文學企業生存更加艱難。吳長青判斷,2017年是中小文學網站的重要轉型期,除了一部分中小文學企業之間互相抱團取暖之外,會有一批文學網站被并購或是轉讓。
中小原創文學網站想要生存,則需探索新樣式,深耕某一分眾市場。例如,2016年長江中文網便決定將定位由大眾閱讀平臺轉為精品閱讀平臺,通過征文形式集合湖北省的草根作家作品;白熊閱讀則探索二次元同人小說市場。
可以期許的是,行業重組將激發中小網站形成一種創新格局,帶動全行業的轉型升級。
下一個“大神”在哪里
“2016年我們給網絡作家發放的稿酬超過10億元,其中閱文集團旗下月入過10萬元的作者數量超百人,同比增長3倍。”吳文輝對本刊記者說。
多位網絡作者都對本刊表示收入在顯著提升,但稿酬已不是頂級“大神”最大的收入來源,對網絡作家富豪榜上的佼佼者而言,相當一部分收入來自IP運營。
顯然,在IP產業鏈逐步健全的過程里,一些有“大神”稱號的網絡作家,其影響力已遠遠不局限于線上。
夏烈舉網絡作家南派三叔為例,2016年南派三叔成立泛娛樂公司“南派泛娛”,2017年又以股東身份入駐“三十四天影業”:“他某種意義上是網絡作家+企業老總+ IP孵化人+ IP投資人這樣一個角色。”
頂級“大神”自立門戶并非個案,唐家三少、江南、天下霸唱等網絡作家紛紛開始內容創業,現身頻次遠高于往日,力爭行業話語權。
不過,網絡作者的收入也在大神“霸位”的局勢下,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分化,“高的一個月可達幾十萬元,低者則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到”。
貓膩坦言:“絕大多數職業作者都是起于興趣,因責任而堅持,被金錢與名聲所鼓勵。”
網絡作家的資源與收入漸漸形成了倒金字塔狀,有業界人士擔憂這使網絡作者群體落入階層固化和精英化的窠臼。而當中小文學網站營收出現困難,作者便不再留存,轉而投身大平臺,面對更激烈的競爭格局,新作者便因感到“沒有前途”而轉行。
“我不建議新作者全職寫作,因為如今要出頭已不像幾年前那么簡單。”網絡作家烽火戲諸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這似乎能夠解釋為何如今難出下一個貓膩或唐家三少。
吳長青認為,大多數平臺仍執著于“挖人”,卻沒有助力人才培育:“主要是通過資本來誘惑、吸引,說實話就這么多人,新力量培育不出來的話就互相‘挖,這會導致生態枯竭。”
人才培育需要各級網絡作協、各個網絡文學平臺和高校整合資源共同助力。畢竟,創新力決定了網絡文學的活力,也決定了“野百合的春天”有多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