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龍花開》自序
吳 然
《獨龍花開》自序
吳 然
兒童文學聚焦
·主持人語·
“兒童文學聚焦”為本刊新辟欄目,從本期起,將以相應篇幅,專門發表關于兒童文學的批評研究文章。本期所發四篇,既有對云南兒童文學“提燈人”吳然的重點研究,也有對近期云南兒童文學整體情況的解讀介紹。其中,吳然自序一文,披露了老作家吳然一部新著信息。該作描述的獨龍江,在云南最深處,作者數次踏訪,觸摸獨龍江奔跑的脈搏和心跳,傾聽獨龍江流淌的故事和歌謠。一氣呵成的長卷紀實兒童文學《獨龍花開》,以兒童視覺,以曼妙美文,記錄刻寫了老縣長高德榮、小學校長梅西子等系列人物,更描繪了一群呼之欲出的獨龍族孩子形象,讓讀者感受到其中真切的酸楚和疼痛,也感知到獨龍江的發展進步。走進《獨龍花開》,一定會領略到課本名家吳然古稀之年自我超越之作帶給你的別樣風景和審美震撼。我們在此先睹為快,實為新欄目的幸事。(冉隆中)
以前我當高壓輸電線路的巡線工,后來做報紙副刊編輯。多年來,我到過云南邊疆許多地方。
我喜歡寨子里的民族小學。那時候,很多孩子赤著腳,小臉上沾著泥巴,甚至有被刺棵劃破的血痕。但是他們唱著脆亮的歌,那活潑跑跳的小小的身影,山花般裝點著祖國邊疆的土地。
我一直想去獨龍江。
獨龍江,藏在云南的最深處,它的深,它的遠,它的難,它的苦,讓我拜訪它的夢想,推遲了一年又一年……
1985年4月底,我到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采訪。我跟著馬幫,沿著怒江邊的鹽茶古道,去閃打跟怒族同胞和孩子們過鮮花節。回到貢山,我就很想去獨龍江。
早在1981年,我買到馮牧前輩的一本散文小集《滇云攬勝記》,知道他1974年就翻越高黎貢到了獨龍江,在巴坡看望并“愛上了獨龍江畔的第一個小學以及小學旁邊的那座古老的藤索橋,當小學生們走過橋面時,他們搖晃得好像打秋千一樣……”
讀著這些文字,我心旌搖動,也想象著什么時候去拜訪這所小學。可是,當我有了這樣的機會,偏偏通往獨龍江的唯一的人馬驛路,還被幾米厚的冰雪封凍著而難以成行!我的感嘆,難以描述。
這一晃就是21年!
2006年6月,我已經退休,才得以和一群作家朋友在獨一無二的“獨龍江公路”的顛簸中,到了獨龍江。
老縣長高德榮打著傘,站在呼嘯的大雨中,為我們接風洗塵!
第二天,老縣長帶領我們拜訪了馮牧前輩筆下的巴波小學。正是這所建于1956年的小學,結束了獨龍族結繩記事、目不識丁的歷史,讓獨龍江第一次聽到了孩子們的讀書聲。
當我們走進昏暗窄小的教室,跟老師和新奇地看著我們的小學生交談時,老縣長悄悄地離開了學校。
直到中午在村寨里吃飯時,他才對我說,巴坡小學建校50年了。他小時候在這里讀書,以后又在這里當過老師。“整整50年了,學校的破舊讓我害羞。我去江里打了些魚……”他的話讓我感動和感慨。我們吃著洋芋、苞谷,喝著沒有放油的魚湯……
后來,我把我的感動與感慨,以《巴坡小學》為題,寫了篇散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將近10年后的2015年9月,晨光出版社潘燕副社長鼓動我,并安排第五編室主任張磊陪同,由余師傅駕車,再進獨龍江。
我們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六庫,約上州教委的楊李明老師,到貢山縣城后,又拉上楊老師老遠就喊“和大姐”的和麗芬老師,穿過前些日子才打通的6.68公里的“高黎貢山隧道”,三個來小時就到了魂牽夢繞的獨龍江。
一江碧水跳起來歡迎我們。
對我來說,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無以復加!
高老縣長除了多了個手機,似乎沒有什么變化。他正要趕著去指導村民種草果。見到我,說道:“我正想著,這一久你怕是又要來了啰!”拉著我回到屋里的火塘邊,燒了一罐茶,邊喝茶邊向我簡單地介紹了這些年國家助學脫貧的情況,接了個電話后便對我說:“你自己看好啰!我還有別的事……”朝我一笑,拜拜了。
這樣,我和幾位同行者流連在翡翠般的獨龍江畔,走村串寨,拜訪已經越來越少的文面老人,和正在院子里織約多(獨龍毯)的獨龍族婦女交談……
我的心牽掛著學校。
我們走進正在擴建的巴坡小學。我見到了9年前見過面的木文忠校長,他告訴我現在的楊校長年輕有為。
木校長的女兒師范畢業了,來頂替已經調走的小劉老師,和她一起來的,是一位志愿者大學生……
我們來到以前的“馬庫軍民小學”,看到的是已經改建為“馬庫國門小學”的新校區。
一位年輕的女老師正在給一個緬甸籍學生辦理入學手續。
這個靦腆的緬甸小女孩,對我笑著,用剛剛學會的不標準的普通話對我說:“老希(師)好!希希(謝謝)!”
年輕的女老師告訴我,獨龍江所有的學校都是全日制寄宿學校。孩子們,包括從緬甸來求學的孩子,都享受著邊遠的、人口較少民族在義務教育階段所有最優惠的政策:從碗筷、洗漱用具,到被服、鞋襪、書包都是免費提供。
我們看到,鄉政府所在地新建的中心學校,美麗獨特的建筑和孩子們跑跳的身影,倒映在奔跑的江流里。
姚明資助的中心學校的“小小夢之隊”,正在和龍元小學的籃球隊進行激烈的比賽。
兩年前到任的梅西子校長告訴我,在獨龍江,小學生的書包很輕。因為大多數學生的家離學校都較遠,學校實行的是“月假”,即每個月放一次或兩次假,假期有長有短。學校布置一種不帶書包的作業——參加勞動、保護環境、把在學校養成的好習慣帶回家。
梅西子校長帶著我參觀了學校的電化教學室、圖書閱讀室(我看到一些我熟識的作家朋友的書,有許多是他們捐贈的)、化驗室、美術室、音樂舞蹈室,以及傳承獨龍族傳統編織技藝的“約多編織工藝室”……
當梅西子告訴孩子們,和她在校園里轉悠的這個“白發男生”,就是課文《我們的民族小學》的作者時,我被孩子們包圍了!他們拿出課本、作業本、紙片,甚至伸出小手、湊過小臉讓我簽名……
我深深地感受到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寫作者的幸福與榮耀!
從獨龍江回來,潘燕、胡蓉、張磊、劉曉倩約我喝茶,笑瞇瞇地告訴我,要我寫一本以獨龍江小學為背景的紀實兒童文學作品。
一開始我不敢答應。我寫慣了短小之作,以一本書的規模,圍繞一個題材或者說主題來寫作,對年過古稀的我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我怕勝任不了,讓各位失望。而且在江邊撿石頭還砸傷了腳,要是接下這活計,怕真是再次“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我說了許多為難之處,潘燕總是笑瞇瞇地說“不急,不急”,她們也會幫我出主意,找資料等等。盛情難卻啊,只好應承下來。
于是開始整理采訪素材,像梅西子校長說的“用發現羊肚菌”一樣找出每個學生的特點。我在零零碎碎的采訪記錄中,從在搖晃的車上胡亂記下的一句話或者一個符號,在回想中重新回到現場,傾聽獨龍江的水聲和它流淌的故事……
我翻閱、查尋有關怒江、獨龍江,以及獨龍族、怒族、傈僳族等少數民族的種種史料,包括地名志、植物志、動物志和教育志,并收集各民族主要是獨龍族的童謠、民歌、神話、傳說,旁及民族服飾、節慶、宗教信仰和民族風情、生活習俗等等。
同時也請教李愛新、羅榮芬等民族學、民俗學專家,盡可能豐富和擴展自己欠缺的知識。外出時,我甚至都帶著有關的書籍和資料。
盡管在寫作中,有許多素材并沒用上,但卻因一本為孩子們寫的書,我做了許多背后的功課而欣慰。
整本書的寫作,我力求大處不虛,小處不羈,有的地方還帶有兒童視角的觀察與想象。
我用了曾經發表在《人民日報》那篇《巴坡小學》一文的題目和開篇的幾小節文字,作為本書的開篇,這是因為在獨龍江教育史上,“巴坡小學”本身就具有“開篇”的意義。至于書中具體的每一篇,也許看似不太連貫,但合起來又是整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寫作中,有時會一時找不到感覺而停頓,有時則被某個細節某個情景而感動,眼濕而看不清電腦熒屏上的文字。
寫作這種非常個體的勞作過程,在已經完成的作品中,沒有留下痕跡。讀者看不到這個過程。讀者看到的是已經印出來的文字,以及這些文字講述的故事和所表達的情意。我不知道如何與讀者分享這個過程。
衷心感謝幫助我完成這本書的每一位朋友!
感謝獨龍江!祝福我們的民族小學!
(作者系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責任編輯:程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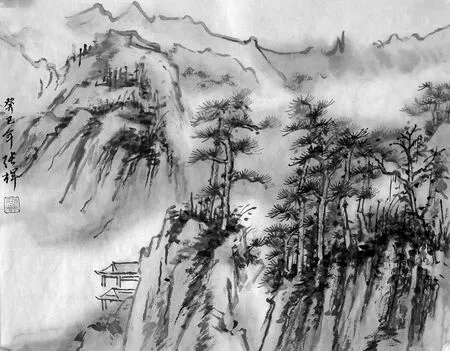
云山圖 國畫 張 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