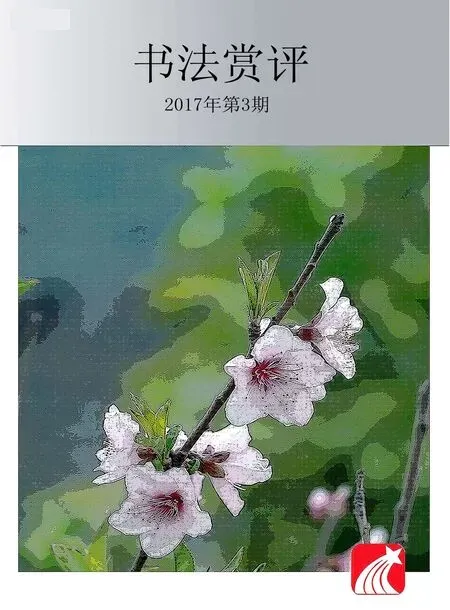影響草書書寫速度的要素探討
■張 敏
影響草書書寫速度的要素探討
■張 敏
一、草書書寫速度的爭議
每個(gè)學(xué)習(xí)草書的人都會遇到這個(gè)問題,草書書寫的速度是快還是慢,說快的可以有一堆的理由,說慢的也可以有一堆的理由。草書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龍飛鳳舞,動詞飛和舞都是自然能讓人和快速的運(yùn)動產(chǎn)生聯(lián)想的詞語,所以草書自然書寫速度是快的。
且有古人的詩句為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1]這里的三五聲應(yīng)該不是狼嚎似的悠長的叫聲吧,而是激情豪邁的叫聲,在這個(gè)叫聲里就完成了滿壁的字的書寫。千萬字雖有修飾的成分在其中,但滿壁絕對不會是幾個(gè)字,所以這里的快是有歷史的場景的。主張慢者,也有其道理,因?yàn)閷P墨的功夫掌握不好的人,字一快自然墨是不能吃進(jìn)宣紙里的,就產(chǎn)生了墨浮于紙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十分常見,且一般學(xué)習(xí)草書的人都不能一下子邁過這個(gè)坎,于是乎我們就聽到無數(shù)的大師諄諄告誡后來者,草書要慢一些,慢一些。快慢之爭將初學(xué)者引入了迷宮,快乎或慢乎,成了一個(gè)無解的問題。
社會上已然形成的教學(xué)定勢是學(xué)書先學(xué)楷,其實(shí)這個(gè)指導(dǎo)思想的深層邏輯也是來源于要先慢下來。楷書的書寫是不能快的,在練楷書的過程中磨掉自己的激情部分,讓書寫的速度慢下來。其實(shí)這種方法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書法發(fā)展的歷史上,楷書是在唐代才發(fā)展起來的,它的發(fā)展是稍后于草書的。那么自然第一個(gè)問題就是古人是怎么練習(xí)草書的,顯然由楷書的慢導(dǎo)致草書的慢這個(gè)邏輯就有先天的不足,不能充分說明問題。上世紀(jì)80年代曾有過學(xué)書是否一定要從楷書學(xué)習(xí)的爭論,但結(jié)果不了了之,后期又變成從楷書開始學(xué)習(xí)這樣一邊倒的潮流。隨之而來的另一個(gè)問題就是學(xué)習(xí)楷書久了的人,很難放開去寫草書,或是寫的草書較為拘謹(jǐn),像章草那樣的章法和結(jié)構(gòu)還能掌握,但像今草和大草那樣的字體、筆法和章法就很難去把握了。這也從另一個(gè)方面說明,楷書和草書還是隸屬于兩個(gè)不同的思維定勢。書譜云:“至如鐘繇隸奇,張芝草圣,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2]說的也是每個(gè)人只會在一個(gè)方面專精,其根本的原因是因?yàn)槭艿饺说乃季S定勢的制約。
可是由快而導(dǎo)致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字跡潦草,墨浮于紙,筆畫泄氣以致軟弱無力。尤其對于書法造詣不深的人,這幾乎成了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可以在各種場合看到這樣的書法作品,該駐筆的地方?jīng)]有駐筆,以至于滿紙滑動的線條,使人的眼睛不能停留,全無閱讀草書時(shí)的情緒起伏跌宕,完全喪失了草書的情感。
這樣的兩種主張旗鼓相當(dāng),彼此很難說服對方。我認(rèn)為,草書有自己的方法,既不是單純地快,也不是單純地慢,而是快中有慢,慢中有快,且有它自己的一套筆法和章法,才形成了獨(dú)特的草書藝術(shù)。書譜云:“真以點(diǎn)畫為形質(zhì),使轉(zhuǎn)為情性;草以點(diǎn)畫為情性,使轉(zhuǎn)為形質(zhì)。”[3]真是楷的前身,這也說明草書自身具有特定的體系。草書的快和慢需要我們從不同的方面去考量,從單字的堅(jiān)實(shí)程度來說需要慢筆,從筆勢的生成來說又不能慢,所以行筆的過程需要張弛有度,才能充分展示草書的張力感。
二、草書速度快慢
草書絕對不是單純地快和單純地慢,單看到任何一點(diǎn)都只是盲人摸象。總體來說草書的書寫速度是快的,這個(gè)快是從總體速度上而言,從上述的“滿壁縱橫千萬字”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書譜云:“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tài),絕岸頹峰之勢。”[4]這些對字的描述都是和草書的快速用筆相關(guān)聯(lián)的,無快不能成此勢,所以他們是對草書的形態(tài)做的描述。
書譜云:“雖篆隸章草,功用多變,濟(jì)成厥美,各有攸宜。”四種字體,各有功用,各有美的方法。但還“然后凜之以風(fēng)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嫻雅”,[5]這四種境界都是用不同速度的書寫體現(xiàn)出來的。以上這些都說明草書是快慢結(jié)合的產(chǎn)物,絕非單純地快和慢。因?yàn)椴輹膶徝谰哂行味系囊饬x,需要一定的審美意趣的人才能感悟,所以造成了很多普通人的誤解,誤以為草書就是一路狂奔地潦草。因?yàn)橹袊乃囆g(shù)門類中的審美體系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我們可以用歌唱來做個(gè)比喻,每首歌都有過門,起伏和高潮階段,如果將一首歌唱的音量大小一樣,就缺乏了美感,變成了直嗓子了。而美正是韻含在這音量的大小,音調(diào)的高低和委婉之中。這是音樂中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有了這樣的對比,音樂才呈現(xiàn)出美。書法也是一樣,草書的美孕育在一切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之中,這些矛盾如枯潤、快慢、方圓、大小和連帶之中,而制造這一切的基礎(chǔ)就是運(yùn)筆的快和慢。失去了這些就無法制造矛盾,沒有矛盾也就沒有統(tǒng)一,也就沒有了產(chǎn)生美的基礎(chǔ),草書的美也將不復(fù)存在。另外人們在書寫草書時(shí),也會因書寫的內(nèi)容的感染而產(chǎn)生情緒的起伏,這個(gè)情緒的起伏也會反應(yīng)在手上,使得行筆的速度產(chǎn)生快慢的差異。總之,快慢的張馳有度是草書美的基礎(chǔ),單獨(dú)地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方面將使草書失去審美的基礎(chǔ)。
三、書寫的空間結(jié)構(gòu)制約了單純的快或單純的慢
中國書法通過一個(gè)特殊的途徑把所有的空間組織成一個(gè)整體。[6]有些時(shí)候人們將中國書法描述成是用線條來分割平面空間,從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劃分有一定的道理。邱振中先生把書法的空間劃分為字內(nèi)空間、字間空間和行間空間。行間空間是由我們的視覺審美來調(diào)節(jié)的,可以和書寫的速度不關(guān)聯(lián),但字間空間就需要用用筆的速度來表達(dá)關(guān)聯(lián)性,常用的表達(dá)方法就是牽絲映帶和筆斷意連。牽絲和映帶的書寫一定是要快的,唯快才能產(chǎn)生動勢,才能產(chǎn)生牽絲,才能將上下字之間產(chǎn)生有關(guān)聯(lián)的感覺。在筆斷意連的方式中,筆斷處的鋒也一定是快速的提筆產(chǎn)生的銳利的鋒以造成空中行筆的意象。這兩種方式都是在牽絲的起點(diǎn)或筆斷的時(shí)候快速發(fā)力形成的結(jié)果,這個(gè)速度一般而言是比在字內(nèi)書寫的速度稍快,所以構(gòu)成了書寫過程的快慢對比。字內(nèi)空間也是一樣,單純的慢速就是描字,與書寫的感覺完全不符,由于缺少快速搶鋒的動作,字不能形成一定的勢,自然就無法表現(xiàn)出字的韻味,線條的動態(tài)感也無從表現(xiàn)。缺乏了這樣表現(xiàn)力的字也是呆板的字,與書法的定義相去甚遠(yuǎn)。所以即使在字內(nèi)空間的營造上我們也是要有不同的速度來表現(xiàn)一個(gè)單字的韻味以便構(gòu)筑一個(gè)有韻味的字形結(jié)構(gòu)。這方面的比較可以很容易從清代的館閣體和一般的行書體的比較得出判斷。
四、書寫的速度受到人的心理和物理結(jié)構(gòu)的制約
書寫是一個(gè)人情緒外泄的一個(gè)渠道,最著名的《蘭亭序》和《祭侄稿》帖都是在情緒軒昂的時(shí)候留下的印記,它準(zhǔn)確地記載了書寫者當(dāng)時(shí)的心情。后世的閱讀著能夠從存留的印記中在心里復(fù)現(xiàn)出當(dāng)年書寫者的情緒,這也是藝術(shù)品很重要的移情性特征,所以書法藝術(shù)品要想成為藝術(shù)品必須具備這樣的特質(zhì)。換句話說一個(gè)作品要想成為好的藝術(shù)品,它必須是與情緒結(jié)合的作品,所以作品肯定帶有人的心理情緒的起伏。另一方面,人是一個(gè)活的有機(jī)體,書寫是非常精巧的活動,它受到人的生理特征的影響和人的自身的物理結(jié)構(gòu)的影響,所以我們才能看到世人的書寫千人千面,即使是書法高手在臨摹前人的作品時(shí)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相同,而只能做到相似。其中蘊(yùn)含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書寫會帶有主觀的情緒因素和受自身物理特征的制約,其中情感因素又無法像物理特征那樣可以度量。無法度量的東西要想準(zhǔn)確復(fù)制就十分的困難,而這一點(diǎn)也正是我們在鑒定前人作品時(shí)所依賴的一個(gè)很重要的方法。我曾經(jīng)有過臨習(xí)《祭侄稿》帖的體驗(yàn),從字體上來看自我感覺是臨得很像的,但別人告訴我看不出悲憤的味道。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yàn)榕R帖時(shí)沒有充分體驗(yàn)顏真卿當(dāng)年聽到兄侄同為國家陣亡的那種悲憤的情感,所以臨帖只注重了筆型特征而沒有注入情感的因素。人的情感、情緒本身十分微妙且是一個(gè)隨時(shí)間而不斷在變化的一個(gè)東西,要想維持一個(gè)恒定不變的情緒也是不易的,所以嚴(yán)格地說我們是要控制書寫時(shí)情緒的起伏變化符合我想要表達(dá)的作品的意味,造成作品意味的正在于這些由于情緒影響的快慢的變化之中,不可能單純地快或慢。書法史上常常提到的書為心聲其內(nèi)在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我們說從人的主觀書寫的制約性和對藝術(shù)品的要求兩方面來看,書寫中快慢間雜而帶來的書法面目的變化是藝術(shù)品的必備條件。所以我們書寫草書時(shí)就要將這樣的情感起伏加以疏導(dǎo)和充分表現(xiàn),方能成就一件好的草書作品。
五、結(jié)論
草書的書寫速度是產(chǎn)生草書美的基礎(chǔ),沒有了速度的變化就沒有草書的美,或是將草書的美單調(diào)化了。學(xué)寫草書的人需要仔細(xì)研讀墨跡本的法帖,仔細(xì)揣摩其中的奧秘。由于古代的很多法帖都是以刻本的形式流傳下來的,在這些刻本中,由于復(fù)制的過程是一次成型的,所以筆畫中的速度感會消失。而這種沒有了速度感的法帖是會誤導(dǎo)人們進(jìn)入一個(gè)誤區(qū),或許要浪費(fèi)很多年我們才能真正領(lǐng)會到其中蘊(yùn)含有書寫速度的變化而形成的筆法的意味。
注釋:
[1]懷素上人草書歌,唐代竇冀
[2]書譜唐代孫過庭
[3]書譜唐代孫過庭
[4]書譜唐代孫過庭
[5]書譜唐代孫過庭
[6]書法邱振中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