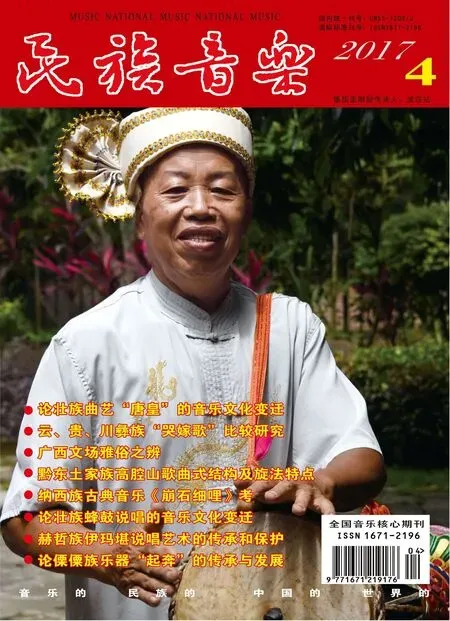論傈僳族樂器“起奔”的傳承與發展
婁斯佳(云南省文化館)
論傈僳族樂器“起奔”的傳承與發展
婁斯佳(云南省文化館)
傈僳族是云南跨境少數民族之一,他們主要居住在云南怒江傈僳自治州。傈僳族和彝族、納西族在族源上關系密切。8世紀以前,傈僳族居住在四川雅礱江及四川與云南交界地的金沙江兩岸廣大地區。傈僳之名首見于唐代樊綽《蠻書》,稱之為“栗粟”,并認為是當時“烏蠻”的一個組成部分。8世紀時他們的先民居住于金沙江畔。12世紀以后,受麗江土司木氏(納西族)及北勝州土司高氏(白族) 的統治,多數充當莊奴、院奴和農奴。16世紀中葉,由于麗江木土司與藏族統治集團發生戰爭,大批傈僳族在蕎氏族(括扒)首領木必帕的率領下,渡過瀾滄江,越過碧羅雪山,進入怒江地區。此后從17~19世紀的200多年中,傈僳族又有幾次大的遷徙行動,有成批的傈僳族越過高黎貢山進入緬甸境內,另有幾批向南沿著瀾滄江、怒江,經由鎮康、耿馬、滄源、孟連,抵達老撾、泰國等國,這就形成了傈僳族大分散、小聚集,跨境而居的分布狀況。
生活在怒江大峽谷里的傈僳族,位于祖國的西南邊陲,奔騰著波濤滾滾的怒江,高黎貢山雄峙于西,碧羅雪山屹立于東,兩山均在海拔4 000米以上,山勢陡峭,江水湍急,形成了我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峽谷地勢,不僅景色蔚為壯觀,且亦為祖國西南邊疆的天然屏障。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其特有的音樂文化。峽谷地勢,高山多平原少,只有不斷地往高山上開墾田地,造成耕地很大困難,他們不得不在75°的斜坡上耕種糧食,而且山上的土壤不適宜種糧食和蔬菜,所以產量很低。在這樣艱苦的自然條件下,造就了傈僳族勤勞、開朗的性格。他們酷愛打獵,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長刀和弓弩,因此傈僳族的多數音樂舞蹈都來源于勞動生活。處在祖國邊疆,高山形成的天然屏障,峽谷里狹長的公路,沿江相對的村落,使得他們經濟落后,發展緩慢,文化交流少,形成原始、純樸的音樂舞蹈。怒江峽谷里還居住著怒族、傈僳族、白族、漢族、藏族等,他們信仰著多個宗教,如傈僳族的東巴教和藏族的藏傳佛教等,是一個多民族、多信仰和諧共處的地區,各民族間音樂舞蹈有融合相似之處,也有專屬自己的特色。
在進入六庫城區的路口花園里有這么一座石雕塑,一男一女正在歡歌起舞,男的手拿樂器,他彈奏的是傈僳族琵琶——起奔。起奔是傈僳族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樂器,它在傈僳人民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無論男女老幼,只要一聽到起奔聲響,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這件樂器伴隨著傈僳族數百年的歷史發展,經歷了不斷地演變、傳承。它蘊含了無數傈僳人的美麗傳說,琵琶歌里訴說了傈僳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它象征著傈僳族的血脈,世代相傳。
隨著社會不斷進步,經濟快速發展,信息快速傳播,外來文化開始一步步打開落后地區的大門,慢慢滲透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使得原始、純樸、特色的民族民間音樂受到沖擊。起奔,這件古老樂器的傳承和發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礙,瀕于流失和消亡。如何保護、傳承和發展這件樂器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從起奔的傳承現狀做出分析,并結合本民族實際情況,按照其文化發展規律,辯證客觀地提出幾項建議來保護、發展這件民族樂器。
“起奔”及傳承現狀
在進入傈僳村之前就聽到人們形容起奔的形制和演奏,在文獻上也查到了一些關于起奔這件樂器的描述,對它筆者產生了很多想法和疑問。這次有幸拜訪到傈僳族具代表性的3位彈奏起奔的民間藝人,近距離接觸了這件樂器,深入了解它的形制、音色、彈奏方法及發展情況。
“起奔”,是傈僳族的琵琶,根據傈僳語發音而得名。體積比漢族琵琶小,音箱較薄,面板上有10多個圓形的小音孔,無固定品位。四弦,過去用羊腸制弦,現改為金屬弦或吉他弦。彈奏時用右手食指和拇指向內外連撥帶掃,有時2根、3根甚至4根弦同時撥掃,有和弦襯托;有時2個到3個旋律同時進行,演奏技巧較高,音色清晰明朗,富于表現力。起奔的用途主要有3種:獨奏、彈唱和彈跳——為舞蹈伴奏,邊彈邊跳。獨奏曲《打獵調》描繪了獵人出發前準備弓箭、射箭練習、呼喚獵狗、出發進山,直到獵獲野物的整個狩獵過程,加上彈奏者富于情趣的表演,使聽者猶如身臨其境。如:《打獵調》 《老虎與水獺》等。起奔在舞蹈曲調有幾十種,短小、反復較多,節奏鮮明,在旋律進行中經常出現一個持續音支撐和襯托著旋律。在彈跳中,還可以把起奔舉到頭上或放到背后反彈,與敦煌壁畫中的反彈琵琶相似,這種姿勢在傈僳族比較古老的舞蹈中就有。青年男女談情說愛時,互相搭肩,男的撥彈,女的按弦,稱為“雙人琵琶舞”。這些演奏都須有較高的技巧。如:《雙人琵琶舞》 《高山調》 《且俄》等。
從這件樂器的形制和用途可以看出,它既方便使用、用途廣泛又具有本民族特色,在傈僳人民生活中有著重要作用。但是,當我們深入研究的時候,發現它的傳承逐漸消亡。
1.獨自享樂在起奔音樂中的民間藝人
鄧四垮,男,傈僳族。1950年出生,被命名為云南省民族民間音樂藝人,擅長起奔(傈僳族琵琶)演奏。他獨自居住在福貢縣城,看到我們的到來,他馬上換上傈僳族的傳統服裝為我們熱情、投入地表演并講述有關打獵的場景《老虎與水獺》。邊彈他的身體就隨著旋律開始動,形象地表現了一個獵人的機智、靈敏。演奏完之后他說:“現在年紀大了,在過去能跳得更好。”接著他就叫我們年輕人跟著他跳,聽著節奏,雙腿跳著步伐,身體隨著旋律擺動。他說:“現在來學的人越來越少,你們來的人,我都教你們。”之后,他又坐下來為我們彈奏起奔,因為患了風濕,手指疼痛,他制作了撥片來代替右手指彈奏起奔,音色較清脆。起奔弦用的是緬甸買來的吉他弦。除了彈奏的這把起奔,墻上還掛著另外兩把,都是他親自制作的,琴頭還雕刻了羊頭,工藝很精致。他說:“有時會有演出隊或個人來找他買起奔。”當我們問:“您的徒弟多嗎?”他微笑著回答說:“真正感興趣來學的很少,沒有年輕人,都是對自己民族文化了解的同輩人。還有些是聽到政策學習民族民間音樂有補助就來了,補助沒發,又走了。”講完之后,老人說:“來,我教你彈。”
2.虔誠的基督教徒、專業制作起奔的民間藝人
阿赤恒老人,他居住在福貢縣的赤恒底村,在江對岸的半山腰上,那里風景秀美,往下看是蜿蜒的怒江,往上看藍天白云和河對岸的高聳青山。山上最好的建筑是教堂,鋪的水泥地,建的磚房。他們居住的是自己建蓋的木質房。村子里居住有傈僳族、白族、怒族等,多民族雜居,他們和諧相處,只有4戶人家沒有信奉基督教。走在村路上,每戶人家的大門都是敞開的,村民見到我們,就會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們到家里。會說漢話的村民,主動與我們打招呼,問我們有什么需要幫助,并為我們帶路。進入阿赤恒老人家里,有兩個小孩和兩個老人,他的兒子和女兒都在新疆打工。他也信奉基督教,看到我們的到來,他很高興也很歡迎,給我們倒水。在了解了我們的來意后,他為我們彈奏了幾首起奔樂曲。歡快的節拍和短小、反復的樂曲沒有歌聲和舞蹈動作的配合,稍顯僵硬而沒有生機。這是因為老人信仰基督教,教義不讓信奉的教徒唱歌、跳舞,彈琴也只能在家自己小聲地彈奏。我們不解,老人又跟我們進一步解釋:“歌里唱道‘彈起琵琶,唱起歌,喝起酒來,跳起舞’傈僳人民的歌舞和酒是有聯系的,人們總是唱起歌來想喝酒,喝起酒來想跳舞。但是,基督教不允許信教者抽煙、喝酒。”所以自從信教以后,他都不再唱歌、跳舞了。
在老人居住的房子對面,有一間專門制作起奔的閣樓,整齊地堆放著10多個起奔的模子,還有切割木頭的機器以及制作起奔的工具。他說:“有些旅游公司或是單位會跟他訂做起奔,有的一次就要20把。”我們問:“有人來跟你學習制作起奔嗎?”他說:“沒有人專門來學,感興趣的會來看一下。以前也沒有人教過我,彈起奔是父親帶我彈會的,我們想彈起奔就自己做,或是用家里傳下來的。”我們又問:“那你會教你的兒子或孫子彈琴或是做琴嗎?”他說:“他們感興趣想學了就教,現在年輕人都忙著在外打工,小孩都跟著上教堂唱歌了。”
3.不斷為起奔發展做出努力的藝術團團長
我們在福貢縣文化局的藝術團排練廳里見到了車四恒團長。見到我們就激動地說:“給你們看看我們藝術團排練的節目,有歌舞、器樂還有綜合類的節目呢,把我們的節目宣傳出去,讓我們這個落后地區的音樂發展起來。”團長熱情地為我們表演了節目,背著起奔又唱又跳,他幽默詼諧的表演,帶動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著他跳動起來。車團長跟我們說了藝術團的發展設想,團員們彈奏的起奔都是由他制作的,他在起奔的面板的音孔上畫有山水,他說那是代表了石月亮,傈僳族的傳說里就有說他們的祖先是從石月亮里走出來的。團長的積極、熱情讓我們看到傈僳族民間音樂發展的希望。同時團長也有他的擔憂,雖然他在不斷地為本民族民間音樂做出努力,也改變不了多少現狀,只有靠政府、社會的力量才能看到本民族民間音樂發展的希望。
車團長說:“起奔在傈僳人民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件樂器,幾乎每個傈僳人家里都掛著一把。過去,吃完晚飯后,人們就紛紛站起圍著鍋莊就開始跳起舞蹈,一般男的彈奏起奔,女的吹“嘀哩吐”(傈僳族的一種吹奏樂器,形似小短笛,豎吹),邊跳邊彈、邊彈邊唱,歡快、短小的旋律無限反復,直到跳累了為止。接著又換一首曲調開始唱歌、跳舞,舞步跟著彈奏起奔的節奏一起變化。有時到院子里全家老小一起跳、有時到村里的平壩子里全村人一起跳。它帶給傈僳人快樂,因此人們熱愛它,把它作為傈僳族的代表性標志。只要說到傈僳族就馬上想到起奔,只要彈起起奔就肯定知道是傈僳族。”他說,他就是被背在舅舅身上學會的起奔,長大后起奔拿起來就會彈了。有村民跟他這樣說:“在外打工回來,只要走到山腳,就能聽到村里傳來的起奔響聲,每當這個時候就有想流淚,因為回家了!”在過去,每個傈僳男人都要會彈起奔,姑娘們才會喜歡,所以男孩們自懂事以后就要跟著父輩學習起奔,學會了就結伙到山坡上彈起奔唱情歌,姑娘們心儀了就會吹起“嘀哩吐”或是“口弦”合上旋律。“不過現在這樣的景象少了,”他說,“空余的時間,大家都走進教堂,聽教義,唱教會的歌。”
在采訪完這3位民間藝人后,更深地了解了起奔,也為這件樂器的傳承和發展引發擔憂和設想。在大環境的改變下,它慢慢地退出擔當重要位置的舞臺。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山里人接觸更多新穎的事物;基督教強勢文化的迅速發展,一方面阻礙了民族民間文化的發展;民間藝人都是50年代后,隨著他們的衰老逝去,還有誰來講述有關起奔的故事、有關本民族的傳說、有關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的發展……
起奔的發展設想和改革建議
起奔,傈僳族的琵琶,它同漢族琵琶一樣,隨著人類的發展,經過人們不斷地改進,才演變成今天的形制。但是它的發展軌跡和漢族琵琶有所不同。第一,它還是保留橫抱指彈的演奏方法;第二,起奔樂器本身的形制保留了小型的,音箱較小,能抱在身上靈活彈奏,像最早傳入東方的琉特琴;第三,起奔琴的弦用的是金屬弦,這樣音色較為清脆明亮。當地的人們把它稱為“土吉他”。從它的形制和用途來看,確實是向著吉他的形制、用途方向發展。彈奏者能舞能唱,攜帶方便,實用性很強。音色具有本民族特色,清脆明朗。這些都是起奔的優點,也是流傳了那么久的原因所在。
但是,當更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傳入落后地方的話,它原先積累的文明就會被充斥。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只有取長補短,拿先進的東西充實不足,用傳承的優秀財富排斥這種威脅。
1.發揚本民族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起奔”走進學堂
教育是人們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民族特色藝術教育是承載本民族精神與情感的重要載體。在基礎教育的課堂里,應該增加一門課程——傈僳族音樂課,內容包括:本民族的民歌學習、樂器學習、舞蹈學習等。讓民間老藝人走進學堂,給青少年兒童講民間故事,表演本民族歌舞。提高學習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興趣。
發展本民族特色,要從強化本民族文化做起,從基礎教育做起。也就是說,從本民族最小的文化傳承者做起,普及并發揚。“起奔”作為傈僳族的代表性樂器,應該讓其走進學堂,強化普及。它具獨特的音色,靈活的彈奏方法和方便的實用性,能讓每一個傈僳小孩認識到本民族的文化傳承結晶,知道琵琶歌里唱出的傈僳族歷史,了解因為有了“起奔”情歌才有了血脈相傳,感受到本民族的自豪。
2.發展本民族樂器,改進 “起奔”形制
每一件樂器都歷經過歷史的演變,每一個民族都接受著不同時代的考驗,每一次發展進程都面臨著改革的過程,每一次成功喜悅的背后都蘊含著無數次的失敗嘗試。要繼續傳承就必須有發展,想要發展就要面對改革的困難。
起奔,這件樂器需要不斷發展,才能適應先進的外來文化;只有對其進行不斷地改進,才能跟上時代腳步,得以傳承。首先,樂器本身需要改進,增強它的實用性,發揮它的表現力,不僅能發揮更大的用途,更能突顯個性。筆者在起奔形制上提出大膽的設想,在起奔的琴桿上是否可以裝上像吉他一樣的品格?4根弦都換上尼龍弦或是吉他金屬弦是什么樣的音色?調弦用的弦軸制作方法是否可以改進?做琴用的杉樹木是否可以用別的木制作改變音色?等等設問和構想讓我們對這件樂器產生了濃厚興趣和美好期望。我們深知改進一件樂器是要不斷地探索和堅持不懈地研究,更重要的是落到實處地進行試驗。從我們采訪的民間藝人彈奏的起奔可看出,他們已經在對其進行改革研究,特別是福貢縣藝術團團長車四恒,正在不斷地改進樂器功能。筆者也將會對起奔的形制改革,進行不斷地研究和努力。希望社會各界也能重視民族樂器的改進。
3.發揮本民族樂器實用性, “起奔”走進教堂
自從19世紀中葉后,基督教和天主教傳入傈僳族地區,他們絕大多數對基督教的信仰都是一致的,只有極少數的人保持著原始的信仰。進入怒江地區,沿路都可看到高山坡上坐落著傈僳族村莊,山坡上最好的建筑就是基督教堂,當地的基督教信仰影響著怒江傈僳族人民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各民族之間和諧相處、穩定發展、民風淳樸,情感紐帶深厚,形成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有著深厚西方文化根基的基督教不斷滲透、同化,慢慢地影響著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給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帶來很大地沖擊。
在本土的基督教堂里有吉他、架子鼓等西方樂器作為唱贊美歌的伴奏樂器。那么,為什么本土的民族樂器不能作為伴奏樂器進入教堂,為本民族人民服務,發揮它的社會功能。一件樂器必須在各個時代,發揮它的社會功能呢?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如果樂器本身音域有局限,我們可以對其進行改進,有很多人為此正在做出努力。信仰基督教的人們受到教義的積極影響,認識到喝酒有害身體。因此,起奔進入教堂不會帶來負面影響。起奔走進教堂,既能讓人們體會到基督教會的包容,又能打造出民族地區教堂特色的品牌。我想,隨著贊美詩應用了傈僳語唱誦等本民族特色的應用,這個提議應該可以實現的。
“起奔”走進教堂,可加快本民族樂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加強本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延續了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
4.打造本民族樂器品牌, “起奔”走進市場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樂器作為代表,傣族的葫蘆絲、彝族的月琴、佤族的獨弦琴、藏族的弦子等。傈僳族的“起奔”也可打造本民族品牌,打入市場,提升其社會認知度。到了怒江地區,我們只有在趕集或藝人家里能交易到“起奔”,來旅游的人們就了解不到這件樂器。本民族樂器需要市場窗口,來作為推廣它。如,在旅游景區提供本民族樂器展覽、交易的場所,鼓勵傈僳百姓制作本民族樂器,并進行裝飾,形成手工藝商品展示、交易。
品牌需要通過一些社會活動來進行推廣。如,每年舉行本民族樂器比賽,分年齡組進行,請民間藝人作為評委。選出的最佳演奏者,可參加對外交流演出,多鼓勵、組織年輕人參與。加強民眾參與性,提高學習興趣,加深各階層人們對本民族傳統的了解。
結 語
“起奔”,是傈僳族人民日常娛樂生活離不開的一件樂器,它的形制、音色、琵琶歌、琵琶舞里唱出了傈僳人的勤勞、歡快、純樸、勇敢,以及對美好生活的無限向往。“起奔”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是傈僳族歷史文化傳承的一個載體,能體現本民族音樂藝術發展方向。傳承和發展這件樂器的研究工作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傈僳族,是云南跨境少數民族之一,他們跨境而居,有著純樸、優秀的本民族傳統音樂文化。隨著時代變革、信息快速發展,面對強勢、外來文化的沖擊,本土民族民間音樂(樂器、民歌、舞蹈),正面臨著發展和傳承的危機。我們應該積極探索云南跨境少數民族樂器的發展方向和解決它們的傳承問題,并探究它們的發展軌跡和基本內涵。不僅這一件樂器接受著考驗,另外其他音樂樣式也同樣需要人們用辯證的目光分析并進行搶救性研究,提出方案,來拯救我們的少數民族音樂藝術,讓它繼續傳承少數民族人民的文化歷史,隨著時代的變革繼續發展。這是時代給我們提出的挑戰,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