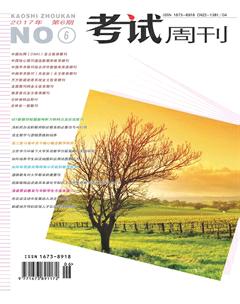“漁父莞爾而笑”中“笑”的含意
王莉
摘 要: 文章結(jié)合時代背景,立足教材,由淺入深地對蘇教版必修五《漁父》一文中“漁父莞爾而笑”進行探究。弄明白兩人對話的意思、《滄浪歌》的含義及漁父的形象意義,把握“笑”的含意,理解漁父對屈原的態(tài)度。
關(guān)鍵詞: 理解 同情 敬佩
蘇教版必修五里有篇文章《漁父》:“一打魚的老年男子,在湘江邊遇到了被流放的屈原,對心力交瘁的屈原進行了勸導(dǎo);但屈原有自己的堅持,沒聽漁父的勸,漁父就微微一笑,敲打船槳,唱了一首《滄浪歌》離開了。”很多學(xué)生對“漁父莞爾而笑”的“笑”字不解,他們很想弄清楚漁父對屈原以死明志的看法。于是筆者進行了探究,并明白了三點:兩人的對話是什么意思,《滄浪歌》是什么意思,以及漁父的形象意義。
從字面看,漁父勸屈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聯(lián)系時代背景不難發(fā)現(xiàn),漁父是在勸屈原:“‘不拘泥于任何事物,并能夠隨著世道而變化——不要再被三閭大夫、左徒等職束縛住了,楚國都已經(jīng)君昏臣聵節(jié)節(jié)敗退、岌岌可危了,屈原你就不要再以楚國興衰為己任了,你從眾吧!”這番勸導(dǎo),屈原如明鏡般通曉,但他有著強烈的責(zé)任感,他認為“帝高陽之苗裔兮”,必“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為了楚國,他始終不渝地堅持“聯(lián)齊抗秦”的主張。于是他回答漁父:“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上官大夫的讒言、楚懷王的怒而遠疏、子蘭的指使誣陷、頃襄王的怒而遷之,這些都是污濁的外物,都在玷污屈原的人格、抹殺屈原的忠心,銷毀屈原的理想。屈原把人格和理想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他怎么可能聽從漁父的與世推移呢?屈原激憤地向漁父宣告自己決定以死明志:“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漁父聽了,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漁父真正理解屈原嗎?漁父,漁翁,在水邊打打魚,看看煙霞,唱唱歌,他能一眼認出三閭大夫屈原,可見他有豐富的閱歷、卓越的見識,并不是一個愚昧無知以打魚為生的社會底層平民。他能說出“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的話,足見他能看透塵世,非常有智慧。這位老年男子看似只是一介漁翁,但必是隱士高人。在那樣一個混亂動蕩的時代,漁父避世汀濱,不與世事,恬然自安,不能不說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這樣的智者是能理解屈原雖不在其位仍有著存君興國的抱負的;也能理解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怨憤;更能理解屈原以死明志、舍生取義的決絕。“莞爾而笑”里有理解。
有人說屈原是行到水窮處的儒生,漁父是坐看云起時的隱者,兩人代表兩種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面對屈原的決絕赴死,漁父不慍不怒、不強人所難、莞爾而笑,鼓著枻唱著留給屈原最后勸告的《滄浪歌》離開,留下屈原在江邊孤獨思考。“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清的時候可以用來洗滌冠纓;水濁的時候就可以用來洗腳。“水清”喻指世道清明;“水濁”喻指楚王昏庸、小人當?shù)馈⒔尤障碌默F(xiàn)狀;“濯我纓”,喻指入朝為官、實現(xiàn)自己理想;“濯我足”,意味(屈原)你可以“蓮出淤泥而不染”,沒必要以死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潔,既然你無力改變“舉世皆濁”的世態(tài),你應(yīng)該豁然地面對這種世態(tài)。常言“君子處世,遇治則仕,遇亂則隱”(《漢書新注》)。此時筆者聯(lián)想到了《笑傲江湖》的主題曲,“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記今朝。”兩首歌都表達了“在社會的浪潮里,渺小的人只能隨浪沉浮,與世推移”的意思,而屈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非要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弄得自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自令放為”。在漁父看來,屈原活得沒有自我(一心忠君愛民)、活得太累(堅持政見獨木難支)、活得太慘(被中傷被排擠)。漁父唱起了在楚地流傳久遠的滄浪歌,意在啟發(fā)屈原如何面對現(xiàn)實。通過歌詞,我們能讀到漁父對屈原自身不幸遭遇的同情。“莞爾而笑”里有同情。
有人說《漁父》一文中虛構(gòu)了漁父和屈原的對話,實際上是屈原的自問自答,表現(xiàn)了屈原內(nèi)心的矛盾。按照這種觀點,這個漁翁是不存在的。那么戰(zhàn)國秦漢間人記敘屈原事跡的時候,為什么虛構(gòu)出漁父這個人物形象呢?總不會因為屈原在湘江邊遇到的人屬打魚的概率最大吧?王逸的《楚辭章句》:“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楚辭》中的漁父,都是避世埋名的隱士。假如作者虛構(gòu)了這個無拘無束的保持高潔的隱者,他想傳遞哪些觀點呢?漁父乘扁舟漂游水上,自然,愜意,無拘無束。中國文人通過漁父這個意象寄托著對超然生活的向往之情。永貞革新失敗后,處境孤獨的柳宗元借“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表達了自己的傲岸不屈;楊慎因當庭痛哭廷杖被貶后,縱酒自娛,游歷名勝,寫下“白發(fā)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fēng)”;“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李白都曾向好友李云抒發(fā)過自己懷才不遇的牢騷——“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可見漁父們都是得意時出仕兼濟天下,失意后歸隱吟風(fēng)嘯月。在筆者看來,最像漁父的當屬蘇軾。烏臺詩案后,蘇軾平靜地接受了政壇潑來的污水,他的思想幾度變化,由入世轉(zhuǎn)向出世,追求一種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無邊的江海中一葉小舟逐漸行遠,離了塵世。在這余韻深長的歇拍中表達了蘇軾瀟灑如仙的曠達襟懷、向往自由的心愿。《漁父》一文虛構(gòu)出身心自由、鼓枻高歌、欣然自樂的漁父,與積極用世、深思高舉卻慘遭流放、痛苦萬分的屈原作對比襯托。畢竟吟風(fēng)嘯月容易,特立獨行困難;無世無爭容易,憂國憂民困難;合乎自然容易,力挽狂瀾困難;恬然自安容易,矢志不渝困難;明哲保身容易,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困難!漁父的“莞爾一笑”里應(yīng)當還有敬佩。
“漁父莞爾而笑”,這是一位哲人對一位詩人的深層理解,這是一個隱者對一個猛士的深深的同情,這是一個“理想寄托”對“理想追求”的敬佩,這是漁父和屈原基于心靈默契之上的對立和轉(zhuǎn)向。漁父莞爾而笑,意味情長,擊槳遠去那滄浪之歌依然余音裊裊……
參考文獻:
[1]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史記》選讀.
[2]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史記》選讀教學(xué)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