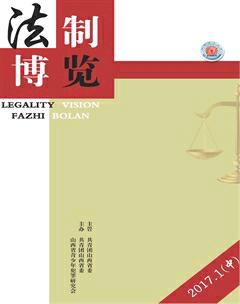我國錄音錄像規定的適用現狀及完善
張璐
摘要:我國目前適用錄音錄像規定的適用現狀主要表現為,對錄音錄像規定的適用缺乏監督機制,存在補錄或者重復錄音錄像的現狀,將犯罪嫌疑人帶出看守所外未規定要進行錄音錄像。就產生這些現狀的原因而言,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新刑訴法為增加該條規定之前,偵查人員主要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定案依據,以傳統的方式進行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攻破。因此在出臺該規定后,偵查人員不愿使用,其次,在立法本身存在不夠明確和科學地方。因此,對我國錄音錄像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議,在不超越法律規定的范圍,對立法進行細化的規定。
關鍵詞:錄音錄像規定;適用現狀;完善建議
中圖分類號:D9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02-0094-03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以來,我國以立法是形式確立了訊問時錄音錄像制度,在新《刑事訴訟法》第121條進行了規定,為確保修改后的該條規定順利實施,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根據新刑訴法的修改,可以看到該條規定的增加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和實踐中的不足之處,以及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研讀了張穎教授的《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一文后,筆者認同他對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現狀的剖析。全文首先從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的立法規定及司法適用方面介紹了該項制度;其次,自新刑訴法增加該規定以來,該制度在我姑目前的適用現狀,又通過比價的方法,與美國地區、臺灣地區進行對比,從而概括出三種模式,分別是:剛性模式、推定模式和權衡模式;最后,基于刑訴法第121條規定,張穎教授認為立法的缺陷在于,如果違反了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得的證據其證明力該如何判斷,以及對排除供述面臨的現實制約進行了法院實地調研和探討。
綜合研讀了郭文利,謝小劍、顏翔,縱博等學者的相關文章后,張穎教授的文章綜合分析了錄音錄像規定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和問題,相較其他文章來看,更有一些見解可以適用于今后的司法實踐中,就拿謝小劍、顏翔的《論同步錄音錄像的口供功能》這篇文章來說,雖然涉及了相同的問題,但是出發點卻不同,重點從口供的功能方面談到同步錄音錄像制度,所解決的問題對司法實踐作用相對較少。張穎教授從學術的角度分析了我姑刑訴法立法中的現狀和不足,有利于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促進有關證據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減少因證據問題導致的實踐中的冤假錯案。
一、美國、英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的錄音錄像規定
(一)美國地區錄音錄像制度的適用情形
在張穎教授的文章中,通過比較研究,提出了三種模式,即剛性模式、推定模式和權衡模式。在美國,阿拉斯加州是第一個制定相關法律的州,該州的法律規定了警察在訊問被指控為犯重罪的犯罪嫌疑人時,必須全程錄音錄像,如果違反該規定,這些犯罪嫌疑人作的有罪供述就不能作為定案依據。這種剛性模式下,只要訊問中未按規定進行全程錄音錄像,那么訊問所得出的供述則不具有證據能力。①這樣的規定優勢在于,有較強的威懾力,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便于執行,但是這個規定,過于機械和絕對,如果斷然否定供述的證據能力未免顯失公平。因此該規定遭到美國各州的反對,在2010年是美國對此做出了一定的改變。如在美國的伊利諾斯州,該州法律作出規定,如果訊問時沒有全程錄音錄像,那么就將直接推定所獲得的供述不具有證據能力,除非控方證明了嫌疑人的供述具有自愿性,這樣才可以推翻之前的推定。這一規定符合了張穎教授提出的推定模式。②
(二)英國錄音錄像制度的適用情形
在訊問中引入錄音錄像制度最早源于英國。在英國,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保障訊問的真實性。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正式將錄音錄像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隨后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執行守則》的相繼出臺,在訊問中同步記錄的制度,具體表現為有兩種方法:一是制作同步訊問筆錄。無論訊問的進行是否在警察局,但每次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都必須準確記錄在案;訊問過程也要做記錄,除非調查人員認為這一行為將干擾訊問或者不可行;訊問的內容必須逐字逐句的完整記錄,如果達不到該標準,記錄須充分概括談話內容。二是對于嚴重犯罪,審訊時必須錄音或錄像。隨著上述法律及相關執行措施的出臺,英國在立法上最終確立了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在此之后,除了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或者少數的恐怖主義犯罪嫌疑人的訊問沒有要求錄音的以外,其他嚴重刑事案件的審訊全部都進行了錄音,有些還進行了錄像。目前,在英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雖然警察對被告人供述采取了保全措施,以及在向法庭出示被告人的供述時,基本上采用錄音錄像帶存儲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該證據能力仍然要受被追訴人意志的制約。③
(三)我國臺灣地區的錄音錄像制度
在我國臺灣地區對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的供述是否具備證據能力,需要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經法官裁判之后作出裁決。在臺灣地區,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警察訊問犯罪嫌疑人如果違反了全程連續錄音錄像的規定,其獲得的供述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由法官決定。法官的決定應審酌司法警察是否有違反法定程序的主觀意圖、客觀上有什么情節、是否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侵害的程度輕重,以及該犯罪所產生的危害和影響,對于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的維護,按照比例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④臺灣地區的這個模式,是否違反由法官進行自由裁量,這無形中擴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由于自由裁量權過大,就會缺乏對法官權力的制約,很可能會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導致判決的不確定性,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當法官由于職業素質、文化道德、法律素質等自身差異,很可能失去中立裁判的地位,就會導致案件的裁判合法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最終還會影響判決的公信力。
二、我國錄音錄像制度的適用現狀
正如張穎教授所說“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頒布而在于實施”⑤,新刑訴法增加了關于錄音錄像制度的規定,從立法層面上說,不僅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也能防止冤家錯案的發生,有利于排除偵查人員在訊問中的違法行為,如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非法手段。
但是該規定仍然給法律適用留有余地,使得在該規定出臺后,仍然存在一些不合法的行為,盡管公安部在新刑訴法出臺后就頒布了相關《規定》,對于其中訊問的一些問題也進行了解釋和細化,但仍然在實踐中存在問題。
就從立法角度來說,錄音錄像應保持全程性和完整性,但由于未規定錄音錄像過程的監督機制,因而在實踐中就缺少中立第三方對該過程進行的監督。如果錄音錄像人員和訊問人員是同一批人,就會出現有的時候補錄或者重復錄的情形。雖然法律規定訊問錄音錄像應該和訊問過程是同步的,不得進行補錄或者重復錄音錄像。實踐中,要求在訊問室內全程錄音錄像都無法實現,更何況在看守所外訊問,會讓人難以信服。
錄音錄像制度能夠有效防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保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長期以來,偵查人員利用偵查謀略等傳統方式進行訊問,這樣更有利于突破口供,而且實踐中也多以口供為定案依據。錄音錄像的規定出臺后,加大了訊問的難度,不利于辦案效率,由此偵查人員產生了對該制度的抵觸情緒,導致該制度在實踐中出現了實施難的問題。因此就會產生先審后錄等現象,使得錄音錄像成為一種由偵查人員安排的表演。在實踐中,最常見的刑訊逼供就是利用犯罪嫌疑人上廁所的機會,將犯罪嫌疑人帶出訊問室,直至打服后再帶回進行訊問。
將犯罪嫌疑人帶出訊問室,在訊問室外進行訊問但未錄音錄像的情況,這也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新刑訴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并且,公安部的《規定》也明確指出,不得以訊問為目的,將犯罪嫌疑人帶出看守所。這就意味著,一旦將犯罪嫌疑人交由看守所,就得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即使是在看守所外的訊問。由于法律未規定對看守所外的訊問行為進行錄音錄像,所以在實踐中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偵查人員以帶犯罪嫌疑人進行現場指認為由,將犯罪嫌疑人帶出看守所,在此過程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的行為,無從確定。
三、對我國錄音錄像制度完善的建議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適用錄音錄像規定的適用現狀主要表現為,對錄音錄像規定的適用缺乏監督機制,存在補錄或者重復錄音錄像的現狀,將犯罪嫌疑人帶出看守所外未規定要進行錄音錄像。就產生這些現狀的原因而言,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新刑訴法為增加該條規定之前,偵查人員主要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定案依據,以傳統的方式進行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攻破。因此在出臺該規定后,偵查人員不愿使用,其次,在立法本身存在不夠明確和科學地方。因此,對我國錄音錄像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議,在不超越法律規定的范圍,對立法進行細化的規定。
目前,針對訊問時違反錄音錄像規定的行為,我國立法仍缺少進行制裁和救濟的規定,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該規定的任意性。因此,應該對違反了錄音錄像規定進行監督和制裁。例如,在美國,在查看同步錄音錄像時為避免法官的認知偏見,所以采取雙攝像頭和畫中畫模式,并且會采取多攝像頭取景。從技術上的角度出發,這種模式的運用,能夠更好的發現和記錄犯罪嫌疑人的面部、身體部位的活動,也更便于偵查人員在此過程中發現偵查線索,在未能確定線索時可以采用回放的方式,多次觀看,便于更加仔細的記錄犯罪嫌疑人細小的行為和表情。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訊問時錄音錄像習慣將攝像頭對準犯罪嫌疑人。不僅有助于偵查人員更仔細的觀察,而且便于發現其中細微的變化,或者一些犯罪嫌疑人可能故意隱藏的證據,最終目的就是揭示事實的真相。不過在美國的實證研究表明,如果同步錄像的攝像頭只對準犯罪嫌疑人,容易讓犯罪嫌疑人產生認罪偏見,不利于法官的自由心證。為了避免產生偏見,錄像時同時對準犯罪嫌疑人和訊問者則能夠消除這一顧慮。⑥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借鑒美國關于錄音錄像規定的細致的做法,所以需要接入“第三者”,保證錄音錄像的公正性。⑦對于違反錄音錄像取得的證據,能否作為定案依據,其證據能力如何判斷,我國的司法實踐所采取的態度是“應當予以排出”。⑧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頒布而在于實施,在實施過程中,還需要偵查人員發揮該制度的真正價值,因此也需要提高偵查人員的個人素質和法律素養。
[注釋]
①張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J].證據科學,2015(6):673.
②張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J].證據科學,2015(6):674.
③董坤.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發展路徑[J].法學研究,2015(6):161-163.
④張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J].證據科學,2015(6):674.
⑤張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J].證據科學,2015(6):674.
⑥謝小劍,顏翔.論同步錄音錄像的口供功能[J].證據科學,2014(2):196.
⑦張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J].證據科學,2015(6):675.
⑧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中規定“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以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所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參考文獻]
[1]陳瑞華.刑事證據法的理論問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
[2]周寶峰.證據法之基本問題[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11.
[3]張穎.違反訊問錄音錄像規定所獲供述之證據能力問題[J].證據科學,2015(6).
[4]董坤.偵查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發展路徑[J].法學研究,2015(6).
[5]謝小劍,顏翔.論同步錄音錄像的口供功能[J].證據科學,2014(2).